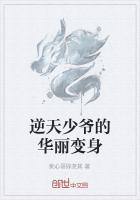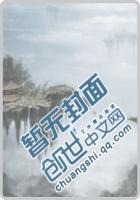我要不要请他一起去吃个饭呢?等他们检查完毕,快要离开的时候,我再找个机会跟他说。
“郭玉清,下班后还有没有事啊?我们找个地方一起去吃个饭怎么样?”在民田村会议室的讨论结束后,市局领导起身准备离开,我见郭玉清走在最后面,就赶紧跟过去,贴近他的身边小声地对他说。
“实在对不起!我今天晚上有点事,等下次再说吧。”他放慢了脚步,犹豫了有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拒绝了。不过正是这一阵短暂的犹豫,暴露了他所谓的“有事”不过是个托词。
“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聚了。”我仍没有放弃。
“是啊,是啊。……下次吧,下次吧。”他伸出手来跟我拉了拉,然后就立即追赶他那两个同事去了。
应该说,自从六年前离开观涛队后,我们虽有过几次见面,可每次都只是几句简短而又匆忙的问候,从未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
两个多月前,也是下午四点多,他们第一次来民田市场检查食品卫生时,我们同样只是简单地拉了几句家常。“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市局领导前来检查指导工作!”一见面,我还是象以前那样无拘无束地开着玩笑跟他打招乎。“怎么就来了你们三个?我还以为会有一大帮人过来。”
“是啊,就我们三个,走在最前面戴眼镜的那位,是市场处的彭处长,他是带队的,那边那一位是我的搭档,监察处的刘付科长。”稍稍停顿之后他又接着问:“你们队里是由谁负责这个市场的?”
“是李国才与我两个人。对这次的市场卫生与食品安全检查,市局好象是动真格的了?”
“那当然,聂局长亲自担任此次行动的总指挥,袁付局长也亲自带队到下面的市场去巡查;由此可见领导的重视程度!而且这次一旦发现问题,第一次是责令立即整改,第二次就要通报批评。”他语气坚定,表情严肃,完全没有了当年在观涛队我们面对诸如此类的检查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情。
“你还住在红旗路那边吗?”我还是换个话题。
“是啊,还住在那边。你小孩几岁了?应该上小学了吧?”
“上小学五年级了。你的呢?”
“告诉你吧,到上个星期天,小家伙才刚刚满月。”
“是吗!?有没有做满月?你也没通知一声,应该去祝贺你的。”他结婚已经有四五年了,怎么也是这么晚才要孩子。
“没有摆酒,就家里的几个亲戚在一起吃了个饭。”
“怎么样?小宝贝吵不吵?”
“快别说了,晚上有时候吵得让人根本就没法睡。”
“有所得就有所失嘛,作父亲是要劳心伤神的,不过慢慢就会好起来。你现在每天上下班都怎么走,从红旗路到市局可是有点远啊?”
“我现在很方便,市局接送员工的大巴就从我住的小区经过,每天只要能按时上下班,就一点都用不费周折。”
再前一次见面是在一年多以前,他也是同其他人一起下来的,那次是检查窗口作风与廉政纪律。来到我们队里,他们首先在各个办公室巡视了一遍,然后就上了队长办公室。那一次我们俩就只在我们办公室握了个手,最后连他们几时走的我都不知道;只是快到下班的时候,才听得林维山阴阳怪气地说:“市局领导已经走了,你也不去欢送一下。”
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俩已经没有单独相处并可无拘交谈的机会了。即使还有再见面的时候,那也不过象现在这样,只能是一些客套的问候而已。就拿这一次说,我们除了见面后打过一声招呼,以及刚刚向他发出的吃饭邀请,另外就再没有多说过一句话;临别的时候也只是淡淡地握了个手,一点都没有了以前老朋友间的那股亲热劲。
印象中的郭玉清一直是个谦和的人,与人相见时总是面带着笑容,特别是与你握手的时候,右手与你握在一起,左手还要抚在你的背上,让人觉得格外亲热。
也许人家现在已经是科长,地位变了,接触的人与事变了,因此各种关系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吧。刚才在民田村的会议室里发言时,他派头十足,对这个市场内存在的一些小问题,不断地发表一些品头品足的意见,还不时地与在坐的其他领导交换着看法。
十年前,我们差不多是同时来到观涛队的,他是七月初大学毕业后从学校分配过来,我则是七月中从内地调到这里。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观涛队的一楼大厅里。
“您好!我叫孙道仁,刚调来这里,以后请多关照。”当时在你的眼里,你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那里的老同志,都是你需要去努力巴结的。
“我叫郭玉清,也是刚毕业分配过来,比你早来十多天吧。”你当即就有一种他乡遇亲人的感觉;因为一来大家都是科班出身,我虽比他早毕业四年,但身上到底还没有完全摆脱那股书生气,对读书人无疑存有一种本能的认同;二来在这异地他乡,你已不再是唯一的外来者与新面孔,已经有了可以相互支持、并肩前行的“革命战友”。
“是吗?!是哪所学校毕业的?”
“楚天大学。”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
“行政管理。”
“那你分到这里来,应该说是专业对口喽。是不是市局去你们学校要的人?”
“是啊,市局每年都会从我们学校招人。”
“这次你们学校一共分来多少?”
“一共有十个,光我们班就有五个;不过就我一个人分得最远,而且在最基层,其他那些不是在市局,就是在各个分局机关。”
“你老家是哪里的?”
“浙江的。你呢?”他回答我,接着又反过来问我。
“湖南的。”
“这样说来,我们还曾经有过四年的老乡之缘啊。”他就读的楚天大学就在我老家那边。
“是啊!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以后咱们可得相互帮衬着点。”
“那是自然的。”
对于两个远离家乡的人来说,观涛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既无亲戚朋友,也无同学故交;因此自然地我们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下班后,两个人有时外出闲逛,有时在宿舍里下棋,有时就去观涛中学的运动场打打羽毛球;但最多的时候还是在一起聊天。在这种天马行空般的闲聊中,我们就曾常常交换一些关于宇宙人生之类的观点与看法。
“你认为人类对宇宙和物质的认识会不会有止境呢?也就是说,人类最终能否完全了解宇宙与物质的所有奥妙?”那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我俩趴在他房间的阳台上,遥望着一尘不染的星空,他突然发出了这样的提问。
“我觉得不可能。因为首先,宇宙太过庞大,到目前为止,人类的视角还仅仅拘限在银河系;然而,相对于浩瀚的宇宙,银河系也不过只是仓海一粟!其次,我们要看到,人类的存在只是一个短暂的偶然过程,说不定那一天他就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可宇宙的存在却是无法想象的久远;因此,要凭这有限的存在去穷尽无限的奥秘,这对人类来说,是难以企及的。况且,在宇宙之外,是否还存在另外的宇宙呢?这些人类也都无从得知,因为这已完全超出了人类的视界范围。
“当然,也不能忽视人类认知能力的强大;看看人类的文明史就能知道,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四五千年,尤其在最近的这一千年,人类的认知活动取得了何等辉煌的成就!探索的触角从宏观已经伸展到遥远的外太空,从微观也已到达了夸克的层面;可以说这个认识的过程是逞几何梯级地向前推进的。因此,人类完全有可能在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的存在中,寻找到将生命与智慧的火种延续下去的办法!
“从你刚才的这个问题,又让我想起了哲学史上一个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命题——就是‘认识的可能’。我刚才说到了人类的认识史,恰恰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你知道,人类对客观的认识,从来就是在对自身的不断否定中完成的,因此,人类的认识始终是‘未完成’和‘待完成’的;也就是说人类总是在对已有认识的否定中走上新的认识,但却永远无法走到认识的终点;因此说,人类根本就不可能达到宇宙的终极真理。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结果呢?这是因为人类总是站在‘事件之外’来认识事物。打个比方说吧,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就好比将洋葱一层层剥开,可每剥去一层,就会失去一层的真实,而且这种剥落将是永无止境的;况且,人类太多地沉迷在自身的感观印象上。因此,注定的:人类将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到‘事物之中’,自然也就无法进入到宇宙与物质的终极奥秘中去。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萨特的一句名言,他说:‘人不过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他说这句话,其实是站在浩瀚宇宙与永恒存在的高度上所发出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慨叹。可以这样形象地理解这句话: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落日沉沉,霞光满天,面对此情此景,人类怆然泪下,发出了无限感叹;然而,对于宇宙,甚至对于渺小的太阳系,乃至于象尘埃一样的地球,这不过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存在瞬间,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无需任何意义;可人类却赋予了它无限的情感与内涵,你说这不是人类在自作多情吗?现在,我甚至都怀疑萨特说这话时,他对自已苦心营造的哲学体系是否也产生了动摇!?”
我的这一通长篇大论显然有卖弄之嫌。但不知是没听懂我的意思,还是在独自思考,他只是木然地望着天空,对我的话未置一词;而我却只顾沿着刚才的思路继续往下胡诌。
“萨特的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悲观了?其实在对未知的认识上,人类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这里,我们就得绕过西方的二元认识论,返回到古老的东方来。二千多年前,东方的先贤们凭本能的直觉,似乎比西方人更接近了真理的殿堂。你看看道家的那些说法:‘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无中生有’等等观点;尤其是那让人叹为观止的太极八卦图,它几乎就涵盖了宇宙人生的一切奥妙!当然,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未能完全解读和充分理解它;但我敢断言:终有一天,人类会利用它去揭开宇宙的更多奥秘!”
稍事停顿后,我又接着往下说:“说到直觉,这确实是东方人最善于使用的思维方式,但现在已差不多快被逻辑思辨所全部取代了。”
“没错,没错。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确实,我们的脑子里已塞进了太多的逻辑与理性,早已将老祖宗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思想忘却得一干二净了。”他象猛然醒悟了似的,对我的说法连连表示赞同。
“话到这一步,再说下去就有点神秘主义的味道了。不知你是否相信有一种宇宙能量。按照某一种观点的说法,所谓‘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其实就是这样一种能量的相互传递。我不太相信这种观点,但在现实生活中,这可能就是有些人所说的那种第六感觉吧!”我知道,这有点胡扯了。
“是吗?!这我可从未听说过。”他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作出一副不置可否状。
我们在一起也谈论理想与追求的话题,我记得那时对他说:我的人生理想就是写一部惊世骇俗的长篇小说、一部全新观点的哲学论著,然后再去周游天下,写一部包罗万象的游记。听我这样一说,他当时就流露出诧异与赞服之色,并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当问到他的理想时,他总是说小的时候梦想当一名科学家,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想法又不断淡化,到后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很明确的目标,现在就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当然,我们之间也不并非什么话题都能谈得来,譬如我同他说到禅与佛等崇教问题时,他却一味地坚持那是迷信的东西,是一种彻底的神秘主义;同时,还劝我要少接触,否则会移情易性,坠入消极的悲观主义中。
我喜欢买书,到观涛队后也买了不少书,一个小小的书架早就被装满了不说,书桌上、床头边也都散落地摆了一大堆。他每次到我房间里来,总爱在这些书堆里翻找一通——这大概是读书人的共同爱好吧。我也曾向他介绍过一些书,有时他听了我的介绍,觉得有趣的也会借去一读。记得有一次我把自已看过两遍的那部《追忆逝水年华》推荐给他,并极力向他吹捧这是如何如何的一部奇书;他受了我的影响,把那部书拿了过去;一个月后,他把书还给了我,我当时有些愕然:这部七卷本的书我至少用了半年才算看完,他却只用了一个月!
“怎么样?有什么心得与感想?不过你的速度可真够快的,要知道这部书我至少花了半年时间才把它啃完!”
“我算是佩服你的阅读功夫了。说实在的,这种书不适合我,我根本就看不下去。”
“第一部总该看完了吧?我觉得这是全卷中最精采的部分。”
“没有。我只翻看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适合看一些轻松的现实主义作品。”
我们在一起工作生活有三年多,我觉得他对我的志趣与爱好应该是相当了解的,因此我将他视为知已;自然,他也将我当成在这异地他乡最可信赖的朋友。在我离开观涛后的时间里,他仍然在原先的一些同事中吹虚我的所谓才学。这是后来我从王久耀嘴里了解到的,他在我来到民福的大概一年后,也由观涛调来了民福,有一次我们在一起闲聊时,他对我说:“你知道吗?孙道仁,郭玉清对你很是摧崇,他说你很有才学,也很有思想。”再后来,这同样的意思我从李少华那里也曾听到过——他也是从观涛调到这边来的。听到这些,我当时就有些羞惭,因为其实一切并非如他所说的那么好。
更让人汗颜的,还是那次上分局时他对我说的那句话。在我离开观涛后的第二年,他也被调到分局商检科。有一次我上分局公干,办完事后去他办公室看他。刚开始我们照样也是一阵寒喧;接着他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最后他对我说了一句:“你有没有写点什么?你应该写点东西,否则,亏了那满腹的才学!”我知道,这看似吹捧的一句话,包含了他的信任与期待;可对我却是个不小的冲击,因为至今你尚无一字见著!
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今天在这里再次相遇,差不多十年过去了,他现在已是市局监察处的一名科长,而且不久的将来肯定是付处长,接下来又会是处长,可以说前途不可限量;而你比他年长四岁,早参加工作四年,至今却仍只是一名普通科员。这让人家怎样看你呢?——那不过是一个光说不练,只知道胡编瞎吹的慵碌之辈而已,这种人既不能著书立说,又无法晋升仕途;至于我原先对他的看法,那不过是被他的那些假象迷惑住,是我把他看高一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