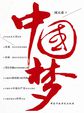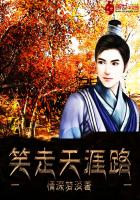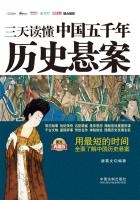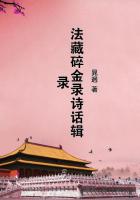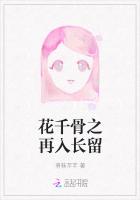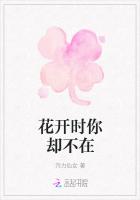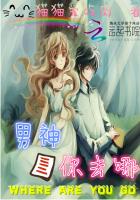鄂尔泰在用兵过程中,深感对偏居一隅的土司光用兵还不行,必须改土归流,将土司制度彻底清除,方可一劳永逸。他提出“计擒为上,兵剿次之;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这亦是改土归流的指导方针。雍正帝十分赞赏鄂尔泰的建议,批准其方案。为了改土归流方便,雍正下令将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府改隶云南。从此大规模改土归流便逐渐在西南地区开展起来。
鄂尔泰的开端是分兵三路进兵长寨。长寨地处苗地之腹,土司猖獗一方,鄂尔泰三路兵进,尽斩其首从,大获全胜。并在此处设参将营,分守险恶地方,设立保甲,推行保甲法。接着,鄂尔泰乘威招服东、西、南三面的广顺定番,镇宁生苗680余寨、永宁、永丰、安顺生苗1398寨,兵锋直抵广东边境。贵州南、北、西三面局势稳定下来后,鄂尔泰集中兵力向黔东苗岭山脉和清江、都江流域进兵。这一地区是贵州著名的“苗疆”地区,土司向来没有约束其地,苗患甚于土司。这里对于清政府在西南的统治与沟通南北交通,都具有重要意义。鄂尔泰任用熟悉此处地形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率兵入“都匀”、“黎平”等地化导群苗。张广泗不负众望,征抚并用,很快平息了此地。
贵州古城、台拱等地设官以后,原土舍势力仍很强大,平定不久即发生叛乱,声势浩大。雍正派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但张照到任后,反对大学士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政策,而且他不懂军机,胡乱指挥,以致于旷久无功。乾隆即位后又起用张广泗经营苗疆。张广泗兵进三路围剿,终于攻破苗疆的险要牛皮大箐,生擒首犯包利等人,斩首万余人,苗疆之乱平息,在古州朗洞及凯里各增设一营,在起乱各处增兵驻防。
云南与贵州相邻,土司势力很强大,猖獗万分,特别是乌蒙、东川、镇雄三府土司势力强大。鄂尔泰于雍正四年初督改土归流时,便将东川府划归了流官管理,一切土臣,尽行更撤,以马龙知州黄世杰为新任流官知府。东川首先实现了改土归流。同时,鄂尔泰派人乘胜招降乌蒙土府禄万种、镇雄土府陇庆侯,但因二府相争作罢。1730年(雍正八年),禄鼎坤(禄万钟之叔)煽动反叛,拥兵数万,声势浩大。鄂尔泰调集万余名官兵,分三路进剿,经激烈战斗,鄂尔泰亲自督战,最后把禄氏土司的叛乱镇压了下去,禄鼎坤被生擒正法。
同时,鄂尔泰亦出兵滇南傣族居住区,平定于雍正五年发生的叛乱,接着,纵兵深入澜沧江下游数千里,无险不搜,将滇南各镇府全部改流;在同时,于四川凉州彝族聚集区亦推行改土归流,设天全州、清溪县、雅州府等县府,至此,滇、黔、川改土归流得以实现。
广西土司在四川、云南、贵州推行改土归流时,纷纷敛迹撤兵,不敢妄动。雍正八年,鄂尔泰在出兵征讨思陵州等地叛乱后,在广西全境改土设置府、镇、县,一些土司纷纷归降,广西局势遂定。
其他一些地区,如湖南、湖北等地土司、土舍,本就与地内接触较多,在此之前又经历了一段“流土并治”的时期,因而改土归流并没有经历大的战斗,至雍正十年左右,清廷大体上在滇、黔、桂、川、湘、鄂等六省的广大地区基本上实现了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清政府在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的基础上,为巩固胜利成果和加强对该地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善后措施。
首先是改土归流后,对土司本人,视其态度分别给以不同的处置,对于个别罪行昭著、对抗朝廷者予以严惩。对于到任的流官,清政府加强对其选任和监督考查,如有不利于地方安定立即撤换或治罪。同时,在新改流地区,实行统一税收政策,一般少于内地;其次,进一步丈量土地,鼓励土民屯田垦荒,并在改流地区大力兴修水利,蓄水灌田。再次,在改流地区大力开发水陆交通,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使内地汉族的一些先进生产经验和技术纷纷传人,促进民族融合。
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的大规模实现,虽然必然伴随着民族压迫的因素,但打击和限制了土司割据势力,加强了中央和西南地区的联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客观上促进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雍正在经营西南的同时,没有忘记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下的西北。
康熙平定噶尔丹叛乱时,噶尔丹侄策妄阿拉布坦曾偷占伊犁,立下功劳,受清廷嘉奖。但后来,策妄阿拉布坦却觊视西藏,派兵进藏,被平定。西藏顾实汗之孙罗卜藏丹津承袭亲王爵,其兄弟多被封为贝勒、公等不同爵位。顾实汗子孙势力复振。按说罗卜藏丹津应该感念清政府恩德,但他却仗着自己是青海和硕特蒙古中唯一的亲王,素以顾实汗嫡孙自居,企图有朝一日能恢复和硕特部对西藏的统治。正当他不敢轻举妄动之际,康熙突然去世,威震西北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禵被其兄雍正新君调回软禁,觉得有机可乘,于是暗中勾结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夏天阴谋发动叛乱。
针对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一面派驻西宁的侍郎常寿去罗卜藏丹津驻地宣布谕旨,令其“罢兵和睦”,一边命川陕总督每羹尧办理平叛军务,准备用兵。
罗卜藏丹津不但不听劝告,还诱禁了常寿。然后,对西宁府周围的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与此同时,罗卜藏丹津还与西宁附近塔尔寺大喇嘛勾结,煽动教徒反叛,一时叛军势力大增。
消息传到北京,雍正见招抚不成,遂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谕令驻西北的平逆将军延信,边防诸大臣皆听年调动,又任命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
年羹尧受命后,立即进驻西宁,分兵把守巴塘、里塘、黄胜关等地,截断叛军人藏通道,令靖逆将军富宁安屯兵吐鲁番和噶斯泊,断绝敌兵与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的联系。一切布置就绪后,年羹尧下令向叛军驻地进攻,罗卜藏丹津见状开始害怕,送还常寿,请求罢兵。雍正谕令年羹尧坚持武力平叛。年底,蒙古各部协从反叛者十余万人降清。雍正二年,岳钟琪先后平定了郭隆寺、郭莽寺、石门寺、奇嘉寺等喇嘛的叛乱。罗卜藏丹津尚负隅顽抗在柴达木。年羹尧调兵二万余人,四面会攻。岳钟琪率兵五千进攻柴达木,敌军一触即溃。罗卜藏丹津衣着女装逃往准噶尔。岳钟琪率兵穷追不舍,俘获罗卜藏丹津母亲和妹妹,斩敌八万余,俘敌数万,缴获大批驼、马、羊、牛等物。至此,西北边疆叛乱闻岳钟琪名即怕。
不久,年羹尧派兵清肃叛军余部。战争结束后,年羹尧先后提出《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和《禁约青海十二年》,主要是整饬蒙古各部、抚治藏民、整顿青海各喇嘛寺院,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人民生活,派驻军队,修建城堡,建立卫所等一系列善后措施。雍正大部分准奏,命奋威将军岳钟琪领兵四千驻西宁,招绥诸部。
然而事情还没有就此了结。罗卜藏丹津率二百余人逃到准噶尔,被策妄阿拉布坦所接纳,清政府屡次派人索要,但被其拒绝。清政府与准噶尔一时呈相持状态。
1727年(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长子噶尔丹策零袭父职。雍正认为这是可乘之机,雍正决定用兵。他用了二年时间解决军需,改良部队的战斗力,以应付擅长骑射的准噶尔兵。雍正七年,雍正发上谕,历数其首领罪恶,准备用兵。廷议时两派争执不下,雍正遂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领八旗兵六千、车骑营九千,蒙古诸部八千共计二万余人为北路军营,屯兵阿尔泰山,命三等公、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屯兵巴里坤,为西路军,约定明年会攻伊犁。
清兵出师后,噶尔丹策零即探知岳钟琪率兵二万出哈密,于是派人假称罗卜藏丹津谋杀噶尔丹策零被擒,欲将他解送给清政府,岳钟琪将情况上报雍正帝,并提出对其诚意的怀疑。
雍正帝以为大势已定,遂召两路大军主帅回京,谕令噶尔丹策零“请封号,所有属下悉编旗分佐领”。
策零乘岳钟琪返京之机,发兵二万,进攻清军,清军毫无防备,被准噶军大败。雍正帝据此对岳钟琪产生怀疑,认为他领兵三万却不进兵,主张坚壁防守,似有异心,遂派人监视和牵制岳,这大大打击了以岳钟琪为代表的汉人将领的积极性。
1731年(雍正九年),噶尔丹策零探知西路军牲畜缺乏,不能组织有效进攻。遂派敦多布领兵三万,进犯傅尔丹的北路军。傅尔丹虽勇却寡谋,中敌诈降之计,率一万人轻装前进,被准噶尔军包围,经激烈战斗,大败而逃回科布多,和通绰尔一役以清军惨败告终。
消息传到北京,雍正为掩饰失败,言词饰过。命顺承郡王锡保为靖边大将军,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继续屯兵科布多。
噶尔丹策零自和通绰尔大胜清军后,进一步滋长了扩展势力的野心。但时有岳钟琪坐镇西路,准噶军未敢轻举妄动。当傅尔丹失利和通绰尔时,岳钟琪出兵乌鲁木齐,杀敌甚众,使乌鲁木齐附近敌军纷纷迁徙。十年,噶尔丹策零以六千人进犯乌鲁木齐,岳钟琪命副将石云倬断敌后路。但石行动迟缓,结果纵敌而去。岳弹劾石贻误战机,结果雍正反责备岳钟琪,大学士鄂尔泰也弹劾岳钟琪身为大将军,专制边疆。雍正偏听偏信,削岳公爵及少保,降为三等侯,仍留总督衔。后将岳召回京城,指责他政令不一、不纳善言、刚愎自用等。遂改查郎阿署理宁远大将军印,将贵州巡抚张广泗定为副将军,西路大军统帅权由汉人转到满人手中。
1732年(雍正十年),噶尔丹策零亲率大军,由北路入侵,傅尔丹再败于乌逊珠勒。八月,准噶尔袭击喀尔喀蒙古中策零部。其部首领策零亲率蒙古军两万,追击噶尔丹策零败兵至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本可一举击败准噶尔兵,生擒噶尔丹策零,但绥远将军马赛尔却不出兵截其归路,结果虽其属下私自开城追击,但时机错过,噶尔丹策零等贼首都已逃遁。
光显寺大捷后,雍正封策零为超勇亲王,屯兵科布多,经理军务。斩马赛尔及阻挠出击的都统李林于军中,削傅尔丹官爵,罢锡保定边大将军。
西路军自张广泗受任后,局面有所改观,且战争已进入尾声。
噶尔丹策零自光显寺大败后,无力发动进攻,遂派人请和。雍正也看到师久无功,便于1733年(雍正十一年)宣布暂停进兵,在征求策零查郎阿和庄亲王胤禄等人意见后,派人前往准噶尔议和,但议和涉及准噶尔与喀尔喀蒙古牧地问题,直到六年后方才达成协议,以阿尔泰山为界,此时已是乾隆四年。
雍正朝西北两路用兵准噶尔,实际上是以失败告终,没有达到目的,这里主要是作为最高指挥者的雍正帝决策失时,调度无方,尤其是对有勇有谋的岳钟琪先用后疑,继而罢贬,实是一大失误,虽起用能征惯战的张广泗,战争却已进入了尾声。但虽雍正朝用兵西北无果,却也起到了扼制准噶尔的作用,为乾隆一朝最后解决准噶尔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雍正继康熙后进一步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同时,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怎样登基称帝的,没有忘记为争夺皇位而兄弟纷争的血腥历史,所以在即位之初,在残酷无情地打击诸王兄弟势力巩固皇位的同时,为避免在自己一朝重演储位纷争的惨剧,决定确立密储制度。
雍正元年,雍正即位之初,即在宫中召见总理事务王公大臣、九卿等要员,晓谕臣下:圣祖仁皇帝托付江山与朕,不能不从长计议。当年仁皇帝为二阿哥之事,心身忧瘁。今朕诸子尚在幼年,建储一事,必须谨慎。但既然圣祖托付江山,身为宗社之主,不能不防患于未然。现在朕特将建储一事写成密诏,藏于匣内,放在乾清宫正中世祖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这是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测。诸王大臣都应知道这件事,或藏数十年也未可知。
这样,一种非传统的秘储制度诞生了。宣布完谕旨后,雍正又象征性地征求隆科多等人的意见后,将书好的锦匣藏于“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雍正早在当皇子时期就熟读史书,通晓各朝历史,尤其对本朝几代皇位之争深有感触,同时又得到乃父康熙帝晚年欲秘密建储的启迪,于是在即位之初便采取了秘储制度。
为缜密起见,雍正帝在藏锦匣于“正大光明”匾额的同时,又书同样内容的传位诏书放置他经常驻跸的圆明园内,这一诏书存放的地点更为隐秘,议政王公大臣、九卿等均不知晓。直至雍正八年他身染重病时才将存放诏书之事私下告诉了大学士张廷玉,十年,又将此事告诉了大学士鄂尔泰,除此二人外,别人皆不知藏诏之事。
雍正八年,雍正帝身染重病,不久,病势虽有所缓和,但一直未痊愈。
1735年(雍正十三年),享年五十八岁的雍正帝于八月二十三日子夜死去。关于雍正帝的暴亡,这里有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雍正朝大兴文字狱(后文将详述),其中尤以清初著名学者吕留良一门受害最重。因吕留良著述很广,门生颇多,雍正兴文字狱时将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的门生多被杀戮或流放,吕另一儿子斩首,其余亲淑弟子被大量流放、充军。吕留良有一女名吕四娘(可能未必是其真名)。自幼读书习武,谙熟武术,近代许多演义小说中均推吕四娘为岷山派(武术中一个派别)始祖。吕四娘在几次入宫刺杀雍正未遂后,经过缜密筹划,于1735年(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偷入大内,寻得雍正寝宫,将其刺杀。
这是民间传说,虽流行颇广,但史证不足。与清朝三大疑案(即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顺治帝出家为僧、雍正夺嫡)一样,诡秘莫辨。
由于雍正帝事先秘密建储,诏书锦匣,所以在雍正帝去世后,清廷内部没有出现以往的诸皇子相争储位的斗争,其子弘历按遗诏继位,清廷有史以来实现了第一次皇权的平稳过渡。遗诏中,雍正对于亲信大臣鄂尔泰、张廷玉恩赐百年后可享人太庙。弘历登基后,命礼亲王胤禄(即允禄)、果亲王胤礼(即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总理事务大臣,改明年为乾隆元年。十一月,乾隆帝给雍正上尊谥: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为“世宗”。1737年(乾隆二年)三月,将清世宗雍正帝葬于河北易县泰陵,即现清西陵。承前启后的雍正朝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