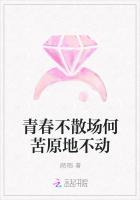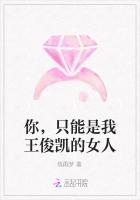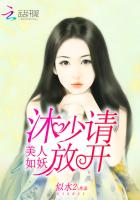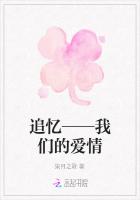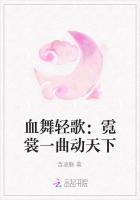自认为“德迈三皇,功过五帝”的乾隆,最不能容忍那些敢于冒犯皇权的士人。如工部主事陆生柟作的《人生论》,里面写道:“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这篇文章虽然不是攻击帝王本身,但它揭示了专制制度的弊端,并指出皇帝本身也将因此受害。陆生柟后来被人告发。乾隆认为陆生柟是“借古非今,肆无忌惮”,以“心怀怨望,讽刺时事”罪,将陆生柟斩于军前。还有,乾隆四十三年,韦玉振为父亲作传,传中有“并赦屡年积欠”等语,而按常规,“赦”字只有皇帝和朝廷才能用,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竟敢冒用,实在是太狂妄了,被判下狱;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惯用语,屈原《离骚》和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于不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里面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马上斩首;大理寺卿尹嘉铨,年过70,自称“古稀老人”,这是根据杜甫诗“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取用的普通名号,不料乾隆也自称“古稀老人”,触犯御名,构成“佞妄不法”的一大罪状。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乾隆制造这类惨案,无非是让天下知道——皇帝的尊严是绝对触犯不得的。
在那时,甚至吟诗作文,也都很容易触犯忌讳,经常是莫名其妙的祸从天降。譬如,“明”、“清”两个字是常用字,但如果诗文中使用这两个字,往往被曲解为反清复明,招来杀身灭族之灾。例如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便是一例。一次,乾隆翻阅诗人胡中藻集,发现有几个句子有比附的嫌疑,就将句子摘出,下令让九卿严审。最后乾隆谕称:“‘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上,是什么居心呢?”乾隆还义形于色地宣称:“夫谤及朕躬犹可,谤及本朝则叛逆耳。”胡中藻的诗本来是一般的咏物抒怀,却被指控为毁谤朝廷,当然处罚就不能轻了。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方芬《涛浣亭诗集》内“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徐述夔《一柱楼诗集》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还有咏正德盃诗“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胡儿)搁半边”;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内“长明宁易得”;李驎《虬蜂集》内有“翘首待重明”,这类诗句都被认为是意在影射,诅咒清朝,图复明朝,构成叛逆大罪。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
在这种望文生义,随意给人定罪的风气下,每一篇诗文都随时有被引申曲解而得罪的可能。礼部尚书沈得潜作诗《咏黑牡丹》,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认为是影射满清,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而指为逆词,沈得潜被刨棺戮尸;江苏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因为写《记梦》一篇,里面有“若姓氏,物之红者”的句子,红者朱也,以“显系怀念故国,实属叛逆”,罪,受大刑;江西德兴生员祝廷诤作《续三字经》,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被认为是毁谤,按“大逆律”戮尸,他的孙子将诗默写保留,也被斩首,家属被连坐,流放了许多人;另外有些诗句如“发短何堪簪,厌此头上帻”被说成是反对薙发;“布袍宽袖浩然巾”被说成是反对清朝服制;“天地一江河,终古自倾泻”,被说成是希望天下大乱,因为天地是平坦的,怎么会倾泻;有人因遭风灾,米价昂贵,表示感叹,写《吊时文》,被斥责“生逢圣世,竟敢以吊时为题”;还有因“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诗句所造成的大狱,都是因乾隆疑心汉人嘲讽满清而造成的著名案件,统治者的多疑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而最为荒唐的是,乾隆时的文字狱,有许多不仅说不上真正的反清思想,其中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只把乾隆的年数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短命,罪大恶极,结果,智天豹被处死。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的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实,就像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说的,“原是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不好,哪里有什么讥讪诽谤呢?乾隆朝的文字狱很多是这类莫须有的冤案。
清朝对文字狱处理之严酷,常常不仅仅是累及亲朋好友,如果在哪里发生了重大文字狱,当地的官员也要以“失察”之罪论处。因此,一旦发生案件,官吏们十分重视,不敢有丝毫疏忽,整个统治机器立刻全速运转起来,捕人抄家,四处搜查,如临大敌,株连宁多勿少,处理宁严勿宽,惟恐被皇帝认为是包庇罪犯,办案不力。刘震宇献《治平新策》,“感颂圣明,尚无悖逆诽谤之语”,不过其中发了些迂腐的议论,本来没有什么治罪的口实。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刘震宇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处罚得很重了,可乾隆还觉得判的太轻,将刘震宇马上处斩。并对范时绶大加斥责,认为他不知大义,给予惩处。10年以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歹去,乾隆还大发雷霆,说“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江苏发生了殷宝山案,乾隆责问“该地方官平日竟置若罔闻”,大骂总督、巡抚等“所司何事,应得何罪”,并要彻查司、道、府县各级官吏的责任,一并查处。在这种情况下,文人士子惴惴不安,各级官吏也都心里非常惶恐。
与此相反,在清朝有许多奸人却因文字狱而飞黄腾达。清代大兴文字狱,是出于帝王强化专制统治的需要,而许多奸人却趁此机会推波助澜,借以谋取私利。他们迎合朝廷的口味,以警犬式敏锐的嗅觉,在书坊、私室广为搜寻,精心罗织罪名,稍有一些收获,就想方设法上告官府,甚至直接上奏给皇上,以此来邀功请赏。而这些奸人往往凭借这个达到了目的,升官发财。所以,清代当官的门径,除科举正途和用银子捐买之外,又多了一条告密升官的门径,被人们称为“用人血染红顶帽子”。这类奸人便被称作“文伥”,而“文伥”的最突出典型,就是“庄廷钅龙明史案”的发难者吴之荣。
吴之荣本是一名因贪赃枉法而革职回乡的县官,但他不甘寂寞,总是四处寻找机会,窥测重返仕途的门道。当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庄氏明史,发现其中有若干触犯清廷的内容,歪心一动,感觉自己机会来了,于是便以此来要挟庄廷钅龙之父庄允诚,庄允诚根本就没搭理他。吴之荣又一向嫉妒乡绅朱佑明富有,就诬蔑说朱佑明是刊印这本书的资助者,但朱佑明也没有理睬他。吴之荣见朱、庄二人都不受其讹诈,便恼羞成怒,向江西巡抚和知府控告。因为在这个时候,文字狱还没有盛行,吴之荣的告发也没有引起重视,地方官没有给上奏。吴之荣怀恨在心,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直接进京上奏朝廷,终于引起了骇人听闻的“庄史案”。不仅庄家全都被杀,连被诬陷的朱佑明还有他的5个儿子全都被凌迟处死,知府谭希闵等地方官也处以绞刑。而吴之荣却因为这个案子升官发财,没收朱佑明的财产都赐给了他,后来官升到右全都。
“戴名世《南山集》案”的告发者赵啐乔,本来不过是都谏小官,因为“戴名世案”告发有功,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升到左都御史、户部尚书。“吕留良案”,是岳钟琪首先告发的。他作为一名汉人而官升到总督,在清代前期是独一无二的,本来已受到满官的嫉恨,但因为在“吕留良案”一事的处理上,岳钟琪表现了对皇帝的“忠心”,赢得了以猜忌刻薄著称的雍正的青睐,这样,岳钟琪在仕途上屡次化险为夷,直到乾隆年间仍然当着封疆大吏。这都是朝廷对告密者给予的特别恩惠。
乾隆时期文网就更加严密了,皇帝和朝廷对文字吹毛求疵,动不动就施以严酷的刑罚,这样,以文字诬陷的奸人更是应运而生。他们或者因为与别人有仇,或者因为贪得别人财产,或者因为家族内部、家族之间的争执,便从对手的诗文中苦心搜求,摘出“谤毁语”、“犯上语”,呈报官府,加以陷害。而官吏们鉴于“庄史案”地方官未奏被绞,当然凡遇到文字案都加重处理,有的明知是冤案,也昧着良心重判。这就导致了社会上的诬告之风更加盛行,闹得人心惶惶。这种情形,引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恐惧,但却敢怒不敢言。乾隆皇帝本人也意识到这样的风气不可大长,他针对当时挟嫌诬告者说:“动于语言文字间,指摘苛求,则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诬诈。有司不察,辄以上闻,告许纷繁,何所不至,迨至辨明昭雪而贻累已甚。此等刁风断不可长。”乾隆虽然有这样明智的话,但在实际行动上,却不断纵容用文字诬告的奸人,使文字狱在乾隆一朝发展到大大超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程度。一些明智的大臣也看到了这类作法的危害,曾上疏劝阻。例如乾隆时的御史曹一士曾经上疏,他从清朝的长治久安着眼,在文中将清代各类文字狱的荒谬性,一一委婉地加以剖析,并指出了频繁地兴大狱,必然导致小人借机报私怨,使天下互相诬告不休,这是不利于朝廷万世基业巩固的。但这些劝阻起不到实质性的作用,因为清朝需要用文字狱来恐吓知识分子,绞杀异端。
直到18世纪的80年代,大约1782年以后,文字狱才较为放宽。这主要是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清朝统治动摇不稳。清廷连镇压武装起义都来不及,顾不得在文字上吹毛求疵,无中生有。同时,统治者放松文网,以此缓和矛盾,希望拉拢知识分子,去共同对付下层人民的反抗。这时,乾隆帝对文字狱的态度有较大的改变。如1782年广西抄获回民经卷书籍,“语多悖逆荒唐”,照以往贯例会严厉追查,治以重罪。但这时甘肃的回民起义刚刚镇压下去,清廷不敢因文字的缘故,再激起回民的反抗。所以乾隆说:“书内字句,大约鄙俚者多,不得竟指为狂悖。此等回民,愚蠢无知,各奉其教,若必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嗣后各省督抚,遇有似此鄙俚书籍,俱不必查办”。显然,像这样的案件,如果都要彻底查究的话,势必是案积如山,株连广泛。在人民已拿起武器,纷起反抗的时侯,清廷不得不稍稍收敛起淫威,对文字犯罪,从宽予以发落了。
有些清朝官员仍乾隆中期的成规,对文字苛求挑剔,乾隆帝为了要缓和社会矛盾,迅速扭转苛求的风气,对这些官员进行了训斥。乾隆四十七年,发生高洽清《沧浪乡志》一案,置湖南巡抚李世杰签出书中的所谓“悖逆不法字句”,其实都是望文生义,罗织罪名。乾隆指出:“书中如‘德洋恩溥,运际升平’等语,乃系颂扬之词,该抚亦一例签出,是颂扬盛美,亦干倒禁,有是理乎?书内如此等类,不一而足。各省查办禁书,若俱如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此事总因李世杰文理不通,以致办理拘泥失当如此”。又说“李世杰任听庸劣幕友属员,谬加签摘,…滋扰闾里。若办理地方事务,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李世杰挨了一顿臭骂,其他官员也不敢再苛求过甚了。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仅见记载的就有108起之多,而且三朝的发展趋势是愈演愈烈,到了乾隆年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竭尽妄意引申、构陷人罪的能事,株连无辜,极其残酷,导致冤狱遍布全国。这一切,都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是清朝残暴的阶级压迫、民族压迫造成的必然恶果。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这种文字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后果,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已在东南一带滋生,同时,又因农民战争的沉重打击,出现了一个“天崩地裂”的局面,由此而来,在明清之交,具有启蒙精神的社会学说,带着若干近代色彩的自然科学,都有所萌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可以和战国时代相比似的繁荣时期。这是一个人才辈出、硕果累累的时代,在16、17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启蒙大师,自然科学涌现出《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杰作。就当时中国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看,与欧洲同时的文艺复兴相差不远。但遗憾的是,此后欧洲文化日进千里,而中国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束缚,由于文字狱等高压政策的实施,启蒙文化发展的道路被残暴地切断了,民主和科学的精神遭到扼杀,广大知识分子再不敢谈国事,一转身钻进了故纸堆里,埋头古籍的考证和整理,像龚自珍在诗中所写的那样“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中国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对此,梁启超曾论述道:“凡主权者喜欢干涉人民思想的时代,学者的聪明才力只有全部用去注释古典。”又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更尖锐地指出:“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这也正是清代统治者所希望达到的目的,他们不愿让知识分子过问政治,如乾隆曾著文说道:“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范,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吕,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且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帝王不希望知识分子“以天下治乱为己任”。这样就使清代的思想学术出现了畸形发展,主宰人们头脑的思想是统治者“钦定”的宋明理学,尤其是陈腐、教条的程朱理学,“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倡导的启蒙思想被一扫而光,人们的思想被牢牢地禁锢住了。学术上出现了“为考据而考据”、“不谈义理”的乾嘉学派。乾嘉学派虽然在古代文化的整理方面做了浩大的工作,有不容忽视的贡献,但就整个中国文化的进程而言,它却是一种病态的发展,延误了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进程。
清代的文字狱,是封建专制制度衍生出的怪胎,是民主、自由和科学的刽子手。17世纪以后,中国文明被欧洲文明远远抛在后面,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这种黑暗、血腥的文字狱所起的恶劣作用,是无法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