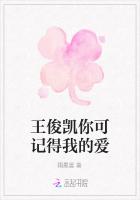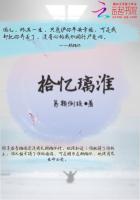寄奴
亦师亦友的马兰录主人王天一先生,年长我十四岁。我认识他可真有些年头了。
大约五十年代,天一老师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我是在他为五泉公园画壁画时认识的。说来,那时我还是个上初中的孩子。
上初中时,我和几个小伙伴特别喜欢看画,尤其爱看画家作画。只要听到哪里有画家画画,那是一趟都不会落下的。听起来,这很有点像眼下“追星族”的味儿。
当时五泉山正在修缮,每修完一处园林建筑,常有画家在墙上留下他们的花鸟、山水画。那一阵子,学生作业不多,学校又是二部制,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隔三间五地泡在公园里头,看画家们怎么在墙上画出和宣纸一样的作品。白灰墙壁上画画,首先遇到的是水墨下流的问题。画家们真是各有各的本事。范振绪老先生往墨里加盐,赵西岩先生一笔不慎水墨下流,他立刻画出屋漏痕的荷梗。顶有趣的是那次北京来参观的孙福熙先生,他一边画一边摇头,嘴里直抱怨他妈的墙头……。
一次,天一老师在东龙口长廊底下画画,他倒简单,用干白扮抹抹墙,又用手帕摸了摸,蘸点水试试墙壁吸水的程度,一笔接一笔画下去,画的是孔雀玉兰,画画得又自然,又一点也不往下流,这很让我们几个吃惊。天一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当时他那么年轻,休息的时候,他问大家,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姓什么,态度十分坦诚。大家好奇地问他:你怎么水墨不流?他告诉我们,画画前我不是作了调查研究,你们喜欢看画画这很好,放了假可以到单位上找我,那里画报让你们看个够。这是我们看画家画画以来,头一回有画家把我们当成了朋友。后来在报刊上我们很注意天一老师的名字。至今我还保留着一页他那时发表的报告文学插图。
我很珍惜这段看画家画画的美好时光。无论是天一老师的友好谈话,还是梁黄胄先生大声诘问:好好看看,‘胃字出头念‘胄……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少年往事,日后连同五泉的壁画,统统被无情的年月劫走了。
时间过去,闹剧收场,为了粮食局几个知青扫尾,我去了成县。人真是秉性难改,去了成县县城,无画可观。工作之余,我就看当地人文景观,看了很使人伤感(杜甫草堂成了猪圈,臭气冲天。吴挺墓周围狼藉一片。西狭摩崖碑上,悬着一个巨大的马蜂巢,马蜂云集,无法走近参观)。日子久了我和成县父老们攀谈,攀谈中才知道这里是天一老师的故乡;才知道天一老师的小名叫“振家”他自小画画就名扬成县百里大山;才知道家乡人民是那么热爱画家王天一,他们把画童小振家绘画传奇化了。编出了一个又一个美丽的传说。一次,我听到一个关于小振家的画让笔客子拿去作广告的故事,迄今我还记得。
故事说,成县原来很穷,孩子们上不起学,就是上了学,家里也很少给孩子们买得起笔墨纸砚,自然笔客子的生意难做。据说小振家成了名扬四乡的小画家后,一个笔客子眼珠子一转,用几支毛笔换了张小振家的画,贴在货箱盖子上,走乡串校逢人便说,小振家的画都是拿他的笔墨画的。不信,你看这就是振家给他画的画。大家看看,画上还真写着这家伙的名字。人经他这么一说,心动了,天下父母谁不想望子成龙……。
故事三言两语,至于笔客子发没发财我倒不在意。这故事很美、很生动,我相信这种事在生活里是经常发生的。它一下子触动了我这颗创伤累累、几近麻木的心。当时我望着陇南苍茫的群山,仿佛看到一个爬山越坡的笔客子,背着天一老师童年的画,背着他那散发着墨香的货箱子,走在这文化底蕴很厚的土地上,播种着古老文化的种子。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想,回到省城兰州,一定去拜访多年不见的天一老师。
回来后,每想去拜访天一老师,心里就忐忑不安,因为他已经是陇上名家,我毕竟人到中年,早失去当年想见谁就见谁那种近似荒唐“发烧”的行径。犹豫再三还是打个电话为妥。我说明来意之后,天一老师快人快语,一“听”如故,来来,欢迎欢迎,我在博物馆后院子有间宿舍,二排,没有围墙的那间,明天中午我等你。
第二天去了,门上贴了张纸条。兰波:我在前楼三楼画画,来了上楼。天一即日。
又是二十年。天一老师从甘肃走向全国画坛,甚至港台、日本……他的声誉可以说盛极一时。我们之间真正认识交往,也成了一部很厚、很有感情的书。每当心闲气静的时候,看看天一老师给我赠送的画,神清气爽,往事历历在目。
自天一老师去北京藻鉴堂专攻花鸟画以来,他锲而不舍,法自然,师万物,不为外物所动,一门心思扑在艺术事业上。他分秒必争,很似李可染先生晚年常书写的“痴思长绳系日”。他不安小成,标准极高,简直给人树立起一个为中国画殉道者的形象。
如今社会糜沸蚁动,人欲横流。他倒能沉得住气,安得下心,在磕头碰脑的建兰市场闹市区,搭起一间“马兰录”竹编草苫的心灵上的小楼,不浮不躁地画他的画、写他的书。一如既往的接待昔日平常的朋友。他一是一,二是二,至诚谈艺,没有什么秘密可隐藏的,画画一有所得,立刻告诉。
他说:孔雀羽毛,绿里泛紫,真复杂,这么看是一种颜色,那么看又是另一种颜色,画起来总不理想。那次在敦煌看壁画你说古人工笔重彩是怎么勾的?许多壁画的底稿,不用墨,是用当地的红土,然后再画上青绿,时间长了绿里见红颜色,很丰富。回来我反复试验也用赭红画底色,再用青绿罩染,果然好看……。
他说:梅、兰、菊、竹四君子,都是人了画谱的,初学可以,画一辈子仿古有什么意思。画,就要画出自己的面貌。关山月先生用群众容易接受的写实方法,画梅花画得多,突出个俏字就画出了时代精神。我在南方见过梅树,这么粗,花开得让人见了不想走……
他说:北方画水仙花,一个水盆、一头两头,我到漳州、泉州去过两回,那水仙真有看头,一片一片长在水地里、自然成趣……。我不喜欢刀子刻,人为地造型,失去天然风貌,再说用刀子刻,那么好的水仙,怎么下得了手。
每当我离开“马兰镓”,穿过高楼大厦的楼群,常想起郑板桥一枚书画印章“无数青山拜草庐”,如果把“青山”换成“楼阁”,送给马兰篸主人也是很恰当的。
中国有句老话,“画如其人”、“字如其人”,可见人们把人品看得是很重的。对于天一老师的品德,说他实在、宽厚、博大、崇高并不过份。和他在一起,因为你普通,他决不看轻你;你好了,他不追名夺利,利用你;你下岗了,困难了,他鼓励你、帮助你。
前几年我在报刊上见到一幅漫画。两画家背对背画画,你甩他墨水,他甩你墨水。这种事凡有画家的地方大概都有。这多年,我在天一老师背上见过这种墨水,难道他不知道?可他几十年如一日,没见他对谁甩过一次。这品格说他宽厚过份吗?
我当过几天小报记者,理解最深的词是“趋之若鹜”。天一老师没叫我在报上为他写过一个字。他说,我画几年再说,画几年再说。说他崇高过份吗?
一次,天一老师告诉我,你真作了个好梦,许老(许麟庐先生)到兰州来了,明天先生没活动,上午在宁卧庄画画。许老是我久已仰慕的大师。看大师作画,一生能有几回,这可不是“歧王宅里寻常见”,了得!
那天,我不但见了大师作画,竟好梦成真,天一老师代我求了张画,真令人兴奋。看许老作画,让我知道了画中国画,怎么叫放,怎么叫收。在许老笔起笔落中,我仿佛听到了古典琵琶曲《十面埋伏》的律,感到了丝竹管弦的韵,看到了墨如古玉,领略了老人家震撼人的力。当时,许老的录像都不叫甘肃电视台放,用得着我这个小报记者吗?天一老师理解我仰慕大师的心。你去问问世人,虽至亲好友肯把好梦送人吗?我感谢德高望重的许老。感谢天一老师。说天一老师博大过份吗?
天一老师是个好人,太好了,好便成了缺点的那种人。这几年报刊上对中国画家的评论很多,溢美、奢侈之词五光十色,实在紊乱了欣赏价值。欣赏是静悄悄的。
天一老师是熟人,我静悄悄地看他的画,看多了。在他的画上,我看到了阳光、清新、天籁真趣、时代精神。
纵观天一老师艺术人生,我想起潘絜兹先生说过的:“画才难得,造就一个画家要有许多条件:个人的禀赋、家庭的熏陶、环境的习染、师友的启导、传统的影响、深厚的修养、非凡的勤奋等等,对中国画来说,还有岁月的积累。历史上许多画家,笔墨精熟,都在老年。”天一老师今年七十五了,巳进入他绘画人生的老年,我期望他衰年变法。待他八十岁,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画展的时候,我相信那将是一次大师级的画展。到时,我会给他送上一束马兰花,表达我对马兰篸主人的敬意。
2000年12月31日兰州
【注】寄奴即刘兰波,兰州晚报记者、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