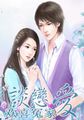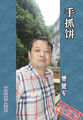5.位置
地理环境是悲壮历史的舞台和背景,大山大江是孕育神话传说的母体。这里的每一段历史,演绎着传奇式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事件;这里的每一条河,每一座山,都笼罩在神秘怪诞的传说中。
这块土地,位于青藏高原的腹地,与西藏交界,与四川康巴毗邻,与新疆接壤,端卧在三大藏地的中心。
这里是藏王松赞干布曾经征战的疆场,又是史诗中的英雄人物格萨尔王那位美貌绝伦的王妃珠姆的故乡,自然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和他们征战的足迹。佳丽们的艳影在人们的口谈中越发妖娆。还有大唐时,文成公主进藏驻足此地,也留下了许多动听的历史传说和人文遗迹。金成公主进藏时再一次踏上了这块土地。这里常遭兵燹之灾,乃兵家必争之地,战事不断,也把这儿的人磨炼得剽悍、好斗、勇猛善战,面对险境无所畏惧。
上世纪初,噶厦政府、西康,还有对此地觊觎已久的马麒,这三方轮番登场,使这块土地常处在动荡之中,没有安宁之日,纷争不断,狼烟四起,生灵涂炭,百姓遭殃。
早些时候,噶厦政府在康巴地区分封了四大藏王——昂欠王、拉斗王、德格王、冷存王,以宗教统治来达到实际的领导。各派佛教寺院寺主由拉萨宗教上层委派任命,那种关系就像老人与儿辈们血脉相连,割舍不断。比如说吧,1896年在反击英军入侵拉萨的战斗中,康巴人的援军骁勇善战,把英军二千人的远征军全部消灭在拉萨市。唯一逃脱的传令兵在写给英国女王的书面报告中说:在喜马拉雅山的北麓,有世界上最强悍的民族,善于短兵格斗,而且是最富有的。他们用奶油(酥油)包和羊毛捆做成堡垒,不断滚动进行近战,使我大英帝国的现代武器失去了威力。其中提到的奶油包和羊毛捆,就是康巴人运上去的。我的外公作为康巴援军曾参加了那次的拉萨巷战。他带回来的战利品是几枚小银币,银币上有维多里亚女王的头像。小时候,外婆缝在我的衣服上做纽扣。
外公常讲起这段往事,那得意的神情不必说,每当我扑进他宽阔的怀抱里听他讲红头发绿眼睛的英国兵时,能感觉到那洪亮的声音是从胸膛里蹦出的,看着外公说到动情处,随下颌抖动的胡须,就知道他的感触多么深,以参加过那次战斗为荣。标榜他作为康巴汉子的勇敢,是他终身最得意的谈资。
因为这次拉萨巷战中,康巴人表现勇猛智慧,拉萨人对康巴人另眼相看。据说达赖和班禅有指令,要优待在拉萨的康巴人。
我的外公很有亲和力,也很健谈,擅长讲故事,人们常围着他想听到有趣的事,打探一些信息,或对一些问题产生疑惑时找到外公,寻求答案。好多我未出生前发生的事都是从他的故事中听来的。
不论是夏季的骄阳还是寒冷冬天的暖阳里。外公的故事总是被阳光熏暖,发酵,使人们痴醉在他的故事里。我常常坐在外公的膝头,聆听他绘声绘色的故事。他的嘴巴是故事的口袋,诨号叫“卡贝扣给”。(卡贝,故事;扣给,口袋)
可我天真地认为,外公的胡子里藏着讲不完的故事,经常是趁其不备。揪他的胡子,总觉得揪一把,故事从胡子里捋出一把来。好多事情得益于外公的讲述,至此我可以把它们连成故事讲述。
一次,外公背着我转对面的大山。
“诺布,这是座神山,转山要从左到右按顺时针方向转,记住。你想知道这座山为什么是神山吗?外公给你讲一段吧。”
我兴奋得忙从外公的背上滑下来,牵上他的手,听他讲:
“很早以前,这座山不存在,这里是一块平坦地,显普菩萨在巡游名山时,法眼望到绿草如茵鲜花怒放的殊景,骑着他的宝骑大象驾临,来点化,显普菩萨沉醉于其美景,大象看到有一孔地眼,冒着一缕幽幽的青烟,袅袅升上天空,大象很有灵性,预感到危险的存在,嗅出这股青烟,是祸害生灵的毒气,为了显普菩萨和众生,大象毫不犹豫地卧在了地眼上,用它的肚腩堵住了青烟,它坐化成这座山。你看,整个山形,像不像是一个大象卧睡的姿态,那是象头,那是象身,还有这是象尾。”
依照外公的指点,我似乎看出这山确实像一头卧象。
我与外公绕着这山转了三圈,外公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都是关于四周山的传说。除了神话传说,外公还讲述历史事件。只要是跨越了今天的事。在外公口里都是故事。
回来的路上,外公指着东面山头的残壁断垣说:
“诺布,看见了吗?山头的矮墙,是碉堡的遗址,你想听外公给你讲吗?”
一听是碉堡,我的好奇心提起了我立马吊住外公的脖子,祈求道:
“想听,想听,你快讲啊!”
外公坐在土坎上,把我放在他的膝头上,又开始下一轮的讲述。
那是1913年,北洋政府时,就是银元上铸有头像的那个老爷,他当皇帝时,出了一件怪事。
我们这地方直属甘肃管辖,当时还没有青海省,只有西宁县。这地方领属权模糊松懈,周边的虎狼都有咬一口抑或吃到口的野心。有一年,北洋政府的一位驻藏大臣,取道昌都去拉萨,经过这儿时,碰上甘肃和西康争夺这地方。甘肃向上呈报这地方时译成一种地名,而那位驻藏大臣上报此地名时,又译成另一种地名,因译音不同,引出了事端,闹出一段笑话。颟顸无识的袁世凯竟作出了把同一地方归西康和甘肃的批复。就像把一个女儿许配给了两家人,这两家为娶到媳妇,打得不可开交。当时还属甘肃的西宁宣尉使马麒乘此机会派兵进驻,与西康军各执一词。1914年北洋政府为了解决争端,派了勘界团到实地调查,才平息了此事。
明令我们二十五部族仍归甘肃管辖,西康军撤出,不用向西康缴纳赋税。原本对这块肥肉虎视眈眈的马麒军队,从这时开始索性赖着不走了。
当时马麒只不过驻有一两个连的兵力。哪像现在,马家的兵多如牛毛。随着马家的野心膨胀和贪欲,盘踞的兵力逐步升级,这个不请自到的神,进来以后,给这方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1932年,西宁县,已升格为青海省。水涨船高,马家人胃口随之变大,与噶厦政府展开了争夺战。
马麒的人不到四百,实在难以抵挡,去电求援。
噶厦政府命令西康的藏军从东面打进去。一时间,这里战火又起,危机四伏。
这时,马麒已死,他的儿子马步芳大显身手,派了一个旅的骑兵前来与六千多藏军在通天河一带展开激战,经过近一个月的拉锯战,最后由达赖喇嘛出面调停,藏军撤出,结束了这场争夺战。
从此以后,噶厦政府失去了对这儿的制约。此地就掌控在马家的手里。
据外公告诉我说:
“藏军的战斗力很弱,军纪松散,平时很少练兵。藏军出来征战。官兵均携带老婆孩子,出征时托儿带女,行军速度缓慢。等到战斗打响了,有了伤亡用毛毡把伤员抬下来,老婆孩子在后方围着伤员和尸体哭成一片,那情景非常悲惨。女人们呼天抢地,儿女们伏尸喊叫,战争让女人孩子们离开,可偏偏他们的战争里让女人和孩子紧随其后。”
外公还说:
“藏军修筑的工事,不堪一击,他们在各山头修了防御工事,修了碉堡,挖了战壕,碉堡是用木头加石头垒砌的,民团们乘着黑夜用皮绳套住碉堡,几个人在山下齐心合力一拉,碉堡就被稀里哗啦拉下了山。”
外公指着东面山头的废墟说:
“看见了吗,那就是当年藏军的碉堡。”
是啊,与其说是战争,还无如说是一方对一方的杀戮,藏军不懂战略战术,只是猛冲猛打,看到战场上占优势,穷追猛打。一旦失利,作鸟状散,各自逃命,有勇无谋,白白送死,伤亡惨重。毕竟藏军的传统战术,与马家军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无法抗衡。
外公每次讲到这儿,忙从怀里掏出念珠,口里念念有词,为亡灵祈求他们的在天之灵得以安息。
当时战事的惨烈程度,外公每每提起,都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正因为这块地方位置的重要性,历史演进的时光隧道步步走近我们,使我们一并共呼吸、共命运、共感受、共记忆那段风雨飘摇的历史。下面发生的部落之间的纷争,有的是我从外公口里听来的,有的是人们转述的,还有的是我自己经历的。
6.富有的百户
这个富有的百户,是人们挂在嘴边谈论的话题,是羡慕富贵的对象。六岁那年,我第一次去富有的百户家做客。懵懂的我,是在穷困的环境里成长的,到百户家,是我第一次开眼界,转换视角,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黑暗的心仿佛透进一束亮光,在我的心脏击穿了一个小小的孔。从此,文明在我心里落下了种子。
六岁,我踏进了这扇门。
六岁,我看到了新奇。
六岁,我开始有了物质以外的向往。
六岁,我的天眼洞开了。
六岁,我捕捉到了文明的影子。
那个有两个轱辘满地跑的脚踏车,还有那个魔鬼的眼睛,把遥远的山路领到你的眼前,让人感到惊怵的望远镜,以及能像星星月亮发光的手电筒,这一切充满魔力的东西,让我跌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这个富有的百户占有四个优势:祖上显贵,属地多样,既是活佛寺主,又是百户,真正体现了藏区政教合一的特殊制度,而且免征赋税徭役。
这个部落的百户,很有经济头脑,他知道钱能生钱的道理,又懂经营之道,拥有一只非常庞大的商队,行走在印度及拉萨、内地,是当时康巴地区一带最大的商户,他的管辖区又是宗教、文化、贸易的核心。
他就是百户昂旺。胖胖的圆脸显得既和善又有亲和力,没有别的头人那种凶猛霸道之气,是个文质彬彬的谦谦君子。
父亲和昂旺百户交往多年了。每当草原上羊羔花初绽,春寒料峭时节,父亲会受到昂旺百户的邀请,去他家,切磋学识,探讨佛教哲学,交流研习佛经的经验。
昂旺活佛是一个海纳百川、眼界开阔的开明人士。他住在僻远的地方,但不孤陋寡闻,善于接受新生事物,不保守、不墨守成规,喜欢结交各类人物,上至达官贵人、宗教僧侣,下至乞丐、平民百姓,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和善仁慈、达观通脱。
父亲常说:
“听昂旺活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一点不为过。”
同时,他们的经历和信仰使二者意趣相投,都是一只脚踏在红尘过着世俗烟火的生活,一脚踩着空门虔诚地守护信仰的神圣。父亲还俗,昂旺活佛娶妻室。
六岁那年我第一次去昂旺活佛家。父亲从学校马厩借了一匹雪青马,大清早上路,我骑在马上,父亲像个脚夫牵着马,只有到渡河时,父亲才肯上马,过了河又下马,他说:
“马不能累着,否则一天的经白念了,罪过。”
一路上,父亲早就叮嘱我去做客的规矩和礼数之事,我一一应诺了父亲的条件。
太阳偏西时,我们到了目的地。只见整个村落处在四边环山的坦地上,由西向东,一条溪水流来,寺院掩映在一片绿荫中,十二座白塔塔身婆娑,经堂屋顶铺着琉璃瓦,金碧辉煌,做工考究,绛红色的寺院墙,白色的塔,交相辉映,铃铎叮珰,经堂的窗户上镶着大块的玻璃,让我感到惊叹好奇。不像其他寺庙那样,经堂大而深,光线昏暗。我家的玻璃只有阿妈那块小圆镜,他们的玻璃装在窗棂上,我认为这是对玻璃的奢侈使用。我和父亲在佛龛前,拈香膜拜,拜遍每尊神像后,去了寺院下方百户的庄园。
昂旺百户家是三层土楼的四合院,底层是仓库,第二层是厨房,佣人住在西南面的下层,上面是他们的经房,客厅,客房,卧室等。后院是禁地,据说是钱库,戒备森严。
侍奉他们的下人全都是沾亲带故的,前院里住的是干粗活的下人,一些是从其他部落投奔来的属民。他们主要是为昂旺百户家种地,百户家有上百亩田,这里地处通天河河岸,地势平缓,气候温和,每年都有好的收成。
侍奉百户小女儿和百户太太的女佣就有十四人之多,都是尼姑,并且都是与百户家有亲戚血缘关系,她们是在内院走动的,活儿轻,有很充裕的时间拜佛诵经。
昂旺百户平时袈裟从不离身,一副僧人的装束,平生好善施舍,抚恤顾惜,他一生就抚养了九十多位孤儿,都把他们当作儿女看待,送他们走上了人生之路,有的出家当和尚,有的成为学者、高僧,有的经商,有的放牧,有的种田,都过着自食其立的生活。而他本人生活过得很俭朴,平易近人,深受属民和信徒们的尊敬爱戴。
百户家有个习惯,那就是晚餐很正式,一家人必须聚在一块吃,顺便谈论一天的事务,交流信息,谈天说地,联络亲情。吃饭入座的位置是有讲究的,正上方是百户的座位,两边是家人,围坐矮几,席地而坐,铺有地毯,(地毯色泽艳丽,图案奇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波斯地毯)。油灯初上时,家庭成员都出场了。大儿子索南是他父亲寺里的一个小活佛,已十六岁,帮助父亲处理寺里的政务和家务,坐在活佛的侧旁。小儿子生格,是拽着他阿妈的衣袖进来的,坐在他阿妈的身边,说是比我小一岁,坐在我对面,先是睁大眼睛看着我,盯着看了一会,他脸上的表情开始丰富起来,先是讨好地笑了一下,后来又做起鬼脸,看我没有反应,又用语言挑逗:“喂,你是谁?”
我怯生生低下头,他更得意,更大胆,处处表现一种优越感,抱住她妈妈的头耳语一番。我知道,他是在向他妈妈告状,他看到了我的这身衣服,这是学校发的军装,经过父亲之手改版的,不算正规,但大小合身。当然比起他,我的确穿得寒酸,我的自卑心在作祟,不敢抬头对视这个顽皮又自以为是的家伙。
只听见他阿妈大声说:
“他是嘉喇嘛的儿子,人家会说汉话,会写汉字,你会吗?”
我知道,这是说给我听的,在表扬我,给我树立信心,给了我找回自尊的契机,同时也向她的儿子,把我作了个介绍。听到这话,我的自信又战胜了自卑,抬起头来,直面对视生格,心里想,这会该轮到他羡慕我了。
大家还没有进餐,似乎是等待重要人物的出场。父亲和昂旺活佛边喝茶,边交谈,大概他俩的话题离小孩们太遥远,太深奥,除了他俩谈兴正浓,其他的人没兴趣,甚至不知谈什么,大儿子索南却很专注,静静地听两位长辈交谈。
我与生格,惯用孩子的方式开始想认识对方,无非是目光对视,做做鬼脸,用肢体语言来交流。
隐隐约约听到走廊里响起脚步声,随着愈来愈近的脚步声,我猜想,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出场呢?
只见三个尼姑送进来一个十来岁左右的小尼姑,披着红袈裟,剃了发,拿着念珠,口中还念念有词,轻轻地走过来,坐在了生格的旁边,她只是顺着眼,我们这些陌生客人,似乎在她眼里不存在,不处不惊,从从容容,似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她的这些举动,让我的好奇心又加了砝码。富人家的人,跟我们一般人家太不一样了。
她一坐稳,众仆人就开始端菜上饭。看看要吃饭了,她把手里的象牙念珠套在了项颈上,像一串珍珠项链,使她显得更加端庄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