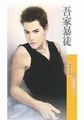郑洞国闻知曾泽生率部队已开出长春,六十军的防区已交给了解放军后,颓然失色了。他已不是躺在沙发上,而是直直地挺在沙发上。往日,他还可以用烟和酒来消愁,如今,再好的烟酒,对他也是索然无味了。他拚命地按电铃,侍卫来了被他轰出,副官来了被他骂走,弄得上上下下这些人不知该怎么好,他光按电铃不说话,这哑谜叫人难猜。良久,郑洞国似乎才清醒过来,自言自语地说:
“难道杨友梅已经死了?!”
侍卫和副官这才知道他原来是要找参谋长。副官赶紧上前报告:
“司令不是才派参谋长到李军长那边视察防务吗?”
“我是叫他去了,可我并没有叫他一去就不回来呀!”郑洞国怒冲冲地说。
“报告司令官,参谋长从这里出去,还不到半个钟头呢!”副官说。
“半个钟头还少吗?”郑洞国似有些神经错乱了,副官要侍卫赶忙给他拿湿手巾。
侍卫把手巾拿来,郑洞国乖乖地躺下了。
窗外传来轻轻柔柔的广东音乐。郑洞国开始还认真地在欣赏,突然他感觉出来了,这不是音乐,而是楚歌。
“司令官电话!”副官拿着电话筒向郑洞国报告。
“哪里来的?”郑洞国问。
“李军长!”郑洞国还是在沙发里挺着,副官把话筒递过去,他一下子就听到李鸿在骂:“司令官的电话怎么这样难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呀!还这样摆官架子?”
“不是我已在跟你说话了吗?”郑洞国淡然地对话筒说,他不知自己为什么现在没有发火。
“呵,司令官……我还以为是总机在捣乱哩。”听到郑洞国的声音,李鸿的口气显然缓和了下来。
“你不是还害着伤寒病吗?”郑洞国似乎很关心地问。“曾泽生部队这一走,解放军部队这一来,伤寒病已经给惊跑了,我现在正在指挥所。”李鸿颇有责怪他的司令官的意思。
“友梅呢?”郑洞国故作不知地把话岔开。“他也在这里。”李鸿答。
“你们怎么样?”郑洞国真不知说什么好。
“我们怎么样?”李鸿有点儿不耐烦地回答,“先前对面是曾泽生,现在中山路东边是我们,西边和后边就是解放军,真是推开纱窗望,人比月还明。司令官,你说怎么办?还突围吗?只是这条中山路就怕通不过啊!”
“解放军有什么举动?”郑洞国问。“什么举动也没有,就是到处在给我们开音乐会。”果然,郑洞国熟悉而且比较喜欢的《雨打芭蕉》又冲进了房间。“司令官,这种情况,部队还能打仗吗?”
“把窗子给我统统关上。”郑洞国在命令他的副官,也是在告诉李鸿。副官把窗子关上了,李鸿可没法执行,他跟郑洞国说:“开关不在我这里。”
“让士兵闭上耳朵!”郑洞国越发蛮横了。
“耳朵不是长在我头上。”李鸿郑重其事地跟郑洞国嚷,“共军开个音乐会都对付不了,我们还想突围?突个屁!丢那妈!”最后两句是李鸿放下电话筒后说的。此时,电话筒里郑洞国在发脾气下令:“给我把那些奏乐的人通通抓来。”
“司令官真是有点歇斯底里了!”杨友梅多少有点颓丧地说,“李军长,今后长春大计,你要多拿些主意才好呵!”
门外传来士兵的呼叫声——
“冷呵!”
听到呼叫声,高烧还未全退的李鸿,忽然也发冷起来。他的侍卫赶快给他送上皮大衣,他随随便便往身上一裹,跟杨友梅说:
“请上复司令官,就是一街之隔,也要打一下,反正不打是没有出路的。”
“应该这么下决心,我祝你胜利。李军长,兄弟这就告辞回去复命了。”杨友梅说着跟李鸿握手告辞。
李鸿当即就向他的主力师——三十八师下令:
“乔师长,趁共军立脚未稳,全师向他们出击。”
霎时就听到中山路绵长十余里的地带响起轰隆隆的炮声和咔咔的机枪声,间或还有手榴弹爆炸声。
市民开始还以为是国民党军内讧,纷纷逃到地下室和临时挖的防空、防炮洞去躲避。
解放军的战士们端着刺刀,背着炸药,沿着墙根向新七军驻守的防地攻击。尽管新七军还拿着美式武器,可他们的心已经散了,解放军的战士趁势向他们喊话:
“蒋军弟兄,你们是作王耀武、范汉杰?还是作曾泽生?是应该当机立断的时候了!放下武器还来得及,解放军优待俘虏。”
“不用说了,我们都明白,可我们当官的不是曾泽生。”
在督战队的强迫下,新七军攻了一阵,守了一阵,他们失去了一片阵地,人死了上千。
李鸿在指挥所还要下令继续攻击的时候,三十八师师长乔麟闯进李鸿的指挥所。他一进门就把腰上的皮带往桌上一甩,气势汹汹地跟李鸿说:
“军座,这仗可打不得了,一下子就是一千多,三十八师现在没有几个一千多了。”
“真是一千多?”李鸿明知故问。
“这还用说谎?死尸、伤员都在那里明摆着。”师长说罢,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耷拉下脑袋。
“那,再不能继续攻了?难道就让共军踩在我们鼻子上!”李鸿无可奈何地说。
“反正三十八师是无能为力了,我请求——”乔师长站起来了,“我请求军座把三十八师换下来。”
“这是什么时候?嗯?可能换下来吗?”李鸿说时很焦急,他心想:三十八师都要求换下来,那六十一师,五十六师更不用说了,所以他很婉转地跟三十八师师长说:
“乔麟兄,你师暂时就坚持着吧!等我请示了司令官后再定。”
“勉强坚持几天倒没什么不可以,就是共军的音乐会和喊话受不了。”乔师长回答。
“你不会用炮轰它!”李鸿也像郑洞国一样犯起歇斯底里来了。
“轰它?说得容易。我们的士兵爱听,他们不肯打。”乔师长表示无可奈何。
“看来,长春我们是守不了啦!”李鸿长叹一声,当着三十八师师长的面取消了第二次攻击的命令,他自己驱车去见郑洞国。
郑洞国还直挺在沙发里,不过头上顶的已经不是凉毛巾,而是冰枕了。他一边大口吸着烟,一边在看曾泽生给他写的信,看到紧要处,他读出声了:
“……公乃长春军政首长,身系全城安危,为使长市军民不作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省自身,断然起义,同襄义举……”
读到此,郑洞国坐起身来,又躺下,躺下,又坐起身来,长吁了一阵,喟然长叹:
“委员长从黄埔一期就培养我,培养了我一生,官至上将,岂能临危反叛?!”
正在这时,门一推,李鸿闯进来了,他忘记了沙发上坐的是他的司令官,直嚷起来:
“乔麟要求撤下来,司令官,你看新七军还怎么去上阵?”
“为什么要求撤下来?”郑洞国毫无表情地问。
“一攻就伤亡了一千多,他说现时三十八师没有几个一千多了。”李鸿的声音是有气无力的,听得出他是站在三十八师一边的。
“打仗还能不死伤点儿人?补嘛!”郑洞国此时真是在大白天说瞎话,李鸿忍不住又顶撞道:
“别说没人补,就是把长春市男女老少全赶上阵去,他们也顶不了一个连用。单是他们的肚子,我们就包不起。况且委员长已来命令,空投机油短缺……”
“别再提这个了!”郑洞国阻止李鸿再说下去。
解放军的音乐会又开始了,从郑洞国的窗子里传进一曲《昭君怨》。
“丢那妈!”郑洞国只骂了一声,就再不管了,让《昭君怨》的哀怨旋律在他的房间里任意回荡。
“如今之计,走、守、降,是该选一条最后的路了!”李鸿在自语,也是在暗中向郑洞国示意。郑洞国只看了李鸿一眼,没有说啥。参谋长杨友梅以为郑洞国别有打算,顺便说了一句:
“起义,我们是落在时间后面了,而且人家解放军这时也不会要——”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郑洞国几乎要上前去打杨友梅的耳光,但他终于克制住自己。
“起义,是走、守、降中的最后、也是最先的一条路,可惜我们是黄埔……”李鸿说出了郑洞国的心事。
郑洞国至此忽然变得严厉极了,他高声地说:
“再有言‘起义’二字者,按叛逆论处!”
李鸿歪着头看了看郑洞国,杨友梅也把肩一耸,他们深知郑洞国此时此话乃违心之说,所以根本不在乎。
就在郑洞国山穷水尽之时,蒋介石却让当初的东北守将杜聿明送来“柳暗花明”的信息。副官怯怯地禀报:
“杜司令来电,再三问银行大楼楼顶平台能否降直升机?”
郑洞国的司令部设在长春银行大楼,楼顶上落直升机是不成问题的。但他想到10万部队都丢了,自己有什么脸回去?于是,挥笔拟就电文:
“大势已去,只有以死报国。请光亭兄电告总裁,来生再见。”其实,此刻沈阳根本没有直升机,杜聿明心里明白,老蒋不过是玩一个收买人心为之拼命的花招罢了。这对郑洞国这个忠勇之士倒是“歪打正着”,可见蒋介石确实是“知人善任”。
事后,周至柔曾当着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的面,说起蒋介石指挥作战的笑话:
“你们不知道,曾泽生的第六十军投共之后,长春的飞机场已在共军的炮火射程之内,飞机已不能降落了。蒋总统还命令我派飞机去把郑洞国接出来。我赶忙报告:‘长春机场已不能降落。’他说:‘从飞机上放绳子下去把他拉上来!’我再报告:‘我们没有直升飞机。这样不把人吊死了吗?’他说:‘死的你也得给我拉回来!’”
10月17日清晨,长春一切如旧,郑洞国在指挥所里一筹莫展。拂晓攻击没有发动。曾泽生已率领所部六十军全军两万六千余人起义,并且把他们在长春东部的防区警戒起来,断绝了与郑洞国设在中央银行的总部联系。
郑洞国不得不做最后的抉择了。
参谋长及一干人等呆立在他身旁,静待他开口,但郑洞国却没啥说的了。倒不是四面楚歌,插翅难飞,那越缩越小的包围圈又缩紧了一大截;而是心头那几乎难以形容、没法解决的问题,正在使他苦苦思索。
1948年3月间郑洞国奉命去长春,至亲好友没一个赞成。沈阳以北蒋介石只剩四平和长春两个孤零零的据点,在对方重重包围中既不能守、又不能退;更无任何新的因素可以挽回这颓势。郑洞国明白长春不过是迟早的事,此去无异送死。杜聿明、熊式辉、陈诚、卫立煌先后出关,对危局同样打不开局面。
当时郑洞国有两种思想在脑子里打转,一种是根深蒂固地服从命令的思想,感到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一个国民党员应该“与党国共存亡”;另一种是时时浮现在心头的朴素的爱国思想,为什么要用美式武器去大量杀害老百姓?给失尽民心、没有前途的国民党去卖命,值得吗?应该为这种政党去死吗?
同时,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郑洞国不知道,旧的想法强烈地占着支配地位,朴素的良心却深藏于内,不但不敢同他人讲,甚至当曾泽生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白的时候,他还不肯同他讲,他并未向这方面去作进一步的慎重考虑。
现在,这两种想法又冲突起来,而且特别剧烈。郑洞国痛苦极了,寝食俱废。
“报告司令,”参谋长道,“地方已经再一次向我们说,——”郑洞国烦躁地制止道:“我知道,我知道,让我多想想。”
就这样,从17日曾泽生起义起,郑洞国在包围圈中想了两整天,还没作出决定。
10月19日黎明,长春在隆隆炮声中醒来。两宵未合眼、眼睛血红的郑洞国在地图上划上几个“☆”号,表示包围圈又告缩小。
这并不使他头痛,在长春中央银行总部标志上加一个“☆”也在他意料之中。问题是怎样安排自己以及六万左右部下的命运,郑洞国矛盾极了。
“你们,”郑洞国对参谋长等人说,“你们不要催我,让我再想一想——”
“对方——”
“对方由它去!”郑洞国烦躁道,“对方既然欢迎我们,也得让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如果真的同曾泽生一样,那么也不是吃闲饭去的。我们行不行?都得仔细想想。”
时钟已经接近中午,各方的意见也交换得差不多了,郑洞国长叹道:“各位,这两天来,是我生平最痛苦的日子。初来长春时的两种思想,在今天更在剧烈冲突!我可以这样说,顽固的旧思想逐渐被削弱了,深藏在心头的潜意识抬头了。但我们不能不想到:现在放下武器,是不是太晚了呢?”“不不,司令,一点儿也不晚!”
“别忙,让我说下去。不管我内心怎样想,不管我意识怎样抬头,作为一个几万人的部队指挥官,在实际行动上我还在迟疑审慎,没有决定采取任何走向民众的步骤。”
“共产党有他们的政策,不能骗人!”一个师长说,“我们好几个同学都在那边,可以作证!”他抹抹眼泪道:“并不是我没出息,怕死贪生,投降敌人,司令知道,抗战时我也带过花。就是因为抗战时我目击中共的团结抗战的精神,更感到本党那种策略对不起人!对不起黄帝祖宗,对不起子子孙孙。现在联合美国拿枪口对准他们,试问我们怎能安心?在平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穿上两尺半,每个月领饷,算了,可是今天的情形不同,今天我们是死里求生,司令呵,我们为什么还要多心?”
在瞻前顾后、审慎考虑之后、郑洞国作出了决定。他倏地起立,严肃地说:“各位,你们经过这几年的教训,心里头有了一种新的思想,这一点非委员长所能防止,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想二十几年前,兄弟一腔热血,在军阀混战时期跑到广州进黄埔第一期,只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我同军阀血战过,也同日寇血战过,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郑洞国悲从中来,“我怪谁呢?怪命运?不对;怪大家打不过共产党?也不对。共产党形势比人强,这句话倒是说对了,今天有这么一个形势,非要我们换换脑筋不可!我们在委员长领导下,走上了一条和初衷完全相反的道路,我们的确错了,跟错了人,也做错了事……”
众将领人人紧张,脸上泛出罕见的兴奋之情。
“不过,”郑洞国道:“我们不是怕死,这一点无论如何要弄清楚。抗战那些年,我们追随委员长,打败仗的时候多,可是没今天的想法,今天,”他长叹,“形势比人强!”他以拳击桌,“既然到了应该放下武器而且不能不放下武器的时候,那就这么办吧!”
众将官闻言欢呼,但有一名新七军的师长发言道:“司令的决定,我们已等待很久了!不过我也有一些意见。”
“你说!”
那师长道:“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在凤山曾经受过美式训练,我们的部队也是美式配备。我们很多人都感到,日本人当年侵略我们是外患;今天我们国共开火是内战;但事实上并非内战,还是外患!而且我们拿了美国人的枪炮武器杀自己人,替美国军在中国打天下,我们是变相的日本兵,这种事情太惨了!太难过,太见不得人了!”
众将官闻言齐皱眉头,痛苦莫名!另一个师长插嘴道:“这是一点不假的,讲卖命,我们绝对不做汉奸!讲爱国,我想起当年请缨杀敌,却挨了委员长一顿臭骂,作声不得!可是有人却骂我们不敢抗战,一口鸟气把弟兄们肚子都气破了!”
郑洞国双拳齐挥,严肃地宣布道:“大家那些话,留着以后再说吧!弟兄们在等待我的决定,我现在已决定放下武器,不再顽抗到底作无谓牺牲,不再坚持死守使玉石俱焚!决定挽救全军袍泽,弃暗投明!”郑洞国热泪长流:“快通知他们,新七军等部三万几千多弟兄和城郊一万八千多被围弟兄一齐放下武器,弃暗投明!”
众将官分头传达,三军欢声雷动。郑洞国待诸事就绪后离开总部,准备出城,去解放军兵团司令部。他朝中央银行大厦回顾一眼,觉得是该离开这个戒备森严、阴暗低沉的地方了,但他对新的事物是如此生疏,一时也无法为未来描绘出一幅什么画图。他轻松之中有沉重,长时期地懊丧悔恨并未去尽,在新旧思想交替之中,有茫然之感。
郑洞国领导一些部队出城,解放军则列队进城。只见纪律严明,军容强盛,忽地有人向郑洞国打招呼,原来是解放军兵团政治委员肖华将军。
郑洞国暗吃一惊,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如此和气,一点儿也没有架子。两人握了握手,肖华道:“欢迎你们一起来!司令员在等您,你们多谈谈,我进城去。回头见。”郑洞国对他质朴和气的印象深刻极了,当下直奔兵团司令部,司令部肖劲光将军欢迎他道:“郑将军早该过来了,为了国家大事,我们之间实在没有你死我活的必要。”
郑洞国道:“是啊,这件事,想想很难过。”
“你该休息一会,”肖劲光道,“晚上我们多谈谈,大家痛饮一杯!您就住在附近好了,房子已经准备好。”
但郑洞国怎么也睡不着。他想得太多了。在解放军非常礼貌的晚餐招待席上,他对肖劲光说:“大体情形,也就那样了。我在国民党里干了二十几年,现在既然失败,当然听凭处理;至于部下官兵,如有愿意回家的,希望能让他们回去。”
“那一定是这样,”肖劲光道,“你愿意回家还是愿意留下?”
郑洞国一怔,没料到对方是如此直爽,态度是这样友好诚恳,招待也是那样客气周到,在这种情形下,他该如何回答呢?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军人,没有了解自己是一个新生的战士。在一些古老观念的影响下,他回答道:“我现在只想做一个老百姓,”他苦笑:“不知道行不行?”
“你想错了。”肖劲光微微一笑。郑洞国诧问道:“那是怎么回事呢?”
肖劲光叹道:“你多看看、多想想之后,再作决定吧。”郑洞国一个劲儿喝洒,总以为自己是英雄落难,“为人民服务”似乎就等于给共产党做事,不大合适吧?可不能这样贸然决定。便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当个老百姓,表示中立的意思。”
“中立?”肖劲光凝视一会,点头道:“希望你多看看、多想想,好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通的。怎么样?到后方去旅行一趟吧?譬如说哈尔滨。”
郑洞国道:“很好,我对你们有很多隔膜。去看看,好主意。”他苦笑道:“有一个时期,我们总以为你们的武器都是苏联造,你们的部队里有很多苏联顾问,现在我对这些明白了。”
肖劲光大笑:“也难怪,你们一天到晚接触的东西,绝大部分是谣言。老实说,没蒋介石,我们这么多美式配备就不可能拿过来;没有南京大规模的空投,我们好多补给也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这些都是美国人奉送的。”说罢举座皆笑,郑洞国也不由得笑出声来。
司徒雷登在南京大使馆里只是干瞪眼,听傅泾波为他诵读各方机要消息,一筹莫展。
“郑洞国并没有死掉。”傅泾波道,“中央社的电报又错了!”
“该死的!该死的!”司徒只有顿脚的份儿,“那同王耀武的下落是一样了?”
“不不,”傅泾波说,“比王耀武还要糟。他是过去的,并未逃跑。”接着声音都变了腔,捧着一张电报说:“范汉杰被捕的消息也到了。”
“我不听,我不听!”
“这里还有共产党的广播记录,也是关于范汉杰的。”司徒无可奈何,咬咬牙道:“好,你说吧,我要看看他的部下!他的部下都反叛了他!”
“范汉杰的情形是这样的,”傅泾波念道,“在16日那天,锦州城东南二十几里的谷家窝东面小道上,走来了4个着黑色服装的中年男女。其中一个高大个儿,穿一件露出棉絮的破棉袄,一条不称身的小棉裤,背上披一个破麻袋,手里捧一个萝卜在边走边啃。”
司徒雷登冷笑道:“他倒装得像啊!”
“正在那个时候,”傅泾波读道,“共军处理俘虏的机关恰巧在那边驻扎。当他们发现这4个人时,就开始盘问了。4个人之中,有个操福建口音的女人屡次抢着答话,另外两个男人显得很疲乏的样子,只是唉声叹气摇头。有个又高又大的男子压低声音,说他是沈阳一家钟表店的账房,从沈阳逃出来,准备回福建老家。这个人总是把破毡帽往下拉,遮往半个脸,避开人们视线。但他很不自然的装束和动作,两只白白的手和牙齿,低低地声音里还听得出一口广东腔,这些同沈阳难民的身份不合。”
司徒摇头道:“国民党的将军啊!国民党的将军真使我们伤心!”
傅泾波说下去道:“共军盘问他们4个人的相互关系,那个大高个儿无法交代清楚。他迟疑了一会,说:‘我没有话说了,你们枪毙我吧!’于是他们被扣押起来,进行审讯时漏洞百出。女的乱说一通,另两个男的自供是尉官和勤务兵。那个大个儿却什么也不说。当共军的卫生员给他擦伤了的头皮上药时,他却很认真地说:‘擦些酒精吧!当心变成破伤风。’”
司徒失笑道:“范汉杰还想活啊!他给美国增加了多少麻烦?给蒋介石丢了多少面子?”接着听傅泾波继续说:
“第二天,那个自供是尉官的人对看守他们的共军说,他有一件要紧的事情告诉审讯员。当审讯员接见他时,他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经过你们多次解释俘虏政策,我还没有说实话。现在我要说了,我就是范汉杰的侍从副官,那个大高个儿就是范汉杰。’”
司徒拍桌子道:“真糟啊!蒋介石手下怎么都是这样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傅泾波皱眉道:“不过,根据共方的情形来说,那个侍从副官如果不招认,恐怕还是会弄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共方锦州前线部队之中,发下去这么一个备忘录:‘范汉杰,广东人,年42岁,高大个子,面黑秃头。’他逃难的打扮同这个备忘录完全一样,人家只是向他解释俘虏政策,迟早会供出来的。”
司徒叹息道:“泾波,你看!这些国民党将领大量背叛我们,我痛心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