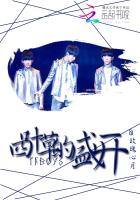霍俊明
“接受抒情的苦味”
——关于芦苇岸的诗
0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芦苇岸”这个名字,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年海子在昌平的好友苇岸。尽管与芦苇岸未有一面之缘,但这两天因为特殊的因由一直在读他的诗。我已经厌倦再谈什么70后了,这招致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诗歌永远是个体的事情,我只想安心静气地谈谈芦苇岸以及我对他诗歌的斑驳观感。
我喜欢诗歌中的“夜晚”胜过现实中的“灿烂正午”。我也更愿意接受一种“抒情的苦味”。
1
我暗自喜欢芦苇岸的近些年的诗歌写作姿势,这甚至在我看来在当下的诗歌话语场中有着不言自明的重要性。2006年开始芦苇岸不再向报刊投稿,这使得诗歌写作回归了最为本真的源头。我们已经看到诗歌的发表已经到了如此简单的地步,如果我们是从“民刊”或者新媒体的角度来谈论诗歌的发表和传播就更显得有些吊诡。当诗歌进入到文学场域中的时候,诗人的写作必然会程度不同地受到刊物品味、编辑眼光和时代诉求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时下如此相近的诗人和大量相互替换的诗歌仿制品。因此,我更喜欢芦苇岸那颗“挑剔的胃”和“素净”之心,我也更乐于阅读这些更加自足和个体的写作以及由此发出的声音和一道道细小却惊心的闪电。
*霍俊明,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协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供职于中国作协创研部。
当他的诗歌发声通过文字放置在我案头的时候,我们得感谢这个无比纷杂的时代。如果在古代,我不知道一个远方诗人的声音如何能够如此轻易地穿越了万水千山以及春夏秋冬的漫漫长途。
惊异的是,在芦苇岸的诗歌中我不断听到了寂静的空空之声。然而这寂静似乎又具有着强大的容留之力。在这寂静的部分我却听到了如此众多的弦外之音和时空流转的释然与茫然。这不仅相当明显的呈现在他的长诗《空白带》中,而且在他的诸多短诗(《从新埭到乍浦的末班车》《宽恕》等)中,我不断与一个个寂静无声的片段、细节和场景相遇。这也不能不是“消费时代的抒情”不可避免的悖论与紧张。但“寂静多美好”显然又是出自于一个当下诗人的反讽的喟叹!因为这寂静背后我看到了田野里薅草的人在正午的土地上留下的汗水洇湿的部分,看到了那些尚未被认领的无家可归的庄稼的集体静默。这寂静已经成为芦苇岸的诗歌美学和情怀底色。在他的一些诗歌中出现了不在少数的“盐粒”的意象,而苦涩、粗糙和沉重的部分我们只能在那些飞鸟的羽翼之下,在滚沸的大海的褶皱部分,在细小事物的幽微纹理当中去寻找他何等渺小却也不容忽视的身影和内心的潮汐翻卷。
芦苇岸的寂静的盐粒里藏有往日的大海的激荡和喧嚣,他的诗歌的知性和忧郁的色彩无疑使得他是一个“成人”诗学的践行者。但是我又往往于他的诗歌中看到暮晚笼罩中一个“孩童”的孤独身影。他仍然在走失的空间里继续寻找,不断跌倒,不断咬破自己的手指寻求遥远的安慰之声。就我个人的观感,我觉得与“孩童”式的发现和询问相应,在诗歌中芦苇岸把“诗人”放的位置非常低。换言之,他是躬下身子在和事物对话,他甚至会趴下身体倾听那些陌生而久违的声音,他也会躺在曾经繁茂的田野的植物之中透过斑驳的叶片看看那些从上空洒下的时间的秘密之光。是的,是那些松针测量了故乡的星光以及一个诗人的干净之心的疼痛。他卑微虔敬的诗人之心一次次让我感动。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斑驳光影深处的“孩童”又是一段历史惨烈的折光在他弱小的身体之上不无沉重的回声。而当这一切以个人化的历史想象能力予以观照和抒写的时候,像《73年的下午》这样重要诗作的产生就成了一种必然。当然,这个“孩童”有时候随着“中年化”的到来而被迫在一条条土路、柏油路、国道或者高速公路以及铁轨上隔着车窗恍惚而盲目地来张望外面的世界——“窗外的原野,像被公牛尾巴扫荡过/又像书生翻过的册页/记忆迅速滑入盲区。一块块/麦田缝合的大地,开始生长色斑”。这在《07省道》《从新埭到乍浦的末班车》《旅程》《悲悯的念头一闪而过》《命运》《过南京》《火车走在霜里》《霜降》等诗中都有着一致性地体现。这些诗的场景都是与“车”和“道路”有关,而背景又往往是发生在夜晚。这构成了某种戏剧性,一个时代真实的个人戏剧性命运的上演和无声落幕。“雨夜,开车行驶在幽暗的省道上”,这种黑暗,这种寒冷在我看来更具有时代寓言的象征。而以前诗人是在桥头、船尾、村落、酒馆、歌楼、山顶和水岸来看待自然的山水和缓慢的内心,而如今我们的时代只能在疾速而眩晕的“高铁”般的时代隔着迷茫的车窗观看迷茫的一切。这种快速行进的观察方式使得芦苇岸的诗歌不能不有着强烈的茫然失落的情绪。必然,这一切又时时与那个“孩童”发生着不可避免的碰撞和摩擦。尽管诗人也曾在21世纪的酒馆里抒情,但是已经是今非昔比,这里有的只能是黑色的抒情无边无比地蔓延——“从一天的烦琐里抽身出来/我们离自己就近了/在吁吁喘息的小酒馆/冬天巫师一样寒冷/白昼消弭黑暗降临/万物逐渐陷入被加热的过程”(《在小酒馆》)。
这个时代,诗人只能靠自身取暖!苦味的抒情似乎无处不在。而在一个诗人日常性的茫茫图景中我又时时看到一个面水而居的诗人和他“老式”的衣襟。芦苇岸有时呈现了一个现代人的古典抒情方式,而这种抒情显然又与当下性直接相关。换言之,芦苇岸呈现了一种矛盾和紧张的抒情方式,古典文人的情怀与当下去诗意化生存状态之间的盘诘和龃龉。这在其组诗《湖光》中有着不言自明的呈现和坦陈。
2
我认为芦苇岸在一个愈益远离了自然之物的时代,他仍怀有一颗亲近“草木”之心。这是一个仍然懂得寒露和薄霜的来由的诗人。这是一个有着“农时”记忆的当下诗人。在这一点上,诗人是怀有“方言”的人,他的某些地方总会让人具有陌生感。
这两天看电视说麦子很快要收割了,我突然愣了许久。突然发现一个有着三十年乡村生活的人突然在北京丧失了“农时”的概念!在芦苇岸的诗歌中我看到了“历史的残余”部分,而这些部分往往是不经意间在他的诗歌文本中现身的。我更认同这种不自觉,就像我们时时在呼吸却忽视了呼吸自身一样。芦苇岸的诗歌中这些不经意间现身的“历史的残余”部分恰恰显现了这个诗人的诗歌呼吸方式的特殊性。在他的诗歌中,我长时间停留于这些偶然惊现的土地、庄稼、手电、扁担、柴门、种猪、乡村、平原等这些已经被时代遗弃之物上。它们延宕着我们往日性的叙事,也提请着一个抒情时代的黯然结束?当诗人在压抑和失望的回溯中喊出“我肉体的故乡”时,故乡是有生命的,而诗歌也不能不是有体温的。在这一点上,生命诗学不如“身体诗学”来得更准确和有力!而这无比真实的“身体”能够让我们提前领受“暮晚的广场”。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迎接那广场的暮晚无边无际的阴影?并且我们是否准备好了足够的词语来面对“天真的晚课”和这一切?这是一个准备时时出走的诗人,他不断在郊外、广场、树林、道路、河滩、小镇的黄昏向晚中寻找?寻找精神的自身,伟大的元素,落寞的时光,还是寻找一个无比真实又无比虚空的存在?
而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些精神性文本中的细节、场景离中国的当代“现实”究竟有多远。是的,在一个如此诡谲的时代,我们进入一个时代“内部”是如何的不易,而进入一个无比真实的“现实”是如何的艰难。在一个写作已经与新媒体打得火热的今天,真正的诗人是否懂得沉默有时候是更好的语言。在芦苇岸这里我强烈感受到了一个冷峻的“旁观者”和“水深火热”中的“介入者”一起推给我们的无边无际的沉默、自语和诘问。而当我们不得不采用“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和言说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种极其尴尬的角色意味着曾经拥有和目睹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连同我们自身也成了“内心”和“故乡”的双重的陌生人。而坦率地讲,阅读当下的诗歌我们会发现诗人在诗歌技艺的娴熟上要远远胜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但是真正有难度的诗歌写作却越来越稀薄了。在我看来这种有难度的诗歌写作不只关乎技艺更关涉一种想象的方式、生存的态度。在近几年的阅读体验中,我可能为一首诗所感动或者惊叹于某一诗人娴熟的技艺,但是我更乐于承认在芦苇岸的诗歌中体味到了一种久违的发自灵魂深处的寂静和捶打。这与诗人的根性记忆和生存履历有关,更与诗人用语言和想象所构筑的特殊修辞场域有关。芦苇岸的诗歌同时具备了两种不同的精神向度:迎拒与挽留、温暖与寒冷、现实与记忆、疼痛与慰藉。而这种不同的诗歌精神向度的产生一方面来自于诗人对生命履历的温暖而失落的感怀与记忆,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个体在强大的工业和城市化时代的浪潮中的阵痛以及在现实生存的压力、时光的流逝和温润情怀的丧失境遇下的分裂与伤痛。正是这种历史、生存和现实在诗人的内心和背脊上洒下了无尽的芒刺,而同时诗人仍然在此境遇下用“寂寞的胃”秘密地爱着他的身边那些无比沉默的部分。
3
芦苇岸的很多诗都能够通过一个细小的事物和场景呈现出带有历史和现实感的宽阔地带,而其中的讽喻性和悖论性精神特征是显豁的。在一个分层愈益明显和激化的时代,“中国现实”的分层和差异已经相当显豁,甚至惊讶到超出了每个人对现实的想象能力。在这种情境之下,由芦苇岸诗歌中的“精神事实”(比如《消费时代的抒情》《身体的地图》《以一个意象缩短和生活的距离》《春天,背母亲去野外走走》《高处》等诗)我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化的方式来观察和反观中国现实的历史和当下的诸多关联。然而可笑和可怕的是很多的写作者和批评者们已经丧失了同时关注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显然在一个多层次化的“现实”场域中,道德化和敏感的社会化题材显然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写作的虚构和想象中都构成了一个不容置疑的“重要现实”。而当下处理这一“重要现实”的文本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
而需要追问的一首诗歌与一条社会新闻的区别,一首诗歌如何能够与庞杂的类似题材的诗歌文本区别开来?区别的动因和机制以及标准是什么?这显然是一个必须探究的问题,而且非常有必要。实际上,我们的诗歌界这些年来一直都在强调和“忧虑”甚至“质疑”的就是指认当下的诗歌写作已经远离了“社会”和“现实”。里尔克的名言“生活与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在今天的中国是否仍然适用和有效?尤其是面对着当下的带有“重要现实”层面的诗歌写作而言,诗歌和诗人与“现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当诗人作为一个社会的生存个体,甚至是各个阶层的象征符号,当他们的写作不能不具有伦理道德甚至社会学的色彩,那么他们所呈现的那些诗歌是什么“口味”的?我想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任何企图回答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具备综合的能力,显然诗歌自身的力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出现了抗震诗、高铁诗,但是真正能够留下和被记忆的却几乎成了空白的原因。曾记得2009年,著名艺术家徐冰用废弃的钢铁、建筑垃圾等材料打造成了两只巨大的凤凰。这本身更像是一场诗歌行动,时代这只巨大“凤凰”的绚烂、飞升、涅槃却是由这些被废弃、被抛弃、被搁置的“无用”“剩余”事物构成的。这就是诗歌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实际上,诗人和现实的关系有时候往往不是拳击比赛一样直来直去,而更多的时候是间接、含蓄和迂回的。显然,中国当下的诗歌更多是直接的、表层的、低级的对所谓现实的回应。“足不出户”并非与现实不发生关系。“出户”的诗并非就一定能与现实发生关系。人们似乎已经忘却了1995年诺贝尔诗歌奖在希尼的授奖词中所强调的“既有优美的抒情,又有伦理思考的深度,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一个加速度前进的“新寓言”化的拆迁时代,各种层出不穷的“现实”实则对写作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试图贴近和呈现“现实”的诗作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相应的像芦苇岸这样的具有提升度的来自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具有理想、热度、冷度和情怀的诗歌却真的是越来越稀有了。在一个重新消费了“底层”和“苦难”的伦理化写作的今天,芦苇岸的一些同类题材的诗歌却让我们发现了极其陌生而真实的声部,比如《高处》这首诗就是近年来少有的带有“发现性”和“真实感”的诗作——“炫目的高楼,肃立在上班途中/一声口哨经过我/在我仰望的高度/一群人膏药一样贴在玻璃幕墙上//看不清他们的脸/黄色的安全帽和背上的红吊桶/让更高的高处,温暖、悦目、稳靠/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抬头送上惊讶/而让路人更惊讶的/是他们中间竟然有女人——长长的马尾辫/像划过时空的一道黑色闪电//他们说着黄段子,放浪地大笑/沾满泡沫的污水通过手里的刮器/流进红色的吊桶里/蓝天渐渐直立,离人们越来越近/太阳靠在玻璃上,安静地睡去/她的梦,在反光,干净、清新”。更多诗人浮于现实表层,用类似于新闻播报体和现场直播体地方式复制事件。而这些诗歌显然是在借用“非虚构”的力量引起受众的注意,而这些诗歌从本体考量却恰恰是劣诗、伪诗和反诗歌的。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多年来我们注意到一些诗人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想象和叙述能力,但是更多的却是丧失了对“日常化现实”的发现和想象能力。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一个讯息极其发达的“自媒体”时代,很多写作者都自认为在现实生活和写作情境中都不断地呈现了这个时代最为“真实”的一面。
4
我曾一度怀疑“当下”人写作长诗的必要性,因为无论是呈现个人情怀还是历史想象能力与诗歌的“长度”并不本质的关联;再者我对当下诗人的写作能力持怀疑的态度。尽管我不断听到诸多诗人朋友和批评家同仁们对当下诗歌的溢美之词。甚至不是有更多的人指认当下是中国诗歌发展的最好时期(起码是好时期之一)?我不断听到诗人们在新媒体时代高呼“诗歌的好日子”来了。然而,那些所谓的流行的伦理性、社会性的关涉“现实”的诸多诗作我却一次次阅读后失望而归,因为真正的、重要的诗歌在这个时代仍然是欠缺的。
芦苇岸在渐进“中年”的时刻,其身体和内心都具备了构造一首长诗的能力。尽管《空白带》在处理强大的个体经验与“现在时态”以及相关的场域中仍有未予以发现和抵达之处,但是这首长诗在当下确实有一定的“表征”能力。或者换言之,这首诗能够回答诗人和诗歌在面对个体、现实甚至更为庞大的“历史”与存在之物时应该予以怎样的发声?尽管《空白带》最大的优点或者也可以视为“不足”的是并无明显的构架体系,看起来似乎有些“涣散”,但是我想这种“没有结构的结构”却似乎暗合了这首长诗的精神内核和诗人的言说状态。空白带,我们曾试图一次次记录我们的过往,让往事留下行踪和印记,甚至我们会用文字的方式来铭刻一个窄窄的碑文。但是我们真的具有这种综合的记忆能力吗?我们真的具备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的能力吗?而“空白带”却恰恰呈现了诗人无所不在的深深的隐忧、恐惧、尴尬,记录与空白、文字与空白、记忆与空白之间就呈现了拉扯不断的无物之阵。诗人——具有记忆能力、现实隐忧、历史能力和个体情怀的诗人——是否就注定是一个“空白带”的宿命?我们试图留下和铭记的越多,我们注定失去的越多。而这种失去还不完全是诗人记述和记忆能力能否被长久传播的可能,而是在于这种关涉文字的记忆会遭受到无所不在的“庞然大物”的侵扰、筛选、迷惑甚至覆盖。或者诗人所呈现的记忆的历史和拨转过往、面向当下的“胶带”是否就足以更大程度上还原、呈现和折射一个曾经的历史过去时甚至面向现在进行时?
长诗《空白带》的起句“生活注定从低音区开始”无疑奠定了全诗的基调和走向。这也是一个诗人面对“现实性”和“想象性”情境的观看方式和特殊入口。当然也是一种伦理性色彩的精神姿态。而“空白带”显然试图记录各种各样的“声响”和“静默”,而我最终在这些轰鸣或者低语的高低错落的声音区域中看到了一个在“空白带”的“空白处”和“静音区”试图在宁静中“俯视落叶”然后起身、在“平静中突围”的背影。在“空白带”中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一个个静默的部分,这些已然消逝或正在消逝的“隐忍”“传统”“落伍”的被时代遗落的部分却正是更多的中国诗人丧失记忆和发声的部分。在“静音区”试图“发声”正是芦苇岸这首长诗的一个非常可贵的质素和势能。《空白带》作为长诗必然具备一个个细节或场景。而这些细节和场景既是个人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实有的又是想象性,即是时间性的也是生命本体的。诗人以精神地形学的方式设置了大量的“眷顾性”的精神积淀层面的寓言性、想象性、吟述性和歌咏性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也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光褶皱和无处不在又无比驳杂的现实境遇的真实内里。在《空白带》这里是通过“遥望”和“当下”、“回溯”与“照看”的想象性的真切擦亮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向度上使诗歌具有巨大的承载力和容留的力量。时间在记忆中共时呈现、交错、盘诘,既避免了耽溺内心的凌空虚蹈的矫情,又规避了沉滞表象细节的臃肿困顿的刻板。这正如遥远历史深处的那口小小的但幽幽而沁凉的水井,往日的倒影尽管还斑驳回荡其中,但这注定已经成了历史和生命过往的不可挽回的回响。正是在这些具有黑白照片性质的“已逝”之物之上,诗人得以同时怀抱秋风和寒雪,也许只有诗歌的想象性图景能够获得重新面对时间的能力与资格。而这种冷暖并置、晴阴交接的景象以及时而舒缓,时而喷发式的诗句交错正是一个诗人生存世界和精神场域的象征。黑白夹杂的诗歌成色让我想起了黑白照片,这些黑白照片更多呈现了摄影是一门挽歌甚至死亡的艺术。这些黑白的带有逝去性质的照片和影像使得无比坚硬和无情的时间在语言和想象的空间得以挽留和停顿。可以说,芦苇岸以“空白带”的方式呈现给我们既熟悉又不无陌生的“另一个世界”。他所设置和安排的场景、氛围和纹理清晰的细节都真实得像一个个我们所不愿意接受的遥远的“寓言”,也像一个个抹不去的真实与想象相夹杂的白日梦。它们所构成的温暖、寒冷、空无、实有、黑暗、明亮共生的景观让我们有些对现在这个世界心生恐慌。面对着这些现实化和想象性同时呈现的场景以及经过诗人过滤和再造性的象征性空间,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无边的场域。那一切曾经如此熟悉,而今天这一切只能在冥想中现身。而诗人和诗歌所面对的疼痛的时间不能不承担起黑白照片的挽歌的质地。
5
芦苇岸近年来的这些诗歌文本因具有多个方向的巷道而同时打通了个人与历史和现实之间极其交叉的空间。而在想象性的精神层面,这写诗又能够成为反观中国精神现实的重要入口。这入口需要你挤进身去,需要你面对迎面而来的黑暗和寒冷。需要你一次次咬紧牙关在狭窄的通道里前行,也许你必将心存恐慌。但是当你终于战战兢兢地走完了这段短暂却漫长的通道,当你经历了如此的寒冷和黑暗以及压抑的时刻,你才能在真正的意义上懂得你头上的天空到底是什么颜色,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只有如此,你才能在语言的现实和发现性的“现实”空间里真正掂量你所处的社会现实。尽管入口不大,但足以“步步惊心”。
这小小的针尖的部分足以能够搅动整个大海,而这大海阴影和褶皱处的部分那一个个静默的苦涩而晶亮的“盐粒”也终得以现身!
请再一次“接受苦味的抒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