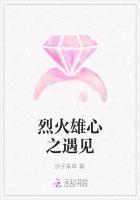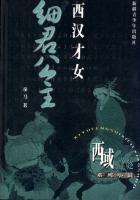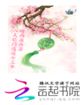管教的内涵当然远不止维持秩序,可以说,它是使孩子朝着令人满意的自控方向逐步成长的过程。大人应该懂得,孩子的道德发展要经历三个主要阶段,而在每个阶段他们都需要大人的帮助。
了解生命历程的自然教学法
如果小时候孩子眼中的父母就彼此互敬、互谅、互爱,那么父母将是他性教育的最佳教材,因为他能从父母身上,看到最完美、最严肃、最真实的男女关系。
蒙台梭利博士从来没有讨论过“性教育”,也没有在书中提到过性的话题。她之所以对性话题避而不谈,绝不是主观忽略或故意逃避,相反,蒙台梭利博士是从更严肃的哲学角度来涉及人类生殖话题的。她将研究重点放在胎儿的发育以及接下来对婴儿的照顾上。她睿智地避免采用医学术语来谈论人类的性话题,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探讨,并且将自然、爱、亲子关系和儿童发展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与目前流行公开讨论“性行为”的家庭计划生育手册、媒体广告、在校性教育以及“性指导”等相比,蒙台梭利的教育方法显然更为独特。在孩子看来,人类性交及其细节的描写非常晦涩难懂。因此,孩子的自然关注点不在这些方面,而是将注意力投向一个更宽广的领域,例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与了解夫妻同床、性疾病等有关知识相比,孩子更想知道上述问题的答案。
孩子想了解与生物起源以及生理机能有关的问题,因为他对自然界天生有一种亲切感。诸如春天候鸟归巢、小动物出生、宠物的养育与成长等现象,不仅能促使孩子更加关爱环境,而且还刺激他去主动探索自己的生物性问题。换言之,每个孩子都知道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于是才有兴趣探索生命的起始和结束。当看到或听到小动物诞生以及母兽抚育幼崽的故事时,孩子会乐在其中、为之陶醉。他们对松鼠难逃被车撞死的厄运、人类杀死动物供自己食用以及养育的宠物突然死亡等现象也非常好奇。这些现象都能激发孩子对生物世界的兴趣,这也是孩子在成长中必然会产生的倾向。
因此,保护孩子对自然界的兴趣并引导他探索自然科学的奥秘,就成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多数小学生对史前生命的演变进程颇感好奇,也希望从现代的动物园里汲取知识养分。无论是原生动物还是人类,孩子都希望发现其中的生命奥秘。他会比较自己和史前人类在外表上有什么异同,并运用想象力进一步探索人体的生命机能,如呼吸、循环、感应力、生殖系统功能等。既然如此,当孩子希望对自然界形成整体概念时,为什么要单独灌输“性教育”呢?
父母根本不必成为动物学家,就为孩子介绍自然界的知识。带孩子到自然历史博物馆、动物园,或者拜访兽医、借动物书籍阅读,这些都是简单易行的方法。动植物的生命历程是一个谈不尽的题材,多花点时间为孩子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绝对值得。
父母不应对性知识持特殊的态度,而应与生物界的其他事件同等视之。向孩子解释动物园猴子的交配过程,为什么会比解释枫树种子盘旋落地更加复杂?孩子不是窥阴狂,因此他们希望知道身体各部位的名称是无可厚非的。可笑的是,由于当代文化过于正统和严肃,以至于人们竟然借用植物学中的术语来描述性行为,比如“父亲正在播种”。但小孩看到动物的性行为,自然就会提及生殖方面的问题,因此,大人应当以简单的动物为例,用自然的方式向孩子介绍。
刚上小学的孩子问到性问题时,多半与“为什么”、“怎么样”有关。蒙台梭利专门制作了一套探讨生殖问题的教材,并称为“照顾下一代”,书中不仅介绍动物交配,更详细地阐述了对后代的抚养。虽然她介绍该课题的方法和用语很简单,但却能使孩子对生物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
教材一开始便介绍鱼儿产卵。鱼把没有保护能力的、“裸体的”卵产在水里,由于数量太多,因此其生存几率仍然较大。两栖动物的卵外面有一层·“果冻”覆盖,这一方面是为了不引起其他动物注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养分给幼崽。教材从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实例开始,讨论如何抚养下一代的问题。雌鸟除筑巢保护幼鸟之外,还通过“反哺”食物给幼鸟喂食。哺乳动物的育婴方式更加体贴,幼崽会一直待在母亲的肚子里,等到发育成熟时才会生下来。之后,母亲以乳汁喂食幼崽,并在提供很长时间的保护之后(远超过其他动物物种),才让它们独立生活。
也许这样介绍过于脱离实际,或者说过于乐观、目的性和方向性太强。但对孩子来说,这样介绍只是为了提醒他们是哺乳动物王国中的成员,并促使他思考与自身有关的问题。蒙台梭利对哺乳动物如何照顾下一代的阐述,是科学研究和本能思考促成的结果。
哺乳动物在自身本能的指引下,会在哺乳期间对新生儿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家猫就是典范。母猫通常会把小猫藏在某个又隐秘又黑暗的角落,她表现得特别排外,甚至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它的下一代。一段时间之后,在母猫的精心呵护下,小猫咪个个变得活泼可爱。
野生动物对幼崽的照顾更是体贴入微。大部分野生动物都群居,可是,母兽在快要产崽时会离开同类,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待产。生育之后,母兽会留下来独自照顾幼崽,时间短则两三个星期,长则一个月甚至更久,具体时间视其所属的物种而定。在这段时间里,母兽既要供养幼崽,又要充当其“守护神”。为保护幼崽免于亮光和噪音的干扰,母兽会选择一个非常安静、非常隐秘的地方。尽管有的野生动物生下来就有很大的力气,发育得也很快,但母亲仍然会隔离它们,单独进行细致耐心的照料,直到它们茁壮成长、有了足够力量、能够适应新环境,才会带着它们去寻找同类,过群居的生活。
总体而言,无论是野马、美洲野牛、野猪、狼还是老虎,所有高等野生动物的母性本能都比较类似,母兽对新生儿的照顾方式的确令人感动。
例如,美洲野牛在产下小牛之后,会独自带着小牛生活数周。在这段时间里,母牛表现出无比的耐心,一心一意照顾小牛。如果小牛体温太低,母牛会用前腿盖住它;小牛的身上脏了,母牛会耐心地用舌头舔干净;小牛饿了,母牛会用三条腿而不是四条腿站立,以便小牛能吃到奶水。当小牛长大、被母亲带回同类中时,母牛依然会细心地照料它。所有四足野兽的母亲都有同样的本能。
有些动物甚至不满足于“为幼兽找一个偏僻的住所”,于是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寻找最佳地点,其目的只是为了尽好母亲的职责。例如,为了生育和抚养狼崽,母狼会前往森林遥远的角落,竭力找一个黝黑的洞穴。如果找不到理想的避难所,它会想办法在地上挖一个洞,或者在一棵枯树中间打个洞,做成一个中空的“家”。找到或做好这个洞穴后,母狼便从胸前撕咬出许多毛,铺在洞里。这些毛不仅可以使狼崽保暖、有效保护狼崽,而且便于母狼哺乳。狼崽出生之后,有一段时间眼睛和耳朵都是闭上的。在哺育期间,任何动物或人若想接近或侵犯幼崽,母兽都会挺身而出、全力保护孩子。
如果将动物关在动物园里,它们的上述母性本能就会被扭曲。母野猪是最有爱心、最会照顾幼猪的野生动物,但是,一旦把它们关进动物园或者由人类饲养,为了保护小猪,母野猪甚至会吞食自己的孩子。母狮也可能有同样的骇人之举。这些事实证明,只有在免遭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动物天生的保护本能才会得到正常发展。
哺乳动物的母性本能清楚地告诉我们:小动物出生后必须接触外部环境的时候,需要母亲予以特别照顾。对于幼崽来说,经过出生考验并开始显示出各种能力之后的一段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段时间里,它们需要休息,需要谨慎而低调地隐居。就算捱过了这一时期,它们仍然少不了母亲的照料、喂食和保护,时间又可能长达数月。
母兽不仅关心幼崽的生理需求,也关心对其本能的培养。每头母兽都期望下一代长大后和其他同类一样,包括拥有强健的体魄和高超的猎食本领。而培养这些能力的过程,最好在一个光线较暗、安安静静的场所来完成。当小马的四肢有些力气时,母亲会带着它慢跑,让它慢慢成为一匹真正的马,但在此之前,母亲绝不会让小马抛头露面。同样,除非小猫睁开双眼、学会了走路、长成了真正的“小猫”模样,否则母猫不会让小猫露面。
按照动物的天性,所有母兽都会用最大的耐心和爱心,去认真照顾自己的下一代。更重要的是,在引导后代显露和培养身上的潜能时,母兽甚至关心后代身体以外的其他需要。
同样,对于新生儿,我们除了关心其身体健康,也应当关心其心理需要。·从蒙台梭利提供的启示可以看出,孩子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时,就有一个涉及心理和生理两个层面的隐秘计划在付诸实施。生理生命始于一个小小细胞的生成,并依据一张“精确的建筑蓝图”来建造。因此,向一个10岁的孩子传授生育知识时,应强调母体身上具有自然保护机能的部位如羊水、子宫、脐带等。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传宗接代的事实,再次将科学和父母无微不至的爱结合在一起,这种爱是与生俱来的。至于被称为“最高等动物”的人类,其胚胎更是独一无二,因为它除了生理生命之外,还有心理生命,远比其他动物复杂。人的胚胎不可能移植到猪身上,反之亦然。人的婴儿期虽然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但却有自身的特殊含义。蒙台梭利写道:“孩子生活在爱的沐浴中。因为先有爱,后才有婴儿的诞生。婴儿刚出生就被父母的爱包围。父母的爱出自天性,这种爱会带给他们无限的喜悦,所以不会认为爱是一种牺牲。”因此,性知识的介绍其实是真正的“爱的教育”,绝非仅仅作为告诫“切勿未婚先孕”或解释“亲吻多久会诱发犯罪行为”的教材。
如果小时候孩子眼中的父母就彼此互敬、互谅、互爱,那么父母将是他性教育的最佳教材,因为他能从父母身上,看到最完美、最严肃、最真实的男女关系。倘若接下来让孩子阅读“自然科学”和“生物学”相关书籍,他的胸襟便更加宽广,会了解更多爱与被爱的实例。无论有多少社会现象呈现病态,“大自然”都将教育他生儿育女的神圣使命以及照顾后代的伟大任务。他将对未来充满向往。对他而言,人类的爱不是命令或法律,而是生存的理由。他将能领悟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并懂得“大自然是人类的最佳导师,是最能给人启迪的生动素材”的道理。
(大卫·肯)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人类获得的所有知识,都源于“对自身的探索”。当人第一次试图解释自然现象时,就以人的普遍特点和他自己的特质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
知道自己是谁,或者说具有自我意识的动物,一定不会安于现况,甚至会进而提出“我为何存在于这个星球上”的问题。幸亏老鼠和黑猩猩不知道自己是谁,因此不会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但偏偏人类会问这种问题。一旦人们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就会穷尽一生之力探求真相。数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人全身心地投入这方面的研究。不知道自己是谁的黑猩猩,不会有了解自身起源的冲动,因此不会有预测未来的烦恼。就算人能教会它数100根香蕉,甚至教会它下棋,它也不会有益于任何科学,不会辨别是非美丑。若要问人最伟大的智慧源于何处,恐怕要回溯到他对自身生命何始何终的追问,或者说对自身存在的意义和生命本身含义的探求。
或许你会问:这些问题和孩子的心理成长有什么关系?请相信我,这两者是有关联的。
人类获得的所有知识,都源于“对自身的探索”。当人第一次试图解释自然现象时,就以人的普遍特点和他自己的特质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例如,他可能会说,风是上帝看不见的呼吸,打雷是大力神发怒和报复所致。根据树木和云彩,他发现了人的形状;根据季节的变化和日夜更替,他发现了人的特别之处。他会对自己的身体和天性做详细的观察,从而在面对自然界时,·能很自然地利用观察结果来解释自然现象。不过话说回来,连这一点都是人类运用智慧的成果,因为只有人类才能观察自己。当人类发现自然界的运行法则并联想自我观察的结果时,智力的开发就有了强大动力。但在历史初期,人类最大的好奇心源于对自己卓越天性的追求。通过这种追求的过程,人类得以超越自我。人类已经学会用智慧控制身体活动和心理状态,从而取得许多“只有人才能取得”的成就。简言之,自我观察导致自我控制。人类先学会观察“自我”,然后再学习如何进一步控制生物性自我。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孩子是人类种族历史的缩影。孩子根据自己的身体第一次发现“我”,第一次了解内在与外在、“自我”与“非自我”的区别。一开始,他会触碰自己的身体、吸吮手指头、看见身体的各个部位,第一次形成“我”的概念,但由于对目睹的事物不敢确定,于是再利用新学会的文字,对“自我”和“非自我”进行进一步甄别。处在这一阶段的孩子就像原始人,企图通过找出身体、身体功能和情绪之间的关联,来“解读”各种自然现象。根据对自身形象和对他人身体的观察,婴儿开始了解“男”、“女”两种不同的性别。这是婴儿发育的另一个里程碑。通过了解性别差异,即知道“我是男孩”或者“我是女孩”,“我”这个概念在婴儿头脑中得到强化。再通过辨别“我和爸爸一样是男的”或者“我和妈妈一样是女的”的过程,这个概念便变得更加具体。
在这一阶段,孩子对自己身体的感觉和评价显得特别重要。孩子对自己的身体以及体内排出来的物质会产生“好”或“坏”的感觉。例如,他对大小便感觉不好,觉得厌恶或害羞,甚至形成“我这个人招人讨厌”或者“我这个人就是没用”的感觉。孩子发现生殖器带给自己好感,但却会导致父母(以及宠爱他的人)不快、厌恶甚至惊恐,于是便觉得这种感觉不好、自己的身体不好,甚至认为自己也不好。同时,由于孩子对男女性别的感受与他对自己性器官的感受有关,因此,讨厌自己身体的孩子也可能会由此讨厌自己的性别。怪不得如今的性教育强调:培养孩子对自己身体的正确态度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基础。
到了三四岁左右,当孩子知道自己是“谁”并能从观念上对“我”进行某种程度的组合时,其智力开发将会由于碰到一系列问题而受阻。他开始知道每件事都事出有因,于是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他希望了解某种物品的制作过程。最令他着迷的问题,则是他自己是什么材料做的、他是从哪里来的。
5岁的谢莉问:“我出生之前在哪里?”妈妈回答:“你不记得了吗?我告诉过你。”谢莉说:“哦,我不是指那个!我是指在你身体里长出来之前。”
妈妈顿悟:“哦,那时你还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受精卵。”“我不是指那个。我是指我还是一个很小的受精卵之前。”“哦,你是这个意思啊。要知道,你在那之前什么都不是。”谢莉叫起来:“什么都下是?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是呢?”可见,母亲给谢莉各种各样奇怪的解释,最后一个最为奇怪。是啊,她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是呢?她无法想象自己尚没有存在时是什么样子,就像无法想象生命的终结是什么样子一样。其实,大人也无法想象此类问题。诗人济慈就曾写道:“不存在带给我无比恐惧……”,莎士比亚也提到过“存在或不存在”之类的字眼。一个人的性格是否刚强,就看他对死亡有多么恐惧。当孩子完全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的时候,“不存在”的想法将通过两种方式进入他的头脑:一种是生命的开始,即“我出生前在哪里?”;另一条是生命的终结,即“人死之后会怎么样?”。从这两个角度,他不停地问各种问题,我们也试着给出各种答案。但很显然,他不满意我们的回答。问题在于我们的答案不恰当,所以才会激起他更强烈的好奇,甚至自行炮制一套理论。简言之,他根本不相信我们说的话!
我们告诉他:“一个很小、很小的受精卵……”。“有多小呢?”“哦,小到用肉眼也难以看到。”(我们也许用铅笔在纸上画个小黑点来形象地比较。)但这种做法只会加深他的怀疑。对四五岁的孩子来说,白鹳送子(传说这种鸟能带来孩子)的故事甚至更为可信。也许蚂蚁可以从那个很小很小的卵生出来,但他不相信自己也是那样来到人世的。因此,他会大刀阔斧地修正这一事实,并提出自己的理论,例如,他可能把这个卵想得像鸡蛋或者鸵鸟蛋那样大,因为对他来说,这种尺寸的卵还说得过去。
至少两个时代以来的性教育,都在向孩子介绍性知识时采用类似于“父亲播种”等间接委婉的词语。在没有大人引导的情况下,许多孩子信以为真,甚至因此而误触法网。一个缺乏想象力的6岁男孩从商店里偷了一袋南瓜子,连包装都没有来得及拆开,就整包种在电线杆下面,期待来年夏天他的小女·友能生出个孩子。另一个小朋友通过了解植物授粉知识,推断出“原来父亲的种子是吹进母亲体内的”播种理论。有的孩子则将生育归功于现代科学的进步,因此经常趁机向医生咨询。
我经常饶有兴趣地请孩子们解释他们的播种理论,他们也都欣然应允。以6岁的比尔为例。虽然不确定医生具体做了什么,但他知道医生确实对父亲动了个小手术,然后把父亲的种子植到母亲体内某个“恰当的地方”。“那是什么地方?”我问。比尔答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值6.4万美元”,然后很谦卑地向我鞠躬。马尔沙的理论就没这么复杂了。“首先,医生要从父亲体内把种子拿出来。”“那么医生是怎么做的?”“我怎么知道?”随后他指出,种子可能是一粒药丸,由父亲交给母亲服下去。马尔沙养了一只公猫、一只母猫和三四只小猫。我问他,“公猫和母猫是怎么生小猫的?”“哦,它们是交配的!你应该知道!”“难道它们不需要医生帮忙吗?”“不,当然不需要!狗和猫不需要找医生帮忙生育,它们就是这样交配的。只是人不能那样做!”
用此类“父亲播种”理论进行性教育依然有很多缺陷。那么,实话实说又如何?事实证明,对孩子讲实话是可行的,只是五六岁的儿童不太容易接受这种事实。有一次,我花了几周的时间,向一个小朋友介绍父亲的精子如何进入母亲体内,他听了之后,露出一脸狐疑的表情说:“哦,也许有些父母会做这种事,但我爸爸妈妈绝不会那样做!”
这个孩子的反应是否证明他神经有问题?是否曾经有人向他灌输性行为可耻的观念?不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一个正常的孩子在头一两次听到这种事的时候,都会有类似的反应。他们也许不像前面那个小朋友那样直接拒绝这一说法,而是用其他方式加以拒绝,比如在知道后不久就装作忘掉这些事。
甚至连最开明人家的孩子,也不愿相信父母之间有性生活的事实。就算他们从在校教育中掌握了人类生殖的知识,但仍然很难相信除生育目的之外,父母的性生活竟然还有其他目的。对他们来说,只为了肉体享乐便沉浸于柔情蜜意的性生活中,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无论大人怎样解释,由于孩子没有亲身体验过,也没有这方面的想象能力,因此仍然认定性交是一种侵略行为,是一种令双方都感到痛苦的行为。有关“进入人体”之类的体验,孩子只能想起“去医院打针”的情景,怪不得他无法想象“做爱”这种让人如此“痛苦”的行为,竟然能让父母乐在其中?他认为,发生性行为只是为了生孩子,而不知道父母竟能“享受”鱼水之欢。这使我想起另一个故事。有位母亲已经生有两个孩子,再过两个月就要生第三胎。6岁的凯蒂问:“妈妈,是不是有些父母想要生孩子却生不下来?”母亲回答:“是啊。”凯蒂接着说:“还好我们家很幸运。每次你和爸爸想要生孩子,都能成功地生下来。”母亲默然。
每当我们试图用解剖学知识,为孩子示范精子和卵子的结合过程,希望他们了解人类生殖知识时,都会很快发现他们反而更加满头雾水。还记得比尔那个以为必须动手术才能取出精子的小男孩吗?我问他为什么需要动手术,他悲伤地说:“因为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把精子取出来。”“为什么?”“因为父亲的种子太大了。”“有多大?”“哦,大得像大理石那样。”“像大理石?你怎么知道?”“我看过图片,就在教科书里。”看到我对他的理论不以为然,比尔显得很生气(这种年龄的孩子已经对教科书奉若至尊)。“比尔,你能凭记忆描绘一下教科书里的精子图片吗?”比尔欣然同意,然后画出一个大理石大小的精子,还有一条尾巴附在后面。对比尔这么聪明的孩子而言,教科书里的精子是高比例放大图但比较可信,而真正的精子需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到,小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两个事实相互矛盾,令他颇感困惑,比尔宁愿相信用高比例放大的那张图片。你或许会问:他怎么会有这种想法?那是因为“眼见为实”,他只能相信大理石那么大的东西,而不会相信肉眼看不到的东西。
当孩子刚刚从虚幻空间进入现实世界、懂得“眼见为实”的道理时,当他正开始怀疑那些神话故事,因为它们“看不见也摸不到”时,大人描述的人类生殖过程,不是再次带给他一种新的困惑么?大人一再强调精子和卵子是客观存在,可是孩子什么也看不到。他无法想象母亲能生出这么大的婴儿,更无法想象神秘的性交过程。因此,那些被父母视为“无所不知”的天才儿童,掌握的知识其实往往非常有限。
以上所述的孩子对性知识的种种反应,都证明我们引以为傲的性教育原来竟有如此多的缺陷。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放弃现行的性教育方式,再回到原来的童话式教育轨道呢?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我们应当进一步了解孩子对性的看法,以便找到更适合需要的教育手段。如果孩子无法完全理解我们提供的性知识,我们就必须设法纠正。一旦真正了解了孩子在特定成长阶段的心路历程,自然就能找到更科学的教育方法。
青少年的性教育
我建议教育工作者多利用生物学知识。老师不妨带孩子们观察母鸡孵蛋过程,并利用这一机会回答他们的问题。
有位老师曾经告诉我,由于青少年已经了解所有其他事物,因此唯一能真正“教”给他们的只有性知识,另外,性方面的话题是纯洁的、值得尊重的。从那之后,我一直大力提倡开展性教育,一有机会就鼓励孩子不必忌讳和老师讨论相关话题。然而,在研读一些文献报告以及性教育课程、指导手册之后,我又开始对其中的部分观点持怀疑态度。考虑到当今社会流行的某些想法已经在这些性教育教材中得到体现,这迫使我必须出面表明立场。简言之,我不认为目前的性教育具有建设性,而觉得应当在讨论“怎样教”之前先检讨一下教材的内容。
大家都知道,亲密的性行为是在特定生命阶段和特殊场景中发生的。它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但也可能是另一个极端,如调情或情绪的宣泄。无论怎样发生性行为以及何时发生,这种行为的意义都不仅仅是身体接触。从轻微的接触到发生真正的性行为,从互相调情到夫妻同床做爱,都与“人”这个主体有关。在性行为过程中,“人”或“自我”必不可少,因为人的情感、欲望、意图等心理因素一定会伴随着身体,共同参与性行为。
人们经常忘记这条最基本的道理。这与青少年的性教育题材直接相关。除了这一点,与个人性行为以及性教育课程有关的,还有“社会的性观念”课题,亦即大人对性的态度、认知和行为。大人的性行为以及谈论性的方式,都是一个社会“性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今社会性文化的主题,已经变成“包括老师在内,为什么许多人对性教育表现得如此忧心忡忡”。
性教育的提倡者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性病流行、未婚先孕的比例剧增。他们指出:“没有人希望得性病以及未婚先孕,因此有必要提倡性教育。”另外,有关“避孕药的使用量减少,未婚先孕的比例增加”的新闻报道同样令人触目惊心。于是,人们更有充足的理由推广性教育,以为这样一来便能减少未婚先孕的比例、性病的案例以及提高青少年的警惕性。
然而我却认为,当今性教育最大的缺失,就是没有触及“减少性行为”这一课题。性教育普遍谈到青少年应进行“更负责任的”、“更明智的”、“更有计划的”以及“更谨慎的”性行为,却从不提及应当减少性行为。性教育建议青少年必须小心、谨慎,却从不建议他们自我控制。
当今社会传递给青少年的信息非常明确:只要不得性病,只要不怀孕,发生性行为没什么关系。由于缺乏经验、不负责任或事先未做好准备而导致怀孕,当然不是好事,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青少年从大人“导师”那里学到的是错误的观念,即怀孕基本上是件坏事。久而久之,他们对这一观念更深信不疑。这就是我们下一代的想法。如果他们的妻子“不小心”怀孕,将被他们看成是一件坏事。
当今性教育导致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青少年早已将性行为和人类生育看成两件毫无关联的事。青少年认为,性行为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与其他事情无关。只要避免怀孕、不染上性病,大人不会过问。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观念。早在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诺斯替敦派(基督教早期出现的神秘主义异端)就喊出了“任何时间、任何方式的性行为都与传宗接代无关”的口号。看来,当今的性教育已经成为诺斯替教派在20世纪的翻版。
许多有关性教育的手册和教材都深入探索“性的本身”并引以为傲,却有意对应当克制、明辨是非之类的正当理念避而不谈。这种让人自我陶醉的教材已经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其数量和种类多得惊人。这些欺世盗名之作的内容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有一本专为3-6岁小女孩写的书名叫《我觉得身体很好》,其中提到:“吸吮手指、摩擦双颊令我愉悦……。我喜欢玩弄阴核。”另一本《学习性功课》则写道:“性是一个人最有趣的一部分……。手淫是称颂人体的活动。”在另一本备受赞扬的《青少年与性》的大作里,加州大学的简森博士这样写道:“尽管在多数时候,性离不开爱情和婚姻,但也不应该让爱‘搞乱’性课题。……女方不小心怀孕称为意外,未婚男女不小心早孕称为悲剧。……手淫是完全健康、正常和令人快乐的。……我再次强调,手淫次数太过频繁于身体无·害。……还有什么性活动比手淫更安全、更不会产生不良后果、更不复杂呢?”
此类性教材有两大误区。第一,它们在说谎。正如我一开始所说,任何性行为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包括自我、感情、欲望等。如果将性看成一种“自然、正常、快乐的活动,并且与其他事物无关”,则纯粹是误导。所有社会都了解性和人的关系,并以这一原则规范人与人之间的性活动。其实,多数人都相信诸如性之类的神秘活动将触及人的灵魂深处。惠特曼指出:“性包括人的全部。从肉体、灵魂、意义、证明、纯洁、敏感、结果,一直到宣告,都与性密切相关。”从古到今的诗人、小说家、哲学家、圣徒以及多数心理学家,都深刻了解性之所以与众不同,乃是因为它具备独特的美、力量和特质。性可以是爱与承诺最深层的结合,也可能导致强暴、谋杀、自杀,但绝对不会“仅仅是”一种“自然或好玩的活动”。性是严肃的、复杂的、微妙的、神圣的。
第二个误区是:它教导青少年只要能避免不良后果(即性病和怀孕),即可以放心大胆地从事性活动。结果呢,性便成了青少年一心向往、但做起来却毫无意义和目的的活动。性泛滥乃至性病成灾的最终后果,是使得人人自危,于是只好效仿中世纪教士式的禁欲主义。人类曾经发生过这种事,将来还可能再次发生。
面对如此险恶的教育环境,老师应当怎么办?我们当然要扬弃如今荒诞不经的性教材,但也无需一味地谈性色变。例如,有个孩子问父亲“女子色情狂”是什么意思,被父亲痛骂一顿。父亲不仅命令他去漱口,还严禁他再往这方面瞎想。躲避性问题和提供错误观念的后果同样严重。
我建议教育工作者多利用生物学知识。老师不妨带孩子们观察母鸡孵蛋过程,并利用这一机会回答他们的问题。也许与复杂的人类生殖过程相比,母鸡生小鸡的故事过于简单,但打好了这个基础,孩子将会产生敬畏心理,从而树立对生命奇迹的严肃态度。另外,我反对在孩子们不可能有兴趣的时候详细介绍性行为的过程,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
等他长大到一定年龄,我建议采用一对一的教学方式。传授性知识和答疑解惑的人最好是孩子最亲近的人,比如父母、神父、老师、教士等。性教育不适合公开讨论,而应当由一个肯抽出时间、肯付出耐心的人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教导。也许这种简单而又重要的途径是纠正当今社会性教育歪风的唯一办法。
(成廉·班奈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