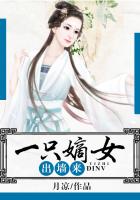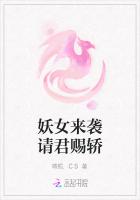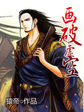腰店子的寡妇不止奶奶一个,总共有三个,一个前屋场的程秀奶奶,一个是后屋场的赵家奶奶,但这三个寡妇中,只有奶奶守得是真寡。程奶奶丧夫后,暗地里交往了一个男人,那男的每次都是夜里来天亮就走,这种叫露水夫妻;赵奶奶也有男人,男人十天半个月来一次,小住一两日便走,或者赵奶奶十天半个月去男人那头,小住一两日便回,这叫两来两走,不论是露水夫妻还是两来两走,到后来各自的儿女大了成家立业了,关系就渐渐断了。
记得小的时候,程秀奶奶和赵家奶奶与她们男人都还保持着紧密联系,因为每次她们男人来后,奶奶都要兴冲冲地跑去看看,或者她们来串门,奶奶就会格外殷勤地端茶倒水留她们多坐会儿,聊天时,奶奶会很自然地把话题往男女之事上引,顺着谈话间的脉络往更隐秘的纵深间挖掘。那时我还小,在地上起劲地拍洋画,我伪装出来的天真令她们对我失去了防备,其实那时我已经人事渐省,隐约地知道了许多男女之事。奶奶在听这些谈话时,虽正襟危坐,面目清高,但她的眼神里透着不可名状的兴奋感,而且时不时地她们还会压低声音地笑几声。两位奶奶走后,奶奶的兴奋感便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落寞与哀伤。
早年间的三个寡友到老了成了牌友,后来村里一个拾荒的鳏夫搀和进来,就凑成了麻友。闲暇时的中午或傍晚,他们就会在我们家稻场前支起一张蓝漆桌儿,鳏夫不来的话就打花牌,鳏夫来了的话,花牌撤下去换成麻将,四个人一人一杆烟袋,一人一杯浓茶,就着手绢里层层包裹着的毛角票,一打就是一个下午或是一天。
稻场前有棵紫桐树,是爷爷当年栽的。那树长得虽然不是亭亭如华盖,但是因枝杈横生,相互交错,且叶子肥厚宽阔,密密匝匝,那一片浓荫快赶上半个堂屋的大小了。到了夏天,除了下雨和来客人外,我们家的晚餐多半都是在紫桐树下吃的,隔着前面池塘吹来的南风,就着树上的声声知了,即便是最简单的稀粥咸菜也别有一番滋味。
我喜欢中午在紫桐树下待着。阳光被桐树叶子筛得细细的,投到地面上,星星点点,明而不喧。枝桠低垂有如一道帘子,一走进来就如走进了一个怀抱。父亲后来又请人围着树做了水泥,拾掇得干干净净,大早上的,父亲就会带上收音机在树下边听《美国之声》,边做些保健运动。
奶奶她们打牌也喜欢选在树下打,说是清净,其实一点也不,那树下人气旺着呢。一开局,桌旁就围了一圈人在旁边指指点点,若是指点得让奶奶输了牌,奶奶便会破口大骂,村人并不计较,依然说说笑笑。若是到了初夏,紫桐开了花,村人在树下敞亮地打几个哈哈或是高声说几句话,就会震得那些花三五朵、六七朵地扑簌簌往下落,有时落在人的头顶上,有时落在脚边上,有时落在奶奶他们的牌桌上,甚至是茶缸里。巧的,落在人嘴巴里也是有的。那花是紫色的,样子如牵牛花般,但是不像牵牛花妓女似的将花瓣张着。紫桐花的花瓣是向里收的,如教养极好的闺阁小姐,含蓄而温婉。自从我在阁楼上粗读了几章《红楼梦》后,我就对那些花生出了怜惜,将那些花捡了埋在前面橘园里。父亲后来发现我葬花后,大发雷霆,将我从橘园里揪了出来,一把掼在稻场上,说我下作。这样美好的事在父亲看来是有毒的,是我应该远离的。
奶奶他们打牌时,经常会说些村里的旧事。奶奶说她搞集体挣工分,吃了不少苦头,不会插秧不会割稻不会挑担不会播种。她在生产队里经常受捉弄,她插秧极慢,她插一行别人插一垄,经常等她插完身边的秧直起身一看,她已经被四周插好的秧苗给包围了,令她在田中间动弹不得,她在田里叫喊,回应她的却是田埂上响亮的笑声;她也打不好连枷,那时村里收割的绿豆或是麦子什么的,就要靠连枷来脱粒,连枷是竹制的,上面的枷板是用大小相等的竹片绞链而成,按在枷柄上,用的活轴,枷柄长长的,使用的时候要使枷板绕枷柄旋转,奶奶使不好连枷,她的枷板总跟枷柄纠结着,打下去,要不就是软踏踏的,要不那枷板就是站着的。队里打连枷都是妇女,一个稻场铺满麦子,十几个妇女围着一起打,打一下走一步,我的奶奶经常是连连枷都还没举上去,就被人催着要往前挪步了,到最后奶奶只得背着连枷跟她们跑,有时跑慢了还被她们排挤出去,这样的干活,所挣的工分是可想而知的,奶奶那时还有四个孩子,可见日子恓惶到了什么地步。
母亲说,幸亏二爹,爷爷死后,成为家里顶梁柱的不是你爸爸,而是二爹。
我问,日子这么艰难,奶奶怎么不改嫁呢?
母亲说,好女不嫁二夫,你奶奶有这个志向。
后来,我听母亲说,村里那个拾荒货的鳏夫对奶奶动过心思。那个鳏夫姓蔡名秋,村里人都叫他秋老汉。听村人说,我爷爷在世时与秋老汉关系甚好,早年间,秋老汉在腰店子的长街上做饭馆生意,隔三差五地就整些卤猪头肉和花生米到药铺来与爷爷对酌。秋老汉好酒,我爷爷也好酒,不同的白酒他们喝一口,就能断出是哪种酿造工艺,是采用的什么水,陈了多少年头,是头道酒还是二道酒。只要我爷爷一说,秋老汉就会拍案击掌,说,神了,神了,祝先生真神了。两人话也投机,秋老汉将我爷爷视为知己,人前人后对我爷爷的称呼都是一口一个祝先生。后来秋老汉还自己开酒作坊,酒酿好后,无论多晚都要请我爷爷尝头道酒。慢后,奶奶来到了腰店子,第二天,秋老汉到药铺来,看见药铺忽然间多了个穿洋布旗袍的年轻女子,竟愣了老半天,说,哎呀,这不是前儿请来唱《白蛇传》的小海棠吗?我奶奶不说话,虽然从话音里听出来者是在夸她的美貌,但是她很反感别人拿戏子来比她。
我爷爷从碾药房里走出来。说,秋老弟,这是嫂子,雷十三家的大小姐,岂是戏子能比得。
秋老汉顿时明白过来,说,哦,原来是先生娘子,就是春林大爹的干女儿?听说是大学问啊。秋老汉像是想起什么了似的,说,你们等着。猛然掉转身就跑了,不多会儿,就端了个漆木盘,后面还跟了个伙计,手里捧着个盖篮。
那是一桌精致的酒席。秋老汉将三个粗瓷碗倒满了酒,头一碗递给奶奶,客气道,先生娘子,我跟祝先生如亲兄弟般,我知道你是独身一人来腰店子的,既来之则安之,我蔡秋不敢说别的,但我敢保证,先生娘子在腰店子不会受欺负。来,我干了,先生娘子不会喝就别勉强。
哪知道,我奶奶一仰头也给干了,反身又给自己和蔡秋倒满了。奶奶说,我从昨儿个晚上就是腰店子的人了,死了也埋在腰店子的地界上。干!话一说完,我奶奶就向秋老汉亮了碗底。
秋老汉竖起大拇指,赞道:先生娘子好酒量!
此后,秋老汉来药铺越发地勤了,在没有病人的午后,三人在药铺堰边的小院子经常喝的醉熏熏的。有时候爷爷出诊去了,秋老汉也不避讳,有点好菜也照样端过来,跟奶奶对酌,奶奶也不避讳,反正门大开着,药铺里还有俩学徒呢,来喜也在院子里蹲着,俩眼睛瞪得如铜铃一般,生怕错过一块丢下的骨头。爷爷出诊回来了,看到这样的情形也不恼,捡起酒杯便倒酒,然后跟秋老汉谈一些人生无常生死由命的话来。
一九四九年后,腰店子的长街就被撤了,在街上做生意的人便沿着自己的田地盖房子,秋老汉本来是想着把房子盖在我们家对面的,可是他女人不同意,说俩酒鬼挨在一起,日子甭过了,以前开饭馆还有些个活钱,眼下还不知道是个什么世道,哪顿顿有酒。这样一闹,秋老汉就没有与我们做成邻居,他们到最西边的王家屋场那里盖了两间偏厦。
偏厦刚落成,秋老汉的女人因上梁取东西,一脚踏空给摔死了。秋老汉的儿子才七岁,没了女人,秋老汉的日子就恓惶起来,衣裳因洗得不勤,颜色发污,虽说有些力气,可是又不会干农活,田地里收成也差,孩子跟着秋老汉饥一顿饱一顿的,孩子如果玩到爷爷家来了,爷爷总要留他吃饭,完后还盛一碗饭菜让孩子带回去给秋老汉。靠着这样的接济,秋老汉父子俩度了四五年,后来搞集体,秋老汉因认得几个字,算账厉害,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后来又成了队长。在秋老汉成为队长的第三年,我爷爷就死了。即便是在没有粮食吃的年代里,秋老汉也没有断过酒,当年开饭馆酿的酒,有好大几缸,埋在他家屋前的槐树下,有年槐树花开,花下死了一大片蜜蜂,原来那槐树根伸到了秋老汉的酒坛里,开的花也满身酒气,把蜜蜂给醉死了。
村里人都说,我爷爷死时抱在怀里的半瓶酒准是秋老汉给的,还有人说,我爷爷是秋老汉给害死的,明知道我爷爷一喝酒就头晕,两眼发黑,还给他酒喝,这不是害人吗?但是我奶奶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爱酒的人早晚得死在酒上。
爷爷死后,奶奶的日子举步维艰。爷爷在时,靠开药方抓药顿顿还能吃上南瓜煮白米。爷爷死后,学徒也散了。那些药,奶奶虽认得,但是不懂君君臣臣的用药之道,药也就跟着死了。家道彻底败落,每天的饭食就是南瓜和红薯,再后来就是野菜。奶奶说,连沟边长的矮脚榔树的树皮都被她们孤儿寡母的吃光了。那时,一家人出去,脸上都黄晶晶的,似乎一掐就能掐出水来,都是严重肌饿造成的。我的父亲那年十五岁,正在二中读书,二中就是次勋舅爷爷办的向上中学。二爹十二岁,大姑十一岁、小姑才九岁。二爹和大姑小姑经常为几粒粮食与别人大打出手,到了收割季节,每次回家,虽然手里拽着几棵稻穗,但是脸上身上却是淤青一片,奶奶每次接过那些稻穗时,都忍不住要落泪。
二爹那天又为捡了生产队几根稻穗跟王家屋场的大升起了争执,后来大升的爹王武和掺进来,王武和要从二爹手里夺稻穗,我二爹使劲拽着,就是不撒开,姓王的居然抽了我二爹一耳光,我二爹什么样的人,腰店子出了名的混账,发起脾气六亲不认的主儿,今儿被人扇了耳光还得了。我二爹将手里的稻穗一把摔在姓王的脸上,然后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周围有人劝架,说王大叔这么大年纪不该招惹我二爹,几根稻穗捡回去也填不饱肚子,何必跟永高较真呢。也有人叫我二爹松手,但二爹死活不松,他说,我今儿既然动了手,就得动出个样子来,还真以为孤儿寡母好欺负了。二爹说话间,一使劲,将王武和给推到了旁边的双堰塘。
奶奶闻讯赶来,看着在水中扑腾的乡邻,吓得瑟瑟发抖,她在岸上给他作揖,向他赔不是,一面招呼人下水去救,一面强按着二爹给王武和跪下。我二爹断不肯跪。他将岸上的奶奶给生生拖回去了。二爹高声叫道,你今天淹死了,老子明儿就给你抵命。到了晚上,王武和领着一伙人来到奶奶家,扬言要把狗日的永高沉到双堰塘。我二爹还想出去斗狠,我奶奶一把将他推到收拾屋里锁了起来。
门开了,王武和一干人气势汹汹地问,永高呢?王武和不是腰店子人,是招赘来的,他带的那伙人就是邻村他娘家人。
奶奶说,凡事有个分寸,他再错是个孩子,你再有理,你是大人,你这样闹,也不怕人笑话。你带这么多人来我这里,无非欺负我是个寡妇,但我今儿还真告诉你,我这个寡妇还不好惹。
那人的气焰矮了一些。说,我不跟您说话,您叫永高出来,我们找他算账。
奶奶说,养儿不教父之过,他爹现死了,你们只能冲我来,永高他就在这屋里,你今天把他怎么样了,我立马照样儿地还给你,你别说我护短。奶奶将锁打开了,说,永高,出来。我二爹拿了根冲担杀气腾腾地出来了。奶奶一声喝下,说,放下,你今儿要是没了,妈让他姓王的拿两条命来赔。
二爹便将冲担放下了。奶奶说,永高出来了,你处置吧。
围观的邻居开始劝导,说一个村里的抬头不见低头见,祝先生走了才一年,就这样闹,实在是不应该。王武和的女人来了,也劝自个的男人,僵持了一会儿,王武和自觉无趣,领着一干人骂骂咧咧地走了。
奶奶准备关门睡觉时,秋老汉来了。秋老汉的怀里还抱着一坛酒。奶奶迟疑了一会儿,还是让秋老汉进了屋,秋老汉进来后将门顺手掩上,奶奶却将门打开。秋老汉有些不自在,奶奶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你不要见怪。奶奶让秋老汉坐,秋老汉落座后有些拘谨,跟往日的潇洒做派大不相同,一副有话要说又欲说还休的样子。
奶奶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有话就说吧。
秋老汉说,今天的事儿难为你了,我想为你出头,但是确又不便。
奶奶说,我屋里有出头的人。
秋老汉说,昨儿晚上祝先生给我托梦了,要我照看你们呢。
奶奶说,你不是一直在照顾我们吗,不是你跑前跑后,永泽那能到二中去读书啊。
秋老汉说,这不算什么,你在东头,我在西头,两家离得远,多少还是有照顾不到的地方,要是,要是……
奶奶说,这就够了。
秋老汉说,先生娘子,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想让你们一家少挨饿。
奶奶说,秋老弟,我们相交十多年了,缘分难得,他爹爹去世前三年,也就是你当队长,正是饿肚子的时候,他爹爹说是给人看病得的粮食,其实我都知道,那些粮食都是你给的,跑去湖南看病,只不过是个障眼法,这些好,我们一直都记在心里呢,若要这样的好一直好上头,其他的话就不要说了。
秋老汉起身了,桌上的煤油灯晃了一下,映在秋老汉眼里的光也随即变暗。秋老汉在堂屋里站了一会儿,便出去了,走时,他将门给严严地合上了。
奶奶上前,将吊着的门闩一把插进了杠道里。
没几天,因为下雨,秋老汉指挥生产队的人将抢收的粮食堆在奶奶屋后的稻场上。秋老汉对奶奶说,先生娘子,把您稻场借一下,这抢暴呢,时间不等人啊。奶奶说,行,堆吧。这一堆就堆成了定局,此后奶奶家的稻场就成了生产队堆粮食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