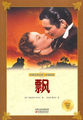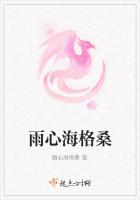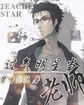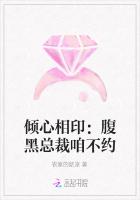其次是李家湾的人没有完全的文盲,就是我母亲的奶奶,我的老外婆高龄九十的人了,她都知道写自己的名字也能算些简单的账目,比腰店子的人强多了。腰店子别说老一辈了,就是到了我们这一辈,也有很多孩子连学堂门都没进。父亲每到开学就各家各户去劝说,讲一番知识改变命运的大道理。但人家问我父亲,祝校长,字能饱肚子么?问得我父亲四门倒地。李家湾的人都非常爱读野史野书。他们那的人个个都知道梨山老母,个个都知道薛丁山,也个个都知道李自成,连毛头娃娃都能讲冲冠一怒为红颜和李闯王“三年不征、一民不杀”的传说。父亲说李家湾是个典型的半耕半读之村,民风淳朴,崇尚文化。
还有我的母亲也喜欢读书,事情忙完了,她就早早地把自己捡到床上读书。当然母亲读的大都是小说传奇之类的书,什么《隋唐演义》、《长生殿》、《彭公断案》等。母亲的阅读习惯一直保留着,后来母亲的阅读水准大有提高,竟读起了《红楼梦》,遇到不认识的字总问父亲,父亲问烦了就给母亲买了本《新华字典》,扉页上还提了字,“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祝永泽赠爱妻李慧玉。母亲靠着这本字典把《红楼梦》读完了,她说《红楼梦》里她最佩服的就是王熙凤,可怜那么大家子人,全靠她一个人劳神谋划,上上下下都治理得不错,实实地不简单。我上大学后给母亲推荐陈忠实的《白鹿原》,母亲喜欢得不得了,读得不舍昼夜,她让书中那个朱先生给深深震撼了,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似乎在以朱先生“慎独”的标准在做人。以后,母亲便迷上了《圣经》。我买《圣经》原是打算当外国文学来读的,但是只读了两页就读不下去了,但母亲却入了迷。夏娃跟亚当是怎么一回事、诺亚方舟是怎么回事、出埃及记是怎么回事,这些都是母亲跟我讲述的。并且母亲对书特别爱惜。她读书之前必定洗手,从不用手沾口水去翻书,也从不在书上折印子来标示记号。上小学的时候,有次我把我的语文书坐在屁股底下,母亲一把揪住我,说,书怎么能坐在屁股底下呢,那些字都是孔夫子的眼睛。母亲说这句话时,把我奶奶和父亲都镇住了。
后来我才知道李家湾是有来头的。居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人都是李自成的后裔。当年吴三桂造反追赶的就是他们的先祖。听母亲说吴三桂当年杀李家的口号是杀至外国龙断桥,一路杀来,血流成河,连藏在树洞里的人都杀了。可巧的是洞庭湖边上刚好有个桥叫龙断桥,说这才放了刀剑。李家先祖沿洞庭湖而居,才得以让这支血脉繁衍生息。
我不信,我说,洞庭湖在湖南啦,离这十万八千里,还洞庭湖呢。
母亲说,洞庭湖有多大你知道?八百里洞庭,是现在填湖造田修路把地势改变了,上早湾里那条土坝是一座山呢,那山比泰山矮不了多少,几百年前的事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能有假。
可能是因为祖宗们是避祸乱而居在此地的,为了明哲保身,这里的人的性格大多是忠厚本分,不传是度非,即使吃了亏也不嚷嚷,很善忍。奶奶之所以三番五次到李家湾上母亲的门要她做媳妇儿,估计也是相中了这方水土养育出了这种性格的人吧。而母亲在奶奶面前也确实做到了忍让,她在祝家一直都是忍辱负重。她心里也一直念着她这个媳妇是奶奶选的,是一种知遇之恩,只是三顾茅庐,境遇有别,诸葛亮成了军师,而她却是祝家的奴仆。奶奶在公众场所都口无遮拦地讲过,慧玉就是祝家的长工。
这样的话传进母亲的耳里,母亲也很冒火,但母亲表达冒火的方式了不起皱一下眉头,鼻子里哼一声。其实这话对于母亲所听到的来说,还算是轻的了,奶奶曾当面说母亲,说,永泽娶的只不过是一个蹲着屙尿的。母亲当时气得不行,但也没看她起多大的板儿。
奶奶一度在这样凌辱的言语上占着上风,她肆意欺负母亲,她说母亲到底是穷门小户出来的,一碗米汤像命根子,前世里是狗子托生;说母亲一红黑就睡,是两魂没还到阳间的关门眨。这些话母亲统统忍了下来,因为母亲的事情太多,跟她顶嘴,田里的活儿要耽误一大半。父亲也厌恶奶奶的要强,站在儿子的立场上也大过言语地讲过他的母亲,奈何他的母亲大人总是高高在上,这令父亲很是为难,有时为了略表孝心,不得不违心教训母亲以讨得奶奶气顺。
我的大姑小姑当时还没出嫁,她们总是站在奶奶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地挤兑我母亲。家里唯有二爹是个直爽之人,经常为嫂嫂抱不平。二爹性情不好,脾气暴躁,一不顺心便摔东摔西,家里谁也不敢惹他,所以二爹在家时,经常把他的娘和两个妹妹压制得连大气也不敢喘,唯独对母亲很尊敬。母亲做菜咸了,大姑小姑嘀咕,二爹就将她们手里的筷子夺了过来,说,咸,你别吃。要是菜淡了,大姑小姑裹筋,二爹便舀一勺盐放在她们碗里,说,做又不做,别人做好还嫌这嫌那,有碗菜吃还得亏了嫂子,以前桌子上有黄瓜、豇豆吃吗?我们的妈连支架都搭不好,园壁子做的连猪都跑得进去。说得一旁的奶奶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又不敢发言。
母亲对这个小叔子也是另眼相待。小叔子上门去给人家做女婿,她从娘家姐姐那儿背来两麻袋棉花为小叔子弹被絮,还卸了家里三块门板偷功摸夫做糨子打布壳,为小叔子在灯下赶制了四双鞋,还为小叔子绣了四双鞋垫子,花样儿都是万福到头。二爹与二妈出门时,二爹只说了一句话,说,你们如果不对嫂子改观点,你们就真黑了良心。
大姑小姑出阁后,母亲稍微宽松了些,但依然是在奶奶的胳肢窝下做人。直到我出生懂事了,母亲在家里才算真正多了一股势力。我跟二爹一样的性子,看不惯持强凌弱的事儿,只要母亲与奶奶开战,我就会无条件站在母亲一边,亲戚来对质,我就会为母亲作证,数落奶奶的不是,一二三说得头头是道。奶奶因此送了我四个字的评价,钉矛铁嘴。
我是家里的混世魔王,连一家之主的父亲也奈何不了我。小学二年级的《自然》课有一节生物链,我看懂了,我把我们家的人也弄了个生物链。放学后,我向母亲显摆,我说,我们家奶奶怕哥哥,哥哥怕爸爸,爸爸怕我,我怕您,您怕奶奶。母亲一双手齐齐挥舞说,这屋里的人,我都怕,都比我狠。
其实母亲也狠,平时母亲虽然不说粗口,但并不代表母亲就不会说粗口,母亲说起粗口来,连唐僧都要破戒的。有回我们家菜园子的一垄青椒和茄子被人偷了个精光,连秧子都弄断了。母亲从厨房拿了块菜刀和砧板出了门,一边骂一边剁。母亲骂牛鸡巴日的,狗鸡巴养的,上日祖宗的十八代,下日十八代的祖宗,每一句不带重样的。就这么从村头骂到村尾,又从村尾骂回来。直骂得腰店子大路小路没了人影,芭芒林子里鸟雀都禁了声。
那天,奶奶在厨房里做饭,我坐在柴匣子边上给她烧火。我明显感觉到奶奶的害怕。沥饭时,她的手在颤抖。她终于见识了母亲的厉害,母亲骨子里从来就不是懦弱之辈,她的本分是来自于她的修为。当母亲回来把砧板和菜刀拿回厨房时,奶奶以一种讨好的口气说,慧玉,案板上有碗米汤,刚沥的,我放了糖,你喝了吧。
当母亲捧碗喝米汤时,我看到母亲的嘴角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
此后,奶奶果真在语言上收敛了很多,那些伤人伤得生疼的话再也没有出口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奶奶就不压制着我母亲了。奶奶从言语上的冲突转为肢体上的了。只要跟母亲吵架,她的手指就像弹簧一般根根掸在母亲的脸上,有时候还会给母亲一个耳刮子。对于奶奶给母亲的耳刮子,村里大多数人都看见了。母亲从不还手。有次,我放学回来后,家里坐满了人,小舅爷爷大舅爷爷大姑父大姨奶奶都来了,我知道奶奶跟母亲肯定又吵架了。每次吵架,奶奶就会托人把她娘家人叫来为她撑腰,而母亲从来不叫舅舅姨妈,她总是独自面对众亲戚的质问、劝解、压制,完了还得到厨房给他们做饭吃。我向来就为母亲感到不平。我对那些以长辈身份压制我母亲的亲戚一向没有好感,他们来了,我总是仰进仰出。
奶奶坐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一只鞋底砸向父亲,说,永泽,这是你的好媳妇,竟敢打我。
父亲的眼光投向母亲。母亲说,我没打。
奶奶说,还没打,你把我按在床上把我打得半死不活,你鸭子死了嘴巴硬,你打人了不承认。
母亲说,还半死不活了,那您现在还能张口说话?
奶奶跪在地上作揖喊,雷公菩萨,你们睁眼看看,你们打死这个黑良心的东西。
村里立刻有人上去扶,说,麦先婆,别这样。
母亲对村人说,您们说说,我来了祝家七八年,现在儿长女大,我是什么样性格的人,她您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只有她经常甩我耳刮子,您们亲眼看见过的,哪一回我还过手。
村里有人作证说,是这样的,麦先婆伸手动脚惯了,这还是慧玉妹性格好呢,要是我,忍不下。
父亲说,您就不能消停下。田里事堆起来了,我一天到晚还要为您这档子事忙上忙下,大舅小舅也陪您瞎耽误工夫。
大舅爷爷说,姐,您的个性我清楚,慧玉的个性我也清楚,只有您欺负人家的,人家是不敢欺负你的,慧玉要真动手了,您不把她吃了。
众人散去,奶奶足足在床上怄了半个月的气。母亲也不叫她,只是一日三餐叫我把饭端到她房里去,另外送一开水瓶。
后来我问母亲是不是真动了手。母亲说,你奶奶是太不讲道理了,不给她点厉害瞧,她只怕不知道黄连是苦的。那天你外公来看我,大老远的,身上一身汗,我说给你外公冲一碗蛋花,我明明知道她抽屉里有四个鸡蛋,等我去拿没有了,我问她鸡蛋哪去了,她说上回借了程秀的鸡蛋,刚刚她来客了取走了。我知道她是撒谎,我便去问你程秀奶奶,你程秀奶奶说她家没来客。我便将情况一五一十跟她说了。连你程秀奶奶都说这个老太婆太过分,亲家大老远来,几个鸡蛋又不是稀奇,还藏着掖着的。你程秀奶奶用手绢给我包了八个鸡蛋,我拿回来全给你外公做了。你外公给你奶奶分了四个,你奶奶脸一扯,说,我不吃,怕吃了倒喉咙。你外公脸皮又薄,四个鸡蛋在碗里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匆匆吃完就走了。
你外公走后,我心里越想越疼。我问她,我说,妈,早上抽屉里的鸡蛋,您说给程秀大娘拿去了,我问了程秀大娘说没拿。我这鸡蛋是找她借的,您把鸡蛋给我我好还她。没想到你奶奶像是被人戳了癞痢一样,脚跳三尺,说我为了几个鸡蛋还跑去找人对质,说屋里的好东西全让我给贴娘屋里了。说着还准备上前来动手的。这回我火了。我将她一把推在房里,门一锁,窗户一关,一条毛巾朝她口里一塞。我把她按在床上着力搞了一顿。
基于母亲一贯所受的凌辱与欺负,我替母亲保守了这个秘密。狗逼急了还跳墙呢。
半个月后,奶奶下床了。
那天,母亲专程赶集到镇上割了一斤肉,买了一条鱼还打了一瓶酒。饭菜上桌后,母亲给奶奶斟了一杯酒,什么也没说。奶奶踟蹰了半天,还是将那杯酒喝下了。
此后,奶奶再也没有甩过母亲的耳刮子,手指没有再如弹簧般掸在母亲的脸上了。
§§§第五章
在奶奶那一辈人中,是很少有大脚的,但奶奶就是一双大脚。她跟大姨奶奶都是大脚,她们三姊妹中,只有小姨奶奶是标准的三寸金莲,据说脚小得在升子里(一种量米的器具)能转圈。这样的脚中看不中用,进进出出都得要人来抱,是有了名的“抱小姐”。在看一些电视电影时,发现民国那个时候,不裹脚的女人一般都是受了新思想影响的,但是地处偏僻的鄂西南角的奶奶,如何有这般勇气敢抵制封建的礼教呢。
奶奶说她不裹脚就是因为怕疼。本来四岁就要裹的,拖了两年,到了六岁上才正式裹足。裹足那天,春林大爹来了,送了一篮子熟食和果品,说是为奶奶压惊的。老外婆还专门宰了只母鸡,加川芎和当归炖得香喷喷的。老外婆从屋里牵出六条两寸宽三米长的棉白布条。奶奶坐在腰磨上,老外婆招呼两位舅爷爷,说,大文,大武,把你大姐着力按住。两个弟弟将姐姐的双手反剪扣在磨盘的转把上。奶奶瞪着一双牛眼横了过来,两个弟弟吓得赶紧低下头。布条还未上脚,村里就响起了奶奶杀猪般的声音。老外婆说,叫破天,今儿也得裹,拖下去骨头成型了就裹不住了。不少村人都过来观看奶奶裹脚。还给老外婆出主意。说,婶娘,大文大武怎么按得住,得拿绳子绑,这裹不好的。这句话说得大文大武暗暗使下不少劲。老外婆上前一把捏住奶奶的脚尖,眼睛一闭,猛地朝下一按,继而便是奶奶的嚎叫,她一下子就挣脱了两位弟弟的手。众人赶紧围上来按住奶奶,奶奶在磨盘上滚来滚去,像只泥鳅一样,然后看准一条缝,“吱”一声溜下磨盘,撒了腿就跑。边跑边嚷嚷,脚断了,脚断了。
春林大爹哈哈大笑,说,我的儿,脚断了还跑得跟兔子似的。又说,好,今天不裹了,到我家休息几天,养好了再裹,刚好你仲书兄也回来了。
奶奶站在百米开外的土台上打着哭声回应道,仲书哥哥回来,次勋哥哥是不是也要来?
你如果要次勋来,我明儿一早就把他接来。
次勋是奶奶的堂兄,大名雷明泽,次勋是字。次勋的爹和老外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因为分家闹出了意见,以致两兄弟绝了交情,再也没有来往过。次勋比奶奶大了十五岁,是雷十三家的长房长孙,因与仲书同窗,故而与春林大爹一家来往甚密。春林大爹说次勋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日后能成大器。奶奶曾听老外公说起过这个堂兄,但是真正见面却是在四岁那年,时值端午,奶奶提着一篮粽子去给春林大爹送节气。在后院的梅花树下立着一个穿长衫,梳分头的男子。男子长相温和,冷不丁见一小女孩,便府下身问,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啊?
雷明翠。
明字辈的,你是哪一家的雷?
十三家的。
你是麦儿?对不对?
奶奶点了点头。
男子当场高兴坏了,一把举起奶奶,说,我的妹子,你是我的妹子。呵呵,我早就想见见散财龙女是个什么模样。
我不是散财龙女。
春林大爹握着一把紫砂壶从天井处走了过来,说,你不是散财龙女谁是,上次过来,摔了我一个青花盘,你看你现在手上又拽了个什么,哎哟,这可是粉彩的薄瓷,谁给你拿这个的,小祖宗,快给我。
是仲书兄给我喝茶的。
小小人儿喝茶用得着这个吗,不是专门给你留了个临澧瓷杯吗,你用那。
那个是粗瓷,细瓷喝茶味儿正些。
你知道个屁!春林大爹当场呵呵大笑,说,小小人儿,还能喝出茶味儿来。来,告诉你,这是你的次勋长兄,你们十三家的长房长孙,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
次勋舅爷爷也笑得不行,抱起奶奶说,好精明的小丫头,等我将来办了学校,你一定要到我的学校里去念书,愚兄把你培养成个女中豪杰。
好,只要不让我当散财龙女就行。
打那以后,奶奶便将这个次勋长兄念在了心里,动不动就我次勋长兄说,我次勋长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