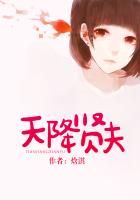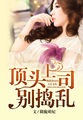自小我就非常崇敬领袖,把他作了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读书的时候,住校,晚上熄灯了,总还有许多同学不顾校规摆龙门阵。一般我是不参与的,但是他们说到领袖,用了轻慢的口气,我却忍不住开腔,急眉赤眼高声驳斥他们。有好几次,被巡夜老师逮住,揪去办公室罚站,在全校同学面前作检讨。我是守规矩的,绝不想也不敢违反学校纪律的。
后来我才明白,我的驳斥是非常可笑的。倒不是那些轻慢领袖的同学说得怎么在理,他们也都是道听途说,一知半解。他们是抱了猎奇的、抖露私秘的,或者说逆反的心理来添油加醋放大那些鳞爪碎片的。不过我的崇敬也毫无根据,因为我对领袖的实际情况其实知道的非常有限,我的全部感知仅仅来自于老师和父母告诉我的那些词语:伟大、英明、正确、战无不胜——这是一些大词,我对领袖的迷信其实是对大词的迷信。大词高标在领袖的头顶,像一层光环,我抬眼仰望的只有光环,领袖本人隐没在了光环的明亮背后。
回过头看看,我发现我对大词的迷信竟然一直贯穿在我的整个学生时代。除了崇拜领袖,我还崇拜各种专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发明家、哲学家、文学家。我崇拜他们有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博大的理论体系、震古烁今的发明创造。我还崇拜他们的“名人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天才就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成功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天赋……我对“名人轶事”也很感兴趣,牛顿请客人吃饭,他却在实验室里满头大汗做实验;苏格拉底与客人高谈阔论,被他家的“河东狮吼”从楼上兜头一瓢冷水泼下来而面不改色,谈论依旧;安培走路时因为深度思考撞在电线杆上;爱迪生煮鸡蛋的时候把怀表放进锅里……我对这些故事特别着迷,紧跟模仿——我把我父亲摔了几千匹土砖才为我买的一个电子表扔进锅里煮;把脑袋在树墩子上撞出一个鸡蛋大的血包;我学会了怠慢,对人不理不睬;我和小伙伴在野外玩耍的时候,任随父母怎么臭骂也不丢弃伙伴独自回家……
开始喜爱文学的时候,总是如饥似渴找好书读。什么是好书?打开一本,首先看作者介绍。作者前面都有一系列大词:“伟大”、“杰出”、“著名”、“知名”。于是我的判断就有了:“伟大”自然是第一选择,然后才是“杰出”,才是“著名”,才是“知名”。有些“伟大”的作品并不好读,打头,常常一翻开,睡意就卷上来了。但我总是努力强撑精神读下去。读到最后,读书成了识字,读书成了仪式。不过我反复告诫自己,既然是“伟大”,自然有其“伟大”的道理,虽然暂时读不出趣味,但是将来的某一天,一定会豁然开朗的。
我一直以好学生的标准要求自己。好学生就是优秀的学生。“优秀”是个大词,“优秀”之下还有其他等级:良好、一般、差。老师有一整套量化的考核体系来对我们做出评价。比如品德方面,老师就制定了一个操行评分细则,一学期下来,如果操行在90分以上,就是“优秀”,75—80分,是“良好”,60—75分,是“一般”,60分以下,是“差”。获“优秀”的,是乖孩子,好学生。获“差”的,他将遭到全班同学的鄙视和唾骂——“差”这个等级,连字也比别的等级少一个。
为了获得“优秀”。我谨小慎微,上课认真听讲,从不讲话;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从不与人生事红脸,别人要惹我,我也总能保持克制,忍气吞声;积极做好事——这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加分条款中的一条——捡到别人遗失的物品迅速交公,抢着帮助别人扫地,在回家的路上帮老奶奶扛柴让老奶奶把这事告诉操行记分员……我密切关注着我操行的动态线条,绝不允它滑到90分以下。
但有时候我对“优秀”的结论也产生过动摇。班上有个调皮鬼,他做了很多捣蛋的事情,但是他的分数也从来没低过90分。每当他的分数从90分滑到89分的时候,他就会找上几个哥们儿在半路上拦住操行记分员,威胁他说,如果那1分给扣了,他将让那记分员满地找牙。而另外一个同样调皮的同学,他的操行也没低过90分,他的办法是不断用一些小恩小惠收买那记分员,然后他被扣去的那些分数就不知不觉地加了上来——在学期结束的时候,他们都如愿以偿地获得“优秀”。
这些调皮鬼的作为虽然让我感到不齿,觉得“优秀”受到玷污,但是,我对“优秀”这个大词本身也产生了怀疑:89分和90分有何区别?它们不就相差1分吗?这区区1分就能对一个人的品德得出不同层次的评判吗?还有,60分就是正向的学生,差1分,59分,他就成了我们鄙弃的反面的对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开始觉得“大词”不可靠。我崇拜的那些“家”们,他们传递给我们的那些成功经验,常常也是可疑的。勤奋,惜时,吃苦,流汗,这些东西根本就代替不了天赋。村里有个孩子,读高中时几乎每天晚上都躲在学校路灯下借光夜读,他把眼睛读成了高度近视,但连续参加了好几年高考——我们称他是“八年抗战”——均没有跨过那道门槛,最接近的一次也是差1分。而1分,他就只得重新回到村子。这时候,他的眼睛已坏,连农活也不能做——做不了官人,连农人也做不了,最后成了“废人”……即便天赋秉人,也未必成功。同样是我们村里的人,他异常聪明,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高考也考了个好学校。他的父母耗尽所有家产且债台高筑才让他完成学业。但是他大学毕业后却四处碰壁,找不到工作,直到现在还窝在家里。而他高中同学中的那些城里干部子弟,既不好学,又蠢笨如牛,但混一个文凭后就立即进了机关,几年过后俨然已是一方长官。
质疑让我清醒,让我认识到追逐大词是荒唐的和盲目的,因为大词本身常常就是过度的,过分的,像一个吹胀的气球,吹得越胀,爆裂的可能越大;或者说像一颗越冬的橘子,有一个好看的外表,内里却模糊不清,有可能是汁水饱满的橘肉,更可能早已干如败絮;或者像一个好看的盒子,因为外表太过突出,妨碍了我们对里面珠子价值的判断;或者是一个羊头,它悬挂在高高的案板上方,但是抽屉里放的却是不同气味的狗肉。
那是一个盛产大词的年代。那时候,人们还对大词奉若神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永远正确,万寿无疆;人定胜天……这些大词造就了一个神谕时代。神谕时代的方式是首先造一个神——或者说造一个偌大无比的大词——然后以神的声音为标准音,以神的语言为标准语言,以神的话语习惯为标准的语法规范。当我们的思想统一在神的光芒烛照之下后,我们就成了强大的执行力量。神的大词越虚假,执行的破坏性越大。我们像一群逐日的夸父,我们奔跑的速度越快,我们就越早地被太阳烤成焦炭。
回顾词语的流变史,我们会发现,人类最早出现的很多词语都是大词。风、雷、雨、大火、洪水、野兽,大自然里这些平常的事物,对于我们的先民来说,全是大词,他们对这些大词深感畏惧又虔诚敬奉。他们把这些含义不明的大词作为自己的姓氏,作为自己的祖先,作为主宰世界和自身命运的鬼神。他们在这些大词的笼罩下过着担惊受怕焦躁不安的生活。历史进入了等级社会,词语也开始分化,有的是大词,有的却成了微言。比如“禽兽”,它原本是大词,因为某种道德系统,它变得卑贱龌龊。再比如一个“朕”字,它本来是一个很平凡的词,和“我”、“吾”、“余”之类的词语处在同样的地平线上,人人可用,但是金字塔最上层的那个人用了,这个词语就成了大词,成了所有人毕生景仰的圣物。而且奇怪的是,所有的有识之士都会自觉维护这个大词的神圣地位,如果它被崇敬得好,社会就很平安,人们就能安居乐业,如果它大词的地位受到挑战、降格,人们肯定就将饱受战乱之苦。
但是随着历史的车轮往前推动,平等自由意识的觉醒,我们逐渐认识到,要恢复人性,彰显人的尊严和独立,我们必须反对大词,揭示隐藏在大词后面的真相。如果它是一个气球,我们应该尽快把它戳破;如果它是一个好看的橘子,我们应该剥开它漂亮的外衣,辨别里面是汁水还是败絮;如果它是一个盒子,我们要有勇气摔碎它,去除遮蔽,把里面的珠子完全显露出来,让它纯正的光芒替代轻浮的斑色;如果它是羊肉店,我们挂羊头,如果是狗肉店,我们卖狗肉,如果是肉食店,那么挂羊头卖狗肉也并不矛盾,我们就由了它——我们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剿大词的运动,让大词回到它的本意,恢复它词语的本来面目,恪守自己的界定域。当大词统治世界的时候,其他词语全都躲在大词爆裂的光影里,噤若寒蝉,不敢出头,怕被大词锋利的刀锋给削掉脑袋。我们要把那些被束缚被禁锢被压抑的词语全部解放出来,让它们发出自己洪亮清晰的声音,该抑的抑,该扬的扬,该判断的果决判断,该质疑的勇敢质疑,让所有词语都站立起来,去除暧昧,确立自己的独立地位。
我们不再把词语做大小的分别,更不会用大小词语来评价我们的孩子。如果要区别,我们应该建立另一套评价系统,在这套系统中,每一个词都只有界域的不同,先后的不同,类别的不同,绝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如果要使用大词,都是大词,都是激励性质的大词。所有的孩子都在这样的大词雨露下,长成独立的茁壮的个体,像森林里的参天大树,而不是藤或其他矮灌。
不过,当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过于乐观,词语并没有回到它的语意和身体,相反,我们身边无处不是大词。经济居于中心地位,经济决定文化,所以我们努力发展经济,并迅速进入商业时代。商业时代使用的语言是广告。打开电视,最热闹的是广告;打开手机,最闹人的是广告;打开电脑,最先跳出来的也是广告;看报纸,整版整版的都是广告,报纸越好,广告越多;出门上街,街两旁一排排巨幅悬挂的是广告,汽车车顶上是广告,悬在空中的大气球是广告,十字口矗立的电子屏是广告,向来来往往的人散发的传单是广告;超市酒楼闪闪烁烁的霓虹灯光是广告,放出的音乐是广告,传出的各种气味也是广告;即便一些隐蔽的地方,广告也无孔不入,各种招贴纸、牛皮癣把整个世界塞得没有空隙,无处落眼——而所有这些广告,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大词。人们可能对其他使用大词的方式有看法,但是所有人都默认广告是大词这一潜规则。广告嘛,不用大词还叫广告!我们在购买物品的时候,明知道使用大词的广告是不可靠的,但是我们仍然会按照广告指引的方向去做。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不知道离开广告我们能做什么。广告是商品唯一的语言,我们要了解商品,除了通过广告,不可能再有第二种办法。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酒香也成了一种广告,一种依靠气味来宣传的广告。而且我们还有一种攀比的心理,广告的大词倾向正好暗合了我们这种心理。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名牌商品,我们的幸福感会远远超过其他商品。而名牌之所以是名牌,正是广告对它的声名的传播。广告越是使用大词,其声名越大。也有因上当受骗而骂娘的,退货的,索赔的。但是再一次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还是只依赖广告。这简直毫无办法。
我们这个时代除了是商业时代,还是娱乐时代。娱乐的本质应该是人个性的极致张扬和性情的最大放松,让人的生命在紧张和局限的同时找到另一种存在方式,从而使一个人在获得丰富性和全面性的同时,获得独立的地位和自由的品格——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而且是需要真正的思想者毕生追求和追问的话题。但是,娱乐时代的表现形式则完全相反,它是消解的,轻化的,向外的,流俗的,甚至恶搞的。它让人放纵而不是放松,张狂而不是张扬,自耗而不是自由。它所使用的语言仍然是大词,是向另一极发展的大词。同时,当娱乐时代和商业时代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娱乐也同时成为商品。如果说,商业时代的语言是广告的话,娱乐时代就是炒作。炒作是这样一种方式,它让一个人不具备的某种能力被添加膨化剂,让一件“皇帝的新装”获得普遍的认同,让一个可笑的谎言被堂而皇之放在大堂上,让一种盗窃行为合法化。它的动机和目的,最终与广告天衣无缝对接起来。
我是喜欢娱乐的,我也想让自己成为有娱乐精神的人。而且我知道,娱乐精神和成为娱乐明星完全是两回事。我不喜欢炒作,讨厌吹塑,讨厌把泡沫凝结。但是这根本不能改变什么,而且在这个时代,一个不炒作的人,连娱乐也是不能得到的,更别说娱乐精神。娱乐是一种公众活动,没有公众参与便不可能有娱乐。在公众娱乐中,如果一个人不能成为娱乐明星,那么他就只能被遮蔽和压制。我看见过很多歌星影星举办的演唱会,唯一突出的只有那些明星们,台下的观众,包括身后的伴舞者,全都是被遮蔽的对象。即便偶然有镜头对准台下,那也是因为那个观众对歌星影星的深度附和,换一句话说,是实现了他的话语被歌星话语彻底同化后的证明。
我们转一圈后,话语又重新回到大词系统,而且,大词系统还在不断地往前延伸,随着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加深,大词系统正大片大片地蚕食着我们的词语群。生态、绿色、节能、健康,这些原本很平常的词语,转眼间就成了大词;贵胄、皇脉、天后、世家,这些一度被解救出来的词语,它们又重新被拉进大词阵营;天津狗不理、重庆猪圈、北京草鞋、底层、草根、民间、边缘,这些一直处于卑贱地位的词语,也一跃进了龙门,加冕了大词的皇冠;搞笑、颓废、无厘头、劲爆、野兽,这些恶俗垃圾的词语,它们也冲进大词的营帐,吆喝号叫,冠冕堂皇……我们再一次进入了全面的大词时代,我们进入了我们心知肚明大词不可靠不真实不诚恳但是我们仍然义无反顾地挥舞着大词的旗帜抢占大词巅峰来确立自己存在的荒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