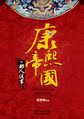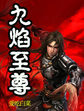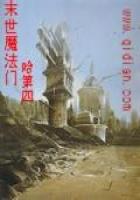和《边城》回到“城”之相对的“乡”不同,《果园城记》似乎没有在这样的对照中有意的取舍和强调,作家“还乡”只是回归到乡土中国。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对乡土、民间的回归和书写,可以发现,作家对于基层民间社会,进入的同时,恰恰又是疏离;强调的同时,往往又在简化,在诸种隐喻、幻象和诗意的书写中,更广袤和深邃的乡土中国的民间社会却沉默着。而芦焚的《果园城记》,乡土、民间社会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话语空间的想象和拟构,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或情感立场的选择,而是“中心”和“边陲”、 “原始”和“现代”、“市镇”和“乡村”、“野性”和“文明”、“凝固”和“流动”诸种力量因素纠结缠绕、对抗与和解生气灌注的世界。
从叙述的视角、立场和姿态来看,虽然同样是回到故乡的“一个远游的客人”,“一个荡子”,一个匆匆的过客,在这样的身份体认上,小说中的“我”和我们前面研究的现实还乡中,多年以后回到故乡的现代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和他们不同的是《果园城记》中的“我”进入故乡更为主动,回到故乡,同时研究故乡,并且以一种近似于探密解谜的心理深入到故乡的日常和细节中去。从孟林太太家,到葛天民家,再到贺文龙家,“当我没有讲果园城的阿嚏之前,首先我应该说明我穿过一片树林,然后,从生着知风草和小树叶的土坡上降下去,我在荒寂的河湾了”。现代作家在处理还乡母题时往往被一种现实的焦虑所左右着,还乡者也自然或多或少带上这样的焦虑,像《果园城记》中“我”这样匆匆而过,但在有限的时间里却在故乡从容地漫游着、叙说着的还乡者很不多见,而且《果园城记》中的“我”进入到故乡,作家又让“我”藏匿起“现代”的身份,在这一组小说中,作家几乎没有对于“我”回到故乡之前离开故乡的经历作多少交代和说明,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性格,作为,一句话,我不知道他是谁,他要到何处去。”芦焚:《〈果园城记〉序》,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这样看,《果园城记》中“我”的视角和立场倒接近古典时代的行走民间、采集史料的史官了。的确,研究《果园城记》,我们能发现它和史传传统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小说写作之间的关系。18篇小说,近半数用人物作题,更有一篇直接作《刘爷列传》。细细揣摩,作家在结构这一组小说时,显然已经自觉到在为乡土中国人物写传,作如是观,不只是从小说题目透露的信息,其实作家自己就是把这一组小说当作传记,在《孟安卿的堂兄弟》中,作家说:“看完这篇传记的人将为他惋惜。”但是《果园城记》又确实是“小说家”言,“以成套(系列)小说家言,点化出一个太虚幻境,例如一个‘果园城’”卞之琳:《果园城·序》,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果园城,一个假想的西亚细亚式的名字,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现在且让我讲一讲关于它的事罢。”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史记》所开创的以“人”为中心,借助“纪传”建构历史的史传传统在《果园城记》中的回响。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史传传统后来成为小说摹写人事的源头,《世说新语》是突出的代表,其后是唐人传奇、宋人笔记。有着这样的传统,在历史的建构中,《果园城记》又不排斥想象,时空腾挪,亦真亦幻,以及掩映其间的人生情怀,显然又是由史传而小说之后“志怪志人”和“传奇化”的路数,所谓历史建构只能是宏大历史叙事之外的“小说”,从这种意义上,《果园城记》的“还乡”是现实的,同时又是精神的、想象的,不仅在内容上取还乡的回归,从小说形式精神的理解和把握上,也回归到中国意义的“小说”。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前面讨论的现实的还乡之作,当还乡被结构化和形式化的时候,同时也难免精神归栖和文化想象的企图。就《果园城记》而言,建构和想象的历史是关于一个中国小城的,“这小书的还乡行动的角色是一个我想象中的小城,不是那位马叔敖先生——或是说那位‘我’……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我从它的寿命中截取我顶熟悉的一段:从清末到民国25年,凡我能了解的合乎它的材料,我全放进去。这些材料不见得同是小城的出产,它们有从乡下来的,也有都市来的,要之乎它们是否跟一个小城的性格适合,我自知太不量力,但我说过,我写我了解的一部分”。因此,从时间的角度,《果园城记》审视“乡土”、“民间”的变动不居,书写乡土中国的“常”与“变”、“赓续”与“断裂”中的流逝与存留。从空间的角度,《果园城记》的18篇小说涉及迟暮的美人、落魄的改革者和梦想家、破败大户和世家的后裔、城主、说书人、卖煤油的小贩、邮差、锡器店的伙计、零食摊的寡妇女儿等,根据芦焚后来所说的目录,“有几个题目一直没有写;另外还有几则零星的札记。这些没有写的题目是驴夫的故事,地方戏艺人的故事,手工业者的故事,当然还有铺子职员与学徒的故事,县官的故事,国民党党老爷的故事”,“按当时的计划,我预备至少写那么三四十篇,想起来就写,尽可能各方面都写到,给小城大体上画出个轮廓”芦焚:《〈果园城记〉序》,上海出版公司1946年版。。在乡土中国的民间社会,这每一个人都意味着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而且这样的世界与世界之间又交织出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在这样的乡土人物志式的书写中,《果园城记》无疑绘制了一幅乡土中国的民间地图。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层次时,殷海光指出,“中国的社会层级在广大的农民底下的有不务正业的无赖群体。这一层次的人素来是中国一般‘正人君子’所瞧不起的。可是这一层次的人素来不乏奇才异能之士”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6页。。值得指出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中对乡村人物的书写也进行分层,但这种分层相当单一,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使作家在书写乡村人物时往往把他们纳入预设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因此,现代小说的乡村人物也逐渐被类型化。《果园城记》的还乡意义在于将这些在书写中被压抑、隐而不彰的乡村人物解放出来,回归到他们生息的乡土,书写他们丰富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不仅如此,《果园城记》还在人间世界之外开拓出一个“非人”的生命世界来丰富它的民间地图,《阿嚏》一篇就是为乡村传说世界的水鬼作传。从某种仅仅从人的世界角度是不足以理解乡土中国的丰富性,乡土中国是一个人、神、鬼和各种精灵共生共处,现实和想象、事实和传说杂糅的世界,从人与自然对抗与和解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生命世界与乡土中国之间的关系,乡土中国的农业文明化,其实也是人与这样的“非人”的世界对抗、和解的过程。在这种对抗与和解中,“非人”与人构成一种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关系。从文本构成的角度,在《果园城记》中水鬼阿嚏的世界和人的世界又构成互文和隐喻。
对于“果园城”,芦焚同时代的诗人卞之琳认为:“这个城更令我想起西班牙‘九八’文艺运动台柱之一阿索林笔下的上世纪末帝国日趋衰落的一些小城的气氛。”并且指出:“芦焚当然也读过徐霞村、戴望舒和我翻译过的阿索林的一些作品。”卞之琳:《果园城·序》,珠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如果我们考察“果园城”和阿索林的“日趋衰落”的西班牙小城之间的渊源,同样受过阿索林影响的汪曾祺所说的一段话差不多也适用于芦焚和他的“果园城”,汪曾祺说:“他是一个沉思的、回忆的、静观的作家。他特别擅长于描写安静,描写在安静的回忆中的人物的心理的潜微的变化。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来的戏剧性。他的‘意识流’是明澈的,覆盖着清凉的阴影,不是芜杂的、纷乱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阿左林(即阿索林——注)笔下的西班牙是一个古旧的西班牙,真正的西班牙。”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阅读《果园城》,在“我”的引领下,走村串户,偶尔驻足静观,打量似曾相识的风景,或者和故人细说掌故、往事,在这样的打量和交谈中,钩沉、索引出果园城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果园城,尤其是那个大变动时代旧新裹挟、相接的西亚细亚小城。
应该说,《果园城记》回归中对乡土中国民间社会地图的勾勒和重绘,只是芦焚还乡书写的开始,接下去《果园城记》所要做的是对“果园城世界”的理解和对“果园城精神”的发现与把握。现在我们和“我”一道还乡,就像小说所写的:“我在河岸上走着,从车站上下来的时候我没有雇牲口,我要用脚踩一踩这里的土地,我怀想着,先前我曾经走过无数次的土地,我慢慢的爬上河岸:在长着柳树以及下面生着鸭跖草蒺藜和蒿蓟的河岸上,我遇见一个脚夫。”系列小说的开篇《果园城》,作家展开了两种意义上的果园城: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小城,果园城,“果园正像云和湖一样展开,装饰了这座古老的小城”。 和任何中国内地小城有着差不多的功能和格局,“这里只有一家邮局”。“此外这里还有一家中学,两家小学,一个诗社,两个也许四个豆腐作房,一家漕房;它没有电灯,没有工厂,没有一家像样的店铺,所有的生意都被隔着河坐落在十里外的车站吸收去了。” 当然这座小城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那塔的故事,还有已经死去的人的故事”,这和其他的中国内地小城也并无二致。情感意义上的果园城,“在这里住着我的一家亲戚”。这种意义上的果园城和其他中国小城区别开来,“你也许要说,所有的泥土都走过一代又一代的人;而这里的黄中微微闪着金星的对于我却大不相同,这里的每一粒沙都留着我的童年,我的青春,我的生命”。因此,还归故乡同时也还归到中国的乡土大地,从这里,我们也发现所谓运用着还乡母题,尤其是体现着精神还乡意义的现代小说比之于一般的书写中国乡村的作品,更能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乡土中国的一部分的意义,故乡所代表的乡土中国成为他们精神建构和成长的重要内容。可以这样说,《果园城》作为《果园城记》的开篇之作,确认了“果园城”作为“我”的生命起点和精神源头的意义。
研究“果园城世界”,我们发现“果园城人”有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想象世界,自己的世界观。比如果园城的那座塔,对于这座塔在果园城日常和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小说中写到:“它是这样重要,假使没有它,据说人们将不认识果园城,将立刻发生恐慌,以为像飞来峰一样,夜里被一阵怪风吹到爪哇国了。”(《塔》)在作家所构建的果园城世界里,这座塔是整个果园城的可追溯历史和可言说意义世界的开端,“当他们——果园城人发现他们的城头上有一座塔,他们以为自己非常重要,以为上天看见了他们,特地送一座塔镇住他们的城脚,使它不至于连他们自己被从河上奔来的洪水冲入大海”,“从此若干年后,果园城出现了一位老员外和他的三个女儿——据和这塔有关系的另一个故事中说……”(《塔》)问题的关键还不仅在此,小说进一步深入到这样的“意义”生成和确立过程。“假如你问这城里的任何居民,他将告诉你它的来历:它是在一天夜里,从一个仙人的袍袖里遗落下来的,当很久很久,没有一个老人的祖父能记忆的时候以前。你也许会根据科学反对这意见,自以为很容易的就驳倒了,可是他们——那些人类中最善良的果园城人——却永远不相信科学;他们有丰富的掌故知识,用完全像亲自看见的言辞证明这传说确实可靠,你即使问遍全城也得不到第二种回答。”(《果园城》)因此,一定程度上,果园城的意义世界是建立于掌故知识和传说之上的,是非科学的。认识到这一点的作家却没有简单地站在现代立场上去否定果园城的经验和意义,而是展示现代价值之下另一种经验和意义的可能。小说中有一个细节相当富有意味:在果园城关于塔的传说生成世界中生活,接受了现代教育的葛天民不是去否定这个传说的真实性,反而是为传说所吸引,转而从细节上去丰富和完善传说,“葛天民开始思索,他过去对于这个问题曾经研究过四年”。在作家的理解中,“这些果园城人,你不能不惊异他们具有这种良好德性;他们是多会用夸大和天赋的想象力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呵!”(《塔》)塔是如此,阿嚏的故事的流传按照小说中所写的:“据我猜想,我是说完全据我个人的意见,它大概是出自天真的,乐观的,没有头脑的,心境常常总是很好的,那些——我相信他们占人口中的百分之十以至十五,那些果园城的蠢汉,因为我认为只有他们在天性上跟这故事不能分开。……你只消想想一个水鬼的鼻子会灌进水,并且活泼,可爱,这样好的打着嚏喷,单单这个嚏喷,你便不能否认果园城的想象力是无比出色。”(《阿嚏》)在这里,无疑作家已经把果园城人赋予世界意义和建构历史的方式与果园城性格联系在一起,而在这样的联系中,我们就能发现果园城赋予世界意义和建构历史的方式在它的世界里是趋同、少变的,但又是自足的和生长的,它在孕育果园城特性的天性的同时,逐渐也形成了世俗生活中观世和处世的方式,这就是果园城规则和果园城的人生哲学:“人是生活在小城里,一种自然而然的规则,一种散漫的单调生活使人们慢慢的变成懒散,人们也渐渐习惯于不用思考。”(《葛天民》)在这样的规则左右下,果园城俨然是“幸福的人们!和平的城!”(《果园城》)但作家在揭示“我”置身果园城,“一种乡村的和平的空气马上包围我们”的生活,又让我们时刻感觉和平的城也是一座走向衰颓的城。“但是夏天的茂盛业已过去,剩下的惟有透着秋天气息的衰老了”(《果园城》);就像葛天民住的公馆,“这是一处破落公馆,我们在各处小城里可以看见许多这种公馆。……它的正对了照壁的大门是高大的,兽脊上装饰着铁花,前檐下有一块匾额,一块凄凉的匾额:‘进士第。’”(《葛天民》)而在这一座座破败的公馆背后意味着一个个家族的盛而后衰,曾经在果园城煊赫一时的“胡左马刘们”,“这些光荣的人们,无疑的他们的禀帖同他们的过于跋扈的家丁们曾使果园城的居民战栗过。现在——时光是不会饶恕人的,这些显耀的祖先的后裔们现在是一个一个的衰落了”(《城主》)。
仔细考辨,《果园城记》往往着重从殷实小康之家的破落来观照“城之衰”,而且对殷实小康之家的破落,作家似乎有一种特别的偏爱。事实上,回顾中国历史太多创业和守成、持家和败家、极盛而后衰的故事,上至庙堂的王朝递嬗,下及民间大户小家的兴衰,一幕幕人间悲喜剧的不断重演,盛衰之期、之变成为一种历史的宿命,果园城自然也难逃这惘惘的宿命。《刘爷列传》中老刘爷一生的梦想就是“战败那位昧心的大刘爷了”,为此,他们竞相买田置地,“最后直到他快要累死,他负了一身债,他大哥还在继续不断的购买”。于是,不得不把种种幻想寄托在精心受孕的孩子身上,“希望有一天他能战胜最大的那位刘爷”。但事与愿违,在“嫉妒,羡叹和娇宠中长大起来”的小刘爷却一天天显露坏的倾向。“老刘爷死后,小刘爷承继了全部遗产:一座乡下的住宅,一座城里的住宅,一处较小一点靠车站的,一处临河人家称做‘米粮仓’的,一处顶小的近山的,共总有三百亩地。”这样的家底在果园城应该也算殷实了,但他却到了省城,而且沾染上城市的“坏,丑,废物和罪恶”,买窑姐,抽大烟,最后荡尽家产,“在老刘爷死后的八年中,小刘爷竟过了五年比乞丐还贫困的生活,即使在顶冷的冬天,你仍看见他仅仅围一条麻袋”。《三个小人物》写“果园城至今还流传一个口号。‘马家的墙;左家的房;胡家的银子用斗量’”。“这口号里第一份人家就是胡凤梧少爷的母亲马夫人的娘家,她的祖父是全果园城的首富,为保护万贯家产,她的父亲曾在光绪初年与小刘爷的祖父同时捐过知州。最后的胡家就是胡凤梧家,他的高祖曾作过布政使,在任上捞到论升论斗计算的银子。然而话虽如此,时间却不饶人,马家的高墙早已夷为平地了,至于用斗量的胡家的银子,也早被布政使的游手好闲的子孙们用光。胡凤梧的父亲在烟榻上躺了一辈子,幸喜去世的早,没有来得及把家产荡完。”而没有荡完的家产,“胡凤梧少爷掌握家政的第四年,在被迫之下,不得不宣告破产”。胡凤梧少爷最后落得身首异处,胡凤英小姐则堕落风尘。值得注意的是,《果园城记》不仅传述一个个由盛而衰的家族故事,而且进而去反思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原因。从现实的角度,就像《刘爷列传》和《三个小人物》中作家揭示果园城衰败和现代都市的兴起之间的隐秘关系,现代都市的物质繁荣和精神奢靡为世家子弟对享乐和奢华病态的沉溺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可以这样说,乡土中国世家子弟的劣根性在现代都市“坏、丑、废物和罪恶”的温床中迅速地合流、膨胀。而乡土中国的内部矛盾也恰逢其时地被共产党策动的农民暴动所激化,从而加剧了乡村殷实小康之家的破毁。但不管怎么说,乡村和都市之罪恶的合流,乡村内部矛盾的激化应该都导源于乡土中国殷实小康之家生成过程中自身所带有的罪恶,就像《刘爷列传》最后写到的:“你也许以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但是为什么大部分有钱人的少爷,他们自己曾经被娇宠过,羡慕过,赞叹过,为什么他们全是没有希望、没有出息的呢?假使他们的父亲根本没有田产,甚至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他们的景况决不会比现在更坏。他们的尊贵的祖先们,并且连他们自己大半都欺凌过农民,蹂躏过穷人的妻女,人家说‘以暴易暴’,不到几年工夫他们就荡尽了家产,比一个真正的要饭还穷。……”时代发展到19、20世纪,乡土中国自身已经匮乏一种转化危机的力量,同时外部压力的渗透、导入则从整个结构上改变,甚至颠覆了乡土中国的力量构成,《三个小人物》中胡家兄妹的沉落和小张的崛起,无疑是大变动中乡土中国力量消长的一个缩影。因此,《果园城记》的还乡,作家的兴趣就不仅在游子归乡时过境迁、景是人非的沧桑之喟,所谓的还乡,对于《果园城记》而言,还在于最大可能地沉潜到乡土中国的真实,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下把握并分析中国乡村。这样,果园城世界已经突破故乡之于游子的意义,而成为变动中的乡土中国的一个标本,在和乡土中国的比照中,果园城世界成为关于乡土中国盛极而衰的隐喻世界,正是从这里,我们理解作家所谓的“果园城”,是“一切这种小城的代表”。
至此,应该说对《果园城记》还乡意义的考察并没有结束,因为在我们对《果园城记》盛衰故事的研究中,隐隐感觉到作家还不仅仅想通过这些故事的书写来穷盛衰之理。固然这些故事中隐含了历史、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道理和秘密,就像巴金的《憩园》的路数。值得玩味的是在《果园城记》中除了这些殷实小康之家的衰败史和败家子列传之外,进入到作家视野的果园城人还有迟暮美人的落寞(《桃红》),政治强人的没落(《城主》),梦想家的幻灭(《贺文龙的文稿》、《狩猎》),改革家的隐遁(《傲骨》)等。这些人和盛衰故事中的败家子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人生道路上的风景也参差相异,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就是他们的生命状态都呈现出坠落和下沉之势,即便在他们的生命历程曾经有过无边梦想和飞扬跋扈,现在作家让这许多的人共生共存于果园城世界,而且又有着相似的生命状态,显然不是偶然的。作家深入到果园城的芸芸众生中间,为他们写记作传,在对这些生命的观察和探询中,必然会传达他对于生命的思考和理解。因此,在写“城之衰”、“家之衰”,必然会深入到“人之衰”。
研究中,我们发现《果园城记》对生命的理解是忧伤的。与故乡暌违多年之后的还乡使《果园城记》的“我”获得一种观照、审视生命的时距;而空间的错置则让“我”具备了一种观照和审视中的冷峻与超越,而不至于被归乡游子的身份所掣肘。因此,《果园城记》的叙述情调忧伤而又不止于忧伤。说它忧伤,除了上面说的它对于生命过程的勾画,还有就是它对于生命渺小和脆弱的细致入微的体察。在《果园城记》中不仅画出生命的轨迹,而且进而对于压抑生命,制约生命自由、舒展的那些力量作了揭示,像贺文龙的庸常、琐碎的日常生活(《贺文龙的文稿》);油三妹失陷于小人的暗算(《颜料盒》);小愤世家和整个社会的敌意(《傲骨》)。也许从这些小说中我们读到的导致“人之衰”的原因还是在和世界的对抗中,人没有发展得足够强大,足以抗拒世界对于自己生命和梦想的威胁。不要说是他们,就是《城主》里的朱魁爷,“一个暗中统治果园城的巨绅”,“他也不受任何政治变动的影响,始终维持着超然地位,一个无形的果园城主人”,“他的根是同果园城的果树一样深深伸进果园城的沃土里的”。但一场乡村政变和随后四太太的变节,内外交困中,这样的一个乡村政治强人,“这个在暗中将果园城支配了十五年的大人物永远成为闷哑的了”,“渐渐的人们把这个大人物忘了。偶然间,当人们怨恨的讲起另外一些新派的大人物,人们拿他来作前鉴,把他称呼作‘鬼爷’或是‘龟爷’”。除了写英雄末路,《果园城记》还反复书写美人迟暮的故事,这中间不仅有素姑、胡凤英和大刘姐的不同人生故事,而且像素姑的故事在《果园城记》还被作家反复地讲述,很显然在这个曾经“像春天一样温柔”的“一个中国的在空闺里憔悴的少女”身上感觉到太多的人生况味,就像小说中写的:“一个橱柜,上面叠着两只大箱,整整锁着她的无数的岁月,锁着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女的青春。”由繁华而寂寞、由强旺而衰颓、由玄想而现实、由傲世到随俗、由沃若到憔悴,就像朱魁爷的觉悟,“好的时候总归要过去的,有那一天也就有这一天!”宿命和无常成为果园城芸芸众生的生命常态。值得注意的是,《果园城记》写宿命和无常背后是深邃、悠远的果园城世界,因此,这样的宿命和无常是乡土中国的宿命和无常,就像《颜料盒》中写的:“在我们周围,广野、堤岸、树林、阳光,这些景物仍旧和我们许多年前看见的时候一样,它们似乎是永恒的,不变的,然而也就是它们加倍的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除却这样大地永在的“常”衬托着生命的无常,乡土中国人事世界的“常”同样衬托出了生命的无常,“假使我们看见的不仅仅是表面,我们若不见出生和死亡,我们会相信,十年,二十年,以至于五十年,它似乎永远停留在一点上没有变动”(《葛天民》)。“……不管世界怎样变动,它总是像那城头上的塔样保持着自己的平静,猪仍旧可以蹒跚途上,女人仍可以坐在门前谈天,孩子仍可以在大路上玩土,狗仍可以在街岸上打鼾。”(《果园城》)
现在我们似乎可以追问:究竟是谁真正主宰着果园城世界和生活在其中的芸芸众生?正是在这方面“时间”成为《果园城记》反复书写的主题。对于整个果园城世界,“时间无声——正像素姑一样无声的过去,它在一个小城里是多么长并且走的是多么慢啊!”在这里时间的有无变得没有意义,果园城“仿佛被时间忘却”,也忘却了时间,“时间于是过去了,自从大刘姐走后,果园城发生了变化:照例谁也没留心从哪一天起,这地方的中心渐渐移转到车站那边”(《一吻》),就像果园城每一家门口坐着和邻人谈天的女人,“一个夏天又一个夏天,一年接着一年,永没谈完过,她们因此不得不从下午谈到黄昏”(《果园城》)。但果园城某些时候、某些人对于时间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尖锐之感、之痛。比如觉悟到时间磨损的素姑,比如像“我”、孟安卿、大刘姐这样的带着旧日记忆回到现在果园城的还乡者,“孟安卿到果园城去,他却不抄直路;他想起河里的沙滩,当初他曾经在上面写过姨表妹的名字的,他忘记中间曾经二十年——时间消灭了一切遗迹,现在是另一代在沙上写他们爱人的名字了”(《狩猎》)。从某种意义上,《果园城记》呈现了乡土中国时间的辩证法,还乡的意义还在恢复了故乡遗忘的时间记忆。《果园城记》告诉我们:乡土中国是有时间的,而且是乡土中国的真正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