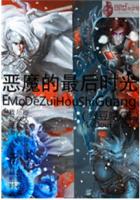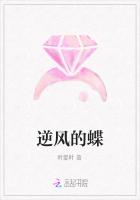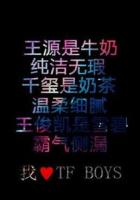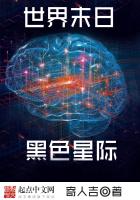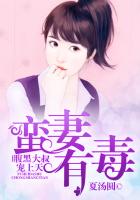几个星期前,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Walk the line》。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男主人公John Cash还默默无闻时,曾在一位音乐代理人面前演唱。他唱的是一首当时很流行的歌曲。他只唱了一分钟,就被代理人不客气地打断了。代理人问他,假如你被一辆卡车撞翻在地,剩下的时间只够你唱一首歌,Only one song,你会唱什么?这首歌要表达你对整个生命的感受。你是唱电台里每天反复播放人们听腻了的歌,还是唱出你真情实感,唱一首特别的歌?一首人们想听到的,真正拯救生命的歌……后来John Cash就唱了一首他自己写的歌,从此渐渐走上了成功之路……
音乐是这样,文学又何尝不是如此?
四年前,我就仿佛被命运的卡车撞倒,奄奄一息,感觉自己剩下的时间只能写一本书,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感悟,于是创作了《梦断得克萨斯》。我的生活不是以我去美国或来加拿大的日期,而是以《梦断》来分界的。《梦断》之前是前生,《梦断》之后是今世。所以这个作品对我来说是独一无二、不可取代的,是My only one song(我唯一的一首歌)。
《梦断得克萨斯》,一生只能有一部,并不是说我正在写的作品和我将来写的作品在思想上、手法上不能超越自己,而是就我在创作过程中所倾注的情感而言,在《梦断》中达到了极限。
从2002年开始动笔,我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这中间经历的情感震荡,真是一言难尽;至少有十次几乎放弃,最终还是一次次回到电脑旁,在键盘上尝试着谱写我生命里的一部心灵的音乐。
现在回味创作体验,感受最深的是三大痛苦。
第一大痛苦,是取材之苦。小说中的的情节时间跨度九年,素材很多。如果把美国监狱、赌场、男主人公阿瑞的经历铺展开来,都能写成一本书。素材的取舍让我很伤脑筋。后来我决定把笔墨花在女主人公舒嘉雯的心路历程上。要表现舒嘉雯的性格,必须把她放在两难的选择之下,通过她在命运压力之下选择的行动来表现她的性格。压力越大,她的选择就越能显示她的性格真相。从本质来讲,主人公创造了其他人物。其他所有的人物之所以在小说中出现,主要是因为他们与舒嘉雯的关系,因为他们对舒嘉雯心灵成长起到警醒或促进的作用。我最初设计的至少还有三个人物,他们的故事也很精彩,可对舒嘉雯的性格塑造没有帮助,就舍弃了。当我千挑万选地把素材整理好了,就进入了第二大痛苦,架构之苦。
我对这个小说的结构做了几次修改。最初的写法是意识流的结构,即把舒嘉雯九年美国生活的时间顺序完全打乱,通过零散的回忆把故事讲述出来,但读起来给人一种情绪时常被间断、被阻隔的感觉。这时有一件事触动了我。那就是我的短篇小说《旋转的硬币》得了联合报文学奖。一位评委说给我评奖是因为我没有玩弄技巧,也就没有犯错,我的小说在题材在表面就有了深度。我想在《梦断》中,我就老老实实地讲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这样我开始对整部小说重新洗牌,把舒嘉雯进监狱之前的经历一次回忆完,使读者很容易捕捉到完整故事的脉搏。我还对开头反复修改,把舒嘉雯入狱的情节一再提前,力求先声夺人。即便如此,百花社的一位编辑至今还认为开头的进入有些慢。对结构的整个调整,工作量非常大,几乎耗尽了我的全部耐心。可是,更大的痛苦还在后头,那就是第三大痛苦,表达之苦。
坦率地讲,这个小说发表、出版后,我至今没有通篇重读过,主要的原因是惭愧。文学实在是永不可能完美的艺术。我一生中最大遗憾就是我的语言不能表达我的思想和情感。每翻到一个章节,就觉得如果重写,可以写得更精炼一点、更传神一点。对几处高潮情节,比如舒嘉雯和阿瑞在太阳城的重逢、阿瑞出狱、机场送别等,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淋漓尽致的效果,可我已经无能为力。写到最后,似乎把情感和体力都耗尽了。写作,像杜鹃歌唱,直至啼血。当时的感觉就是不在表达中疯狂,就是在表达中解脱。当然,此刻能在这里清醒地回顾创作过程,足以证明我是在表达中解脱了。
当我完成了《梦断》,我在后记中写道,“从此,我的一部分生命便离我远去了,我可以轻松一些走未来的路。仿佛一个在舞台上疲惫嘶喊了多时的演员,在曲终落幕之后,洗尽铅华,终于在静夜里有了无梦之眠。”
文学也可能成为一座监狱,You have to do your time,你必须服满你的刑期。如果你正在写一部小说,不要因为我所描述的创作之苦而停滞不前,因为小说发表、出版——那快乐而自由的一刻即将到来。
记得三月的一天,我到邮局去取《梦断》样书。站在邮局的门口,发现夕阳美得有几分特别。翻着这本书,我有一种庆幸的感觉。这个作品能在海内外同步发表,在纯文学出版市场这么低迷的今天,又能被百花出版社赏识,顺利出版,是一大幸运。因此我很感谢我的责编董兆林先生。
创作让原本空虚的生命充实,让原本容易流俗的生活得到了提升。从这个角度讲,不是我写了这本书,而是命运通过这本书拯救了我,所以说,《梦断得克萨斯》对于我,一生只能有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