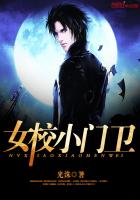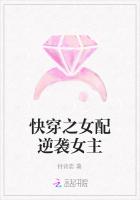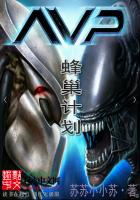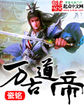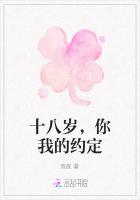发散思维的另一个特征,是永远用比较的眼光观察事物和分析问题。对所能观察到的一切进行比较,甚至不仅比较现有的,还要与现实中没有的、仅仅是想象出来的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有选择,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不全盘否定,也不全盘肯定,在否定中要有所肯定,在肯定中要有所否定,最终要拿到公众和实践中去检验。成功者,都是比较专家。伟人的产生,也只是一系列正确选择的结果。而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都与“囚徒困境”相似,大量的“机会成本”被无谓地付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选择与接受是一回事。选择能力就是接受能力。在学习这个永恒的主题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是每个人的文化取向与文化“食量”不同,消化出来的结果自然就有差异。金融大师巴菲特、索罗斯,就是善于比较各国的投资环境,比较各国的金融环境,比较每只股票的不同,等等。在比较文学领域,有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在比较政治方面,有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在经济一体化时代,世界在变小,使“比较”变得拥挤和迫切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个更好,就是相比较而言的一种结果。追求更好,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或者说,最好,只是一种理想;更好,才是一种可能。
对同一问题的不同阐述,更有比较的必要。比如,管理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特别是我们搞企业管理的,可以深入回顾一下这个问题:“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说管理即追求效率,其实质是思想革命,这种思想革命更多的是体现在工作态度和社会责任感上,应该说他的观点是十分深刻的;美国管理学家孔茨则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协调;还有人说,管理的本质是信息控制;还有这样的说法,“管理的本质是对人的管理,核心是流程的管理,表现是制度的管理”;我们大约可以这样理解老子对管理本质的描述,“无为而无不为”,那就是做该做的,不瞎折腾也是一种作为;如果对《连山易》(相传为上古时代的天皇伏羲氏所创)进行解读,这本书对管理的本质还有这样一种解释:“列山民”(管理的本质在于归类或重组)。这一点认识,可以说深刻至极。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重组是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特征。现在看,重组已经是当今社会发明、创造的主要方式。调整和择优是重组的两条基本原则。一般来讲,事物的现状是由事物的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事物的性质和功能是由结构所决定的。那么,要改变事物的现状,唯有打破现有格局,重新考量其结构的组合,使之形成新的性质和功能,以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或人们的需求。而在考量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多个方案,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和可行性论证后,从中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这就是择优。所谓“最优方案”,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形势发展需要或人们需求的方案。
以“创造学之父”、美国人奥斯本的名字命名的“奥斯本检核表法”,又称“设问法”,即以提问的方式从多个角度对现有产品或发明创造物的结构或顺序进行重组而形成的发明方法。“蓝海战略”也提到重组问题,提出了“剔除、减少、增加、创造”坐标格、“民君食”(管理的本质在于满足受众或承诺一个美好愿景)、“民臣力”(管理的本质在于有效凝聚并充分发挥组织内所有人的力量)、“民物货”(管理的本质在于管理好资源)、“民阴妻”和“民阳夫”(管理的本质在于分工)、“民兵器”(管理的本质是追求实现组织内所有人在共同信仰下采用最佳工具的一致行动)、“民象体”(管理的本质在于统筹为整体);毛泽东有一个大气而简约的说法,领导嘛,就两件事,一是用干部,二是出主意;有专家说,管理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还有人说,管理就是主体(人)通过客体(对象)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活动;管理的本质是对欲望进行管理,这是一种带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的观点;管理的本质是增值,这又是个比较简练的说法;还有一种比较简练的说法,管理的本质是为实现目标寻找捷径;斯隆认为管理就是一种职能,重点在于分工与协调;韦尔奇将管理分为沟通、决策与处理事务三个部分;管理的本质是解决问题,这种说法的依据是“没有问题也就不存在管理”;管理的本质是在充分尊重管理对象的基础上正确地授权,这个说法有点文绉绉的,如果通俗一点地说,管理的本质是不需要管理;松下幸之助认为,管理就是沟通;西蒙说,管理就是决策;法约尔说,管理就是经由他人的努力和成就把事情办好;明茨伯格认为,管理者承担人际角色、信息角色、决策角色;科特认为,管理就是战略、目标、沟通、激励;马克斯·韦伯说,管理即以知识和事实为依据来进行控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管理的实质在于创新;布兰森说,激励人性是管理的真谛;有人说管理是找到、创造并解决问题的循环往复的过程;管理就是正确地做正确的事,这种观点也很常见;曾仕强说,管理就是功夫,是“修己安人”的过程;很多教科书上说,管理就是计划、决策、组织和控制;也有人说,管理就是权变操作的一切艺术行为,这使我想起孟子所说的:“君子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就是“权变”之经;还有人说,管理就是充分可执行的制度化,来抑制人性中贪婪和恶毒的一面;更多人认同这样的说法:管理是激励加约束,一手是胡萝卜,一手是大棒。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基于价值观的实践,管理者的本事完全在于对价值的整合与创新能力;就现实性而言,管理的本质即“一把手”管理自己的延伸;具体来讲,管理就是将一切细节做到精致以使之合乎正理。当然我十分赞成德鲁克对管理本质的定义:“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这话说得很霸气,细细体味也很无情。的确如此。理论永远是灰色的,实践永远是生动而鲜活的。我觉得,实践就像一块绿洲,富含生命。灰色的理论即便有些色彩,也顶多是一张有关绿洲的数码相片。而理论水平就好比像素,但再好的相片、再高的像素,也代表不了绿洲本身——顶多使人凭借相片去寻找或辨认那块绿洲。而要真正领略绿洲的风光,只能置身其中,亲身去行走,切身去感受。所以,我认同德鲁克对管理概念的解释。当然,前面的诸多说法也很有借鉴意义。
顺带说一句,我们在《辞海》中是查不到“管理”一词的。古汉语中,“管”,是“圆形中空之物”;“理”,大意是“纹路”。我不知道西方诸语中“管理”一词都有哪些表达。这涉及语意学的问题。西方思想翻译过来后,难免会有语意上的差别甚至歧义。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比如我们常说的马克思的“公有制”思想,有人说其实是“共有制”思想,这就与翻译有关,当然别有用心者可能会借此混淆视听。马克思的确说过资本主义的股份制企业“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它“表现为通往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的过渡点”,但这话应该如何理解是有争议的。有人就说这个“共有制”是股份形式的“共有制”,“国有制”不应该是马克思的思想。这些问题很复杂,仅通过辩论是不能解决的,要好好研究,而语意学就很重要。一次我在《读者》上看到,同是一首西方诗歌,不同的翻译家翻译过来的作品截然不同,几乎成为两首诗。记得当时我对这种情形深感震惊。“五四”时期就有所谓“意译”、“直译”的争论。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发明。”我想,小平上升到“发明”的高度,可见此事关系重大。的确,中国人用在争论上的时间太多了。搞企业,关键是做事,关键是要解决问题。中国人爱“面子”,更使争论问题复杂化。比如有的人反对,往往是因为他反对的人支持;而有的人支持,又往往是因为他反对的人反对。前面说过“文字相”的问题,与语意学也大有关系。
再比如说,自由是什么?英国行为学家布朗说:“没有规定明确的自由行事范围也就没有自由。”这就是说,在布朗看来,有限制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又有人认为,人们未认识客观规律时,没有真正的自由。这一点我极为赞同。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规律一经被认识,人们便能自觉地运用它来改造客观世界,这时人们就获得一定的自由。人类的自由是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必然与自由是辩证的统一。萨特说:“人是生而要受自由之苦。”为什么?因为自由是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实质上是一种不自由,因为人无法逃避选择的宿命。庄子的自由,是心的自由,是意念的自由。可是,思想真的是自由的吗?观念、学识当然会来束缚它。“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似乎是自由的境界了。然而还是有所凭借,那就是海水和空气。我的看法是,自由就是能力发挥的空间,就是意识活动的空间,就是品格生发实效的空间。没有能力、意识和品格,就没有自由。自由与能力、意识、品格是成正比例关系的。
前面我们比较了对管理、对自由概念的认识。比较对同一概念的不同看法,对于形成我们自己的思想、对于思维创新,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比对、比照、比较,这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
问题无处不在。问题往往相通。在一个问题上钻研久了,进展自然会缓慢下来。这时候,需要在另一个问题上进行钻研以期得到帮助和启示。因为即便是不同专业的问题,表现在思维上,也大致是一样的,有很多共性特征。譬如研究哲学,不妨将世界史通读一遍。因为历史就是哲学的事实体现。如果研究历史,不妨将文学名著读上几百本。因为文学就是经过提炼的、典型化的历史。此时,越是虚拟就越是真实。过去毛泽东说,不读《红楼梦》,就不了解封建社会。孔子很重视诗,花费很大精力编辑了《诗经》,自然不仅仅是将其看作文学问题,而且是看作政治问题,看作修养问题,是一种很高的精神追求。据说孔子在编辑的时候烧掉了很多诗,倒未见得是真的烧掉了,但却是真的经他取舍(客观上造成删减)——可见取舍或删减就是创新,不再流传了。为什么?肯定也不是文学见解的问题,仍然是政治问题、修养问题、道德问题、精神境界的问题。所以,过去称“文史哲不分家”,是有道理的。还有一个说法,中国的“诗书画不分家”,并与篆刻、装裱、古董鉴赏等在艺术境界上都是相通的。像唐伯虎、郑板桥这样的大家,像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这样的大家,在类似的很多艺术领域都有造诣。徐悲鸿在法国潜心研习油画,有很深厚的西方绘画功底。正因如此,他才在国画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刘天华为了精研二胡,把西洋乐器全学了一遍,对小提琴尤有心得——可惜他英年早逝。为什么生活中有的人“干什么都行”,而有的人却“干什么都不行”?思维使然。甚至可以说,要想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就必须在另一领域达到相当的高度。当年爱因斯坦在创立相对论之前,着重攻研了几何、电磁、力学等其他学问。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独树一帜,他的诗词、书法也别具一格。优秀往往是全面的优秀。为什么?思维使然。思维是什么?前面说是一种维度。这个维度是如何修炼出来的?基于品质,基于习惯,基于见识,基于经历,是所有品质、习惯、见识、经历编织出来的一种维度。
发散思维检验的就是这些内容的厚度。确切一点说,检验的就是这个维度的结构是否合理以及这个维度的空间是否足够。“欲此先彼往往是捷径”,还有许多古训可以引证:欲显先隐,是姜太公等隐士的拿手好戏,“出世”是为了更好地“入世”;欲取先予,是郑庄公的阴险把戏,他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纵容方式,陷害了欲谋其大位的弟弟;欲左先右,是国粹围棋的一般战法——典型的“全局一盘棋”的思想。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应该说,“欲此先彼”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为我们取得成功开辟了不同途径,提供了诸多可能。有人讲:“与其反对,不如支持。”此话用意极深,绝对是“政经”。是在用肯定的方式实施否定。2007年央视春节晚会中有个相声,其中有一句话叫“我惯着你”,也是一样的用意,足见国人此种心理在群众中基础之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