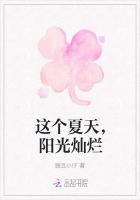创新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无拘束的、富有包容性的环境。对个人来讲,创新需要有一个开放的、无拘束的,甚至是娱乐性的心情。内在的愉悦有利创新,同时创新又能带来愉悦。这是思维创新对心情和心理的要求。人杰地灵,未尝不是规律。将电梯员叫“垂直交通管理员”、火葬场叫“灵魂沙龙”,这何尝不是愉悦的心情所带来的具有愉悦性的创意?这和相声中讲的大碴粥叫“玉米羹”、鸡瓜子叫“凤爪”是一个道理,这是创意经济。
美国人乐于冒险,喜欢探索未知领域,对新事物充满热情,崇尚自由,不受拘束,因此是一个富有创新性的国家。美国的立国就是一个冒险的、开拓的过程。美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很强,要比日本强。日本基本上是借助别人的原始创新,但日本的二次创新能力很强。先“拿来”,然后进行精细制造,把它发挥到极致。这是一种跟随战术,在田径或短道速滑中常见,紧紧跟随,乘风借力,瞧准机会,一举超越。所以日本的制造是全世界一流的,美国人一度甘拜下风。只有瑞士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发达的国家才能够与其媲美。所以,对企业来讲,就要有一种冒险精神、开拓精神、探索精神。我们中国的企业,自主创新这方面是很落后的,没有多少自己的技术,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说到这里,不能不再强调一下思维的愉悦性这个问题。愉悦感能使人更深刻地认识事物。这是思维对人的状态的一种内在要求。愉悦感有利于调动大脑思考,有利于产生灵感,有利于创新。反过来,更深刻地认识事物会使人感觉到愉悦。居里夫人说:“科学的探讨研究,其本身就含有至美,它给予人的报酬就是愉快,所以我在工作里面得到了快乐。”我们只以为居里夫人在找到镭的一刹那是快乐的。其实,她在整个艰难而漫长的探寻过程中都是快乐的,否则她坚持不下来,也找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很多做出卓越事业的人,都有视工作如生命的态度,都有视工作为快乐、视工作为娱乐的状态。正是这种态度或状态,才使他们打开了思维的闸门,解开了思维的缰绳,登上了智慧的殿堂。
前面提到的刘文忻教授讲过一句话,她说:“其实,真正的科学是很好玩的。”北大的丘维声教授也形容过他在数学领域的钻研感受,他是用“奇妙”、“有趣”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的。2006年我在北大听讲座,有人讲:“好玩的科学是最好的科学。”李岚清在山西大学演讲音乐人生的时候,也用“有趣”、“好玩”来描述自己的感受。愉悦也能使动植物很好地生长。给西红柿听音乐,西红柿长得便很好。日本人给牛听音乐、泡温泉、踩地毯(据说柔软的受力能使牛肉口感更佳)、吃绿色食品,连屠宰的时候都用一种特殊的杀法,让牛愉悦地死去,这样肉质会很好。这样生产出来的牛肉价格当然不低,但绝对有市场。这就是一种价值创新。据说德国人的理念是:牛自愿流出来的奶才好喝。所以他们也有许多愉悦牛的本领。他们养的猪每天要晒两个小时太阳,防止猪得抑郁症。猪之间玩儿不上也不行,因为不快乐的猪的肉不好吃。
进一步说,情绪与思维方式有着很深刻的关系。“愤怒出诗人”、“诗以言志”,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司马迁说过:“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什么样的情绪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下围棋的人都知道,平常心是一种很难得的境界。每逢危急艰险的关键时刻,平常心尤为重要。古人说的“猝然临之而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讲的就是平常心。平常心最利发挥。我们看体育比赛,实力是一回事,发挥是另一回事。靠什么才能发挥得好?靠平常心。平常心是一种“无欲则刚”的品格,是一种收放自如的心理状态,是一种淡泊胜负的微细情绪,是一种享受竞赛的处世哲学。这种心情使人能自然地、愉悦地将实力超水平地发挥出来。有时候越是紧张,越是不利于发挥实力。举重好手何灼强在汉城奥运会上因夺冠心切,发挥明显失常,竟然举不起平时训练中轻而易举就能举起来的重量,就是个例子。比赛的时候就要专注于比赛,要拿比赛当训练,不要想着奖杯或奖金,平时训练时却要拿训练当作比赛。过度重视会导致紧张失常。围棋界有一句“长考出臭手”的格言,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吴清源先生就十分推崇平常心的境界。平常心不只是放松,更是高度专注。或者说,只有彻底地放松才能更好地专注。一次,吴清源与劲敌木谷实对弈,激战之中木谷实突然晕厥过去,现场一片混乱,吴清源却若无其事,仍然凝神思考。对此棋界及媒体大为不满,认为吴清源太过残忍。当事后有人问起时,吴清源竟茫然不知,回答说:“当时没看到别的,眼睛里只看到棋子。”
情绪是什么?情绪是品格的表现形式。君子的情绪不可能与小人相同,甚至学者的情绪与村妇的情绪也大异其趣。有什么样的品格就会生发什么样的情绪。当一位国企老总爆发正义之雷霆之怒的时候,那场景是很感人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也许有人会说,光愤怒不行,得拿措施。这话听起来道理很对,但没有应用性。仅仅是正确的道理,没有用。为什么?当然是先有情绪,才有对策。连情绪都没有,何来措施?我觉得,有什么样的品格,才有什么样的情绪;有什么样的情绪,才有什么样的思维;有什么样的思维,才有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措施和对策。前者是世界观,后者是方法论。两者难道不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