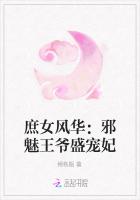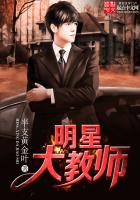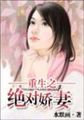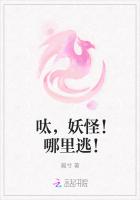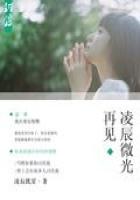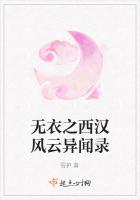现在上海买书十分困难。我住的附近,不但没有旧书店,新书店也只有一家。而卖的多是些中小学生的辅助读物等,有学术价值的书很难看到,反映出我们文化的贫困。人们很难找到一家旧书店,当然很难买到旧书,过去那种逛旧书店的乐趣,当然也谈不到了。我将过去我们到旧书店突然找到一本求之不得的好书时,那种欣喜若狂的情形,讲给现在的青年朋友们听,真如白头宫女说天宝旧事一样。
计划经济时,所造成的这种跛足状况,在当前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时,我希望有所改进。此次游东京,漫步街头,闲逛书店有感于斯,信手写下了这点文字。
哈佛的书香
杜渐
最近到美加跑了一圈,回来后朋友问我:“哪个城市给你印象最好?”我差不多不用思索就立即回答:“波士顿!”当然,多伦多我也很喜欢,但我却更欣赏波士顿的滋味。那是种说不出是什么的味道,姑名之为文化气息吧。哈佛大学有位教授向我介绍波士顿,有这么一句妙语:“波士顿只有两种事业,一是保险,一是教育。”这话说得颇有道理,一条查理士河把波士顿分为两半,河那边是市区,没有什么重工业,大多是保险公司;河这边是剑桥,是文化区,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剑桥的环境优美极了,时届六月,到处人家门前都种满了玫瑰、牡丹、杜鹃和绣球,万紫千红,花团锦簇,空气中飘溢着清甜的花香,但更使人心醉的,是书香!
我这个书痴每到一个城市,首要的事就是逛书店,这比游览名胜风景更吸引我。到剑桥第一天,儿子就带我到哈佛广场的情报中心,买了一张地图,有了这张“拐杖”,我就可以独立活动了。妻子第一件事,是找一间理发店去洗头理发,打扮一番,以便次日参加哈佛的毕业典礼,我趁她进了理发店,就开始了哈佛书店之旅。从此每天一有空,我都泡在书店里了。
多伦多和纽约都有很多书店,但分得很散,只有哈佛,书店差不多全集中在哈佛广场一带。哈佛广场可以说是剑桥的心脏,一条麻省大道横贯其中,旁边就是哈佛大学的正门。波尔士顿街和巴图街交汇于广场一侧,广场中间是个报亭,有各种报刊杂志出售,包括中文报纸,这儿也是地铁站的出口,搭红线地铁就可以跑遍全波士顿,像一条动脉一样。诚然,波士顿的书店并不算多,不像东京的神田,神田可以无愧地称为书店街,哈佛广场却几乎将波士顿的书店十之八九都集中在附近一带,只要在哈佛广场跑上一圈,就能满足书虫的要求。
哈佛的书店数量不少,相当挤迫,看书买书的人很多,而且有一个特点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别的城市书店营业到六点就打烊,但哈佛的书店却开到深宵,夜里睡不着觉,还可以逛书店,有些是十二点才关门的呢。
我的书店之旅是从华兹华斯书店开始的。因为这书店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新书都以半价出售,比别的书店便宜;一般精装书八五折,平装书九折,有些精装书七折,卖又新又便宜的书,就成了这书店吸引大批读者的地方。华兹华斯有两间,一间就在麻省大街,一间在巴图街,经济能力不强的读者,自然欢迎这样的书店了。
在巴图街还有一间叫“平装书匠”的书店,平装书应有尽有,尤以小说为多。店员颇有学问,服务态度很好,我要找某本书,他不只立即找给我,还向我介绍相类的各种书籍。再往前走,有间国际阅读书店,也有大量平装书出售,此店有各国的期刊,以夜间营业至深宵出名。
哈佛大学的学生大多会在哈佛合作社买书,教学参考书最齐全,这是哈佛的商科学生经营的,参加合作社的学生购书,年终会有回扣,第一层是儿童读物和画册,二楼是平装本,三楼是教科书及参考书,还有旧书出售,用过的参考书这儿以两折回收。学生在这儿可以找到各种所需的书籍。
最吸引人的,无疑是哈佛书店了,这儿环境最舒适,过去是两间,现重新装修并成一间。此店的书品质最高,凡新书都陈列介绍,走进去,但见琳琅满目,其中尤以文学批评和哲学书最为丰富。地下室是专卖旧书的,旧书多而且便宜,我走进去后,简直不知时间是怎样过去的,逛了两个钟头仍乐而忘返,在炎热的六月听着不停播送的古典音乐,使人心情为之一爽。
另一间哈佛书店在波士顿的纽伯蕾街,这书店设有咖啡室,走进店中,咖啡香扑鼻而来,逛累了买杯咖啡坐下来,一边品书一边品咖啡,亦一乐也。
记法兰克福国际书市
王安忆
法兰克福国际书市是法兰克福的一部分。那一年在法兰克福的巨大展览馆前驰车经过,就向往着有一个秋季,能够走进国际市场。据说,在那一个时刻里,就好像全世界的书籍都汇集到此,成为一个书的汪洋大海。一本书就像是一滴水珠,刹那间便淹没消失了。有时候,一本书包括了一个作者一生的悲欢离合。那么,在许多人生汇成的汪洋之中,一个人便也像是一滴水珠般的渺小与脆弱。于是,我便想到,当一个作者和一本书走进这一个世界性的市场,光荣之后便面临了灭顶之灾。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一年之后的秋天,也就是1988年的10月,我和我的书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市的一角上出场了。
那一日,我从荷兰乘火车到达法兰克福,出了车站,费了些时间才找到一辆出租,汽车穿过黄昏时分车辆如潮如涌的街道。街道上方悬挂了无数彩旗,以各国文字写着关于书籍的格言。成千上万面彩旗在傍晚晴朗朗的天空飘扬着,车辆无声地在街道里行驶,很像河水在河床里流淌。许多车辆渐渐汇集到通向书市的街道,然后停在书市前的广场上。广场上有各种国籍的人在分发书讯之类的宣传品,转眼间,我的手中已收集了好几份,只好塞进了垃圾箱。垃圾箱里满满的,遍地都是五彩的印刷精美的宣传品。
汉瑟出版社的编辑先生出来接我,向我谈了从现在起至明天晚上的计划,我见我的名字排在汉瑟出版社的摊位前的时间表上。总之,从这时候开始,我将每一个小时接受一位报刊或电台或电视台的采访与摄像。我看见了我的书陈列在书架上,以一幅中国画作封面,题名为“小小的爱情”,这“小”的德语的含义有“非法”,“私情”等内容,其中收集了《荒山之恋》和《锦绣谷之恋》。在这样多的书里面,我想只有我自己注意到我的书。然而,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分钟内,我都将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这又使我的虚荣心抬头了。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书市的巨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总共十个大馆,每个馆有几层袁每一层有几十排,以字母排列,每一排有数十个摊位,一眼望不到头。我们到达了我们的摊位,意大利人将我交给了我的编辑,然后与我庄严地握手,表示一次旅行圆满地结束。然后,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这一天和昨日的一天,是面对记者和出版社开放的,到了明天,才开始向大众开放。浩浩荡荡的记者们在摊位间走来走去,出版商则留意着书的行情,然后着手谈判,购买版权。汉瑟出版社是一个历史很久并有实力的大社,自从出版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获得成功之后,他们便将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出版列入了日程。他们拥有庞大的宣传网络,具有将作家与书推出去的力量。当他们决定出一个作家的一本书,他们就做好了准备,要将这个作家和这本书推上引人注目的位置。我碰巧在了这个位置上,我了解其中的偶然因素,也了解其中商业化的含义。可是,我想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个中国的作者,能够在一个世界性的书市上登场,应是一种幸运,至少我将此视作幸运。当今的时代,印刷术越来越发达,做一个作家,表达自己的机会越来越多。而这样众多的人一起得到机会表达自己,就好比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在呼喊,各自的声音被淹没在声音的巨浪里。也许会有那么一瞬间,有一个声音能够突出,使大家都能听见。或者那一瞬间是出于偶然的机遇,比如其他声音正好一起沉默了、瞌睡了,或者有人选择了这声音与他们的利益发生关系,给了它一个麦克风使它响亮百倍。总之,那一个声音获得了这一瞬间,仅仅是一瞬间,这个声音也是快乐的。当无数照相机围绕了我,摄像机为我工作,记者静听着我朗诵我的作品并对自己作着解释和表白,我想我是快乐的。我想起了许多事情,其中有一件是1983年在美国,有一个人对我说:中国有什么文学?这时照相机的闪光灯组成一个耀眼辉煌的景象,我觉得自己成了这辉煌的中心。这是转瞬即逝的一刻,可是我想我为这一刻却做了长久的等待。我充满了虚荣心,想要表现自己,又缺乏行动的能力,我只能写啊写的,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快乐和悲伤。我渴望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这全是出于虚荣心,没有虚荣心我什么也干不了。我知道在我身前背后,在十个馆内,在几十层市场内,在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书摊上,有无数作家在面对电视,电台,报刊,陈述着自己。我很计较地去留心哪里热闹,哪里又冷清。得意过后心中又不免涌起一股凉意,我想我的声音终究是微弱和单薄的,转眼间被浩荡的风声卷没了。汉瑟出版社的经理先生问我:看见你的书在这样多的书里面,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骄傲。他又问,可是你的书几乎被淹没了啊!我逞强地说:再过几年,或十几年,我要我的书在这里不被淹没。他惊喜地说道:太好了!然后就拥抱了我,而我心中充满了疑虑。
牛津逛书店
陈原
牛津大学是在牛津镇里。大学的建筑物据说是从十二世纪开始陆续修建的。这些经院建筑很有点修道院的味道。到处都是草坪,随时都可以看到伟人的塑像,古色古香的屋顶,烟囱或窗户,而建筑物的外墙却多已斑斑驳驳,活像被废弃的古堡-据说这是因为英伦多雾,潮湿而少阳光,再加上现代化学品的污染,所以这里的外墙显得格外的古意盎然。特别是到黄昏时分,一抹斜阳,照在这些古建筑上更显得幽静。某夜在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夜宴,有点“发思古之幽情”。点着蜡烛,古色古香,厨师捧着烤好了的全羊出示客人,仿佛进入了史各脱小说中所描写的场面。而起立致祝酒辞的则是一位现代物理学的教授,古今汇合,不能不引起许多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