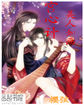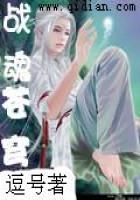鲁迅的书账
何满子
鲁迅比起同时代的缪荃荪、傅增湘等挟有巨赀或声气极广的私人大藏书家来,实在算不上藏书家。大藏书家大多也治学,但不少藏书家的主要兴趣却是为藏书而藏书,作为一种风雅的行为从事搜求善本,广为庋藏,所蓄既丰,就必须编目,以传统方法和自定的章程分类著录。鲁迅的收购书籍则是纯然为了治学参考之用,不是为藏书而藏书,因此他无须编出分类的藏书目录;但为了备忘,也必须有个记录,于是每年有一笔书账,附在当年的日记之后,为目录学开了一个新例,可以称之曰“编年藏书目”。
从1912年起至他逝世的1936年止(1922年日记缺),共有二十四年的书账。书是和他的生活血肉相连的部分,书账也和日记一样是他生命的记录,是研究这位伟人思想、治学进程的重要资料;同时也反映出当时包括出版界、读书界的不少文化信息,不单是目录学上的价值。
书账除了赠书、交换书以外,每年都记下了购书所付出的价款,还有月平均支出数。鲁迅是专靠工资和稿费、版税所得为生的,购书的支出是他生活消费中的一大负担。第一年即1912年的书账题记写道:
审自五月至年莫(暮),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牛津老书店渊蒋建国作冤
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掷月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悦),亦可笑叹人也。
与有大力的藏书家的“玩书”不同,鲁迅是因生命的需要掏钱买书的。查他的书账,费钱最多的是1930年,全年所支出的购书款达二千四百零四元半,月平均支出二百余元。对一个以稿费收入为生的中国作家来说,可称是一笔巨款了。鲁迅爱书,珍惜书,常常亲自修补装订,这不仅是由于珍爱知识,实在也因为系由血汗换来,不容不呵护宝爱之故。
书账反映了鲁迅广泛的阅读面和知识涉猎面,也反映了鲁迅治学方面和发展的轨迹。二十年代以前的书账反映了鲁迅治古籍校勘和碑版研究时期的收藏情况;二十年代初叶的藏目则可看出他在北京各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时所关心的书籍;此后大量购置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世界各国文学、美学书籍、版画等类,都可以找到他研究、创作和所侧重提倡的方面的关联。“编年藏书目”无形中是“鲁迅年谱”的一个重要侧面。由于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现代新文化运动中无可比拟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他的生涯不能不辐射出中国文化尤其现代文化的动向和有关现象。因此,这一编年书账无疑也是中国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的重要史料。佛教书中有《阅藏知津》这类书籍,供读者了解佛学书籍的大要;鲁迅的编年书账也具有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知今”的作用袁虽然它没有书目提要的内容,但毕竟提供了一个探究中国文化的轮廓或示意图;如果仅以一个私人购书的流水账视之,那就太皮相了。
买书
叶公超
以译《鲁拜集》传名于后世的Fitzgerald有一天呆坐在他的小书房里,怒视着围绕他的书。愤怒之下,致书友人云:“我写这信告诉你我最近的决断。我想把所有的书都卖去,或烧去,只留下圣经、字典、失乐园、颇普的诗各一部,放在我书案上,最好都就在手边,那样,我再不会找不着我要用的书了,至少我会知道我此处只有这四部书,别的,世间别的书都在别处,不在我的架上。你一定觉得可笑,假使我告诉你我刚才白生一阵气,找了半天一部我并没有的书……我忽感到我书架上无用的书实在太多了……”这是1873年写的,这位先生已然是64岁了。他买了我想至少有四十年的书才悟到这步,未免令人感觉此道之难也。最苦恼的是,他决不忍真的卖去这些“无用”的书的,至于烧那更不必追究了。不卖不烧就是继续的保存着它们的“无用”,其实也就是它们的“有用”。书的有用与无用者不在书而在人。人用着它,它便有用,大有“相公厚我,我厚相公”之势,人用不着它,它便无用,顿时变成寄生虫一般的可恶,甚至要为人变卖,付焚,其潦倒狼狈之状犹不能击动我们的同情与容忍。我要替书说句公道话:不要这样没有良心,书是有生命的东西,有脉搏有知觉的朋友。朋友也只有一时之用,或仅仅一度的关系,但日后遇见总不免打个招呼,甚而停下寒暄一阵。你想他总算朋友,他想你居然以朋友看待,于是彼此拿出笑容,彼此容忍,彼此拉手再见。这样之后,便算朋友了。既为朋友,见面自必招呼,自必寒暄,自必拿出笑容,自必容忍。书从铺里到我们的架上不能说不是一度的关系,至少你曾看过它,看过之后,或敬它,或爱它,或憎它,或恨它。既有这种经过,我便主张容忍它与你的关系。
藏书家我想一定不会有这种麻烦,至少如汲古阁、海源阁、皕宋楼等等的主人们决不是我们这样慈悲的善心人。在他们,取舍一经决定似乎就不再有别的问题了。除非后来发现自己被骗了,但这也容易解决,只是难过而已。买书来看,或预备来看的人,久而久之总得容忍一些“此刻无用”的朋友们,否则一面买,一面卖,或一面烧,生活便不堪忍受了。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已。同样困难的还有买什么或先买什么再买什么。对于惯于树立原则的人,就是,哪类的书应当自己买,哪类的书应当到图书馆去借。这样一来,问题马上就严重起来了。古人没有图书馆的方便,反倒容易处置;有钱见着要的书就买,买了不用,安排在架上,望望也好,再为子孙留下一点书香,更觉可为。二十世纪的读书人可苦了。除非你住得靠近伦敦博物院,或国会图书馆,或牛津博得利安,总有你要的书图书馆没有的。就是明知道它有,你也未必总愿意去借,况且还有许多不许你借回家的书,而惯于在孤静的斗室中看书的你又不肯天天按着钟点到那公众阅览室里去看。同时,个人的经济能力又有限,禁不住要妄想买到一部永久有用的书。前几年我曾把个人的书分放在三面书架上,一面是要读的各种书,一面是备查的参考书,再一面是既不读又不查的书。我当时立下一条原则:参考书以后不买了,不读不查的书决不买,要读的书,非读不可的,先到图书馆去借,没有,再决定买不买。三年后,三面书架上的书已不分彼此了,同时放不下的书又另占了一整面墙的架子。关于买书,我如今只有感慨,没有原则了。
卖书
宗璞
几年前写过一篇短文《恨书》,恨了若干年,结果是卖掉。这话说说容易,真到做出也颇费周折。卖书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空间。因为侍奉老父,多年随居燕园,房子总算不小,但大部为书所占。四壁图书固然可爱,到了四壁容不下,横七竖八向房中伸出,书墙层叠,挡住去路,则不免闷气。而且新书源源不绝,往往信手一塞,混入历史之中,再难寻觅。有一天忽然悟出,要有搁新书的地方,先得处理旧书。
其实处理零散的旧书,早在不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成套的大书。以为若卖了,既可腾出地盘,又可贴补家用,何乐而不为遥依外子仲的意见,要请出的首先是丛书集成,而我认为这部书包罗万象,很有用;且因他曾险些错卖了几本,受我责备,不免有含恨的嫌疑,不能卖。又讨论了百衲本的二十四史,因为放那书柜之处正好放饭桌。但这书恰是父亲心爱之物,虽然他现在视力极弱,不能再读,却愿留着。我们笑说这书有大后台,更不能卖。仲屡次败北后,目光转向全唐文。全唐文有一千卷,占据了全家最大书柜的最上一层。若要取阅,须得搬椅子,上椅子,开柜门,翻动叠压着的卷册,好不费事。作为唯一读者的仲屡次呼吁卖掉它,说是北大图书馆对许多书实行开架,查阅方便多了。又不知交何运道,经过“文革”洗礼,这书无损污,无缺册,心中暗自盘算一定卖得好价钱,够贴补几个月。经过讨论协商,顺利取得一致意见。书店很快来人估看,出价一千元。
这部书究竟价值几何,实在心中无数。可这也太少了!因向北京图书馆馆长请教。过几天馆长先生打电话来说,全唐文已有新版,这种线装书查阅不便,经过调查,价钱也就是这样了。书店来取书的这天,一千卷全唐文堆放在客厅地下等待捆扎,这时我才拿起一本翻阅,只见纸色洁白,字大悦目。随手翻到一篇讲音乐的文章:“烈与悲者角之声,欢与壮者鼓之声;烈与悲似火,欢与壮似勇。”作者李磎。心想这形容很好,只是久不见悲壮的艺术了。又想知道这书的由来,特地找出第一卷,读到嘉庆皇帝的序文:“天地大文日月山川万古著昭著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经世载道,立言牖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时义大矣哉!”又知嘉庆十二年,皇帝得内府旧藏唐文缮本一百六十册,认为体例未协,选择不精,命儒臣重加厘定,于十九年编成。古代开国皇帝大都从马上得天下,以后知道不能从马上治之,都要演习斯文,不敢轻渎知识的作用,似比某些现代人还多几分见识。我极厌烦近来流行的宫廷热,这时却对皇帝生出几分敬意。
书店的人见我把玩不舍,安慰道,这价钱也就差不多。以前官宦人家讲究排场,都得有几部老书装门面,价钱自然上去。现在不讲这门面了,过几年说不定只能当废纸卖了。
为了避免一部大书变为废纸,遂请他们立刻拿走。还附带消灭了两套最惹人厌的《皇清经解》。《皇清经解》中夹有父亲当年写的纸签,倒是珍贵之物,我小心地把纸签依次序取下,放在一个信封内。可是一转眼,信封又不知放到何处去了。
虽然得了一大块地盘,许多旧英文书得以舒展,心中仍觉不安,似乎卖书总不是读书人的本份事。及至读到《书太多了》这篇文章,不觉精神大振。吕叔湘先生在文中介绍一篇英国散文《毁书》,那作者因书太多无法处理,用麻袋装了大批初版诗集,午夜沉之于泰晤士河,书既然可毁,卖又何妨!比起毁书,卖书要强多了。若是得半夜里鬼鬼祟祟跑到昆明湖去摆脱这些书,我们这些庸人怕只能老老实实缩在墙角,永世也不得出来了。
最近在一次会上得见吕先生,因说及受到的启发。吕先生笑说:“那文章有点讽刺意味,不是说毁去的是初版诗集么!”
可不是!初版诗集的意思是说那些不必再版,经不起时间考验的无病呻吟,也许它们本不应得到出版的机会。对大家无用的书可毁,对一家无用的书可卖,自是天经地义。至于卖不出好价钱,也不是我管得了的。
如此想过,心安理得。整理了两天书,自觉辛苦,等疲劳去后,大概又要打新主意。那时可能真是迫于生计,不只为图地盘了。
八道六难
唐弢
从前的人大都把买书包括在求书或者访书里面,因而有“八道六难”之说。什么叫做八道?八道就是宋朝郑樵所说的八求: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八求既包含着方法,也说明了目标。不过,根据郑樵自己的解释,还是以目标为主,即是说可以向之求书的人,因为他的希望是借校,而当时所谓求书,实际上也是指借抄,和后来有钱便能购下不同。清人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里,说什么“渔仲求书有八道,腐儒经济堪绝倒”,把个郑渔仲当作了笑柄,时代不同,看来真不免有点隔膜了。
但是,同是清人的祁承,却在《澹生堂藏书约》里加以引用,八求之外,又补充了三点:一、对于已佚的书,从前代著述中辑录引文,恢复其部分面貌;二、古书中有注释多于本文的,析而为二,使注释另成一书;三、从诸家文集中纂辑书序,别为一目,以便按目求书。祁承虽然把这三点放在“购书”项下,大体上未改前人求书遗意,特别是他的辑佚主张,对当时颇有影响。后来,鲁迅先生辑《会稽先贤传》和《会稽典录》,还从他所举的《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书里,钩稽出了不少重要的材料。可是提倡把一本书分为两本,但求量多,不问披读是否方便,那可不见得比郑渔仲高明。因为这虽然不是“腐儒经济”,却多少有点“商人伎俩”,为那些改头换面地乱印古书的人张目,给学术界带来了更大的坏处。
八求及其补充大部分已经过时,不过作为方法,买书的因类以求、因代以求和因人以求,却可以有新的含义,仍不失为积储资料的一个门径。记得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庋藏的一批戏曲书籍,为至德周氏几礼居捐赠,数量不多,却有一些他处不易见到的材料,不能不说是收藏者当初因类以求所获得的成果。友好之中,西谛早岁留意弹词、宝卷,后来转到版画、戏曲,晚年又大发宏愿,欲尽收清人文集。阿英对说部极有兴趣,尤致力于晚清小说。这些都和他们对俗文学史、版画史、晚清小说史的撰述有关。还有一些从事作家研究的人,因人以求,专门搜购有关某个作家的著作。最近两三年来,陶渊明、杜甫、白居易、杨万里、陆游等都已有资料专书;新文学方面,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等的作品,也都有人在认真地访求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