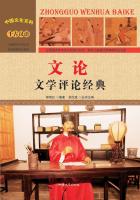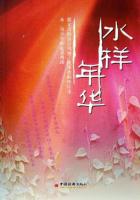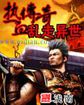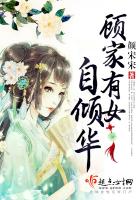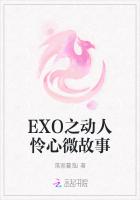抗战以后,我又买了不少的书,存在重庆一个教会里面,还有我那口装子弹的箱子里(这是一位在战地认识的朋友送给我的),盛着许多战利品。后来日本军阀炸弹,又把我的全部财产炸个精光,他们好容易在泥土里替我挖出来了四只炸破了的花洋瓷菜盘,那时我正在西安,范定九先生还特地托人替我带去,我把破了的地方叫锡匠修理好,每逢朋友来家吃饭的时候,便要叙述一遍关于这四个盘子的遭遇,同时还要提到那些被炸毁的书,好像得到朋友们几声同情的叹息,我的心里就很舒服似的。
经过这几次的灾难,我对于藏书的热情,渐渐地冷淡下去。1943年的春天,我回到故乡替先父母扫墓,临别的晚上,我爬上楼,看到还有几箱新文艺和抗战的书籍,我高兴极了。更宝贵的是那些日记和友人的书信、相片等等都好好地保存在那里,一点也没有散失。
我把相片带去成都,日记和书信,书籍,仍然锁在楼上。没想到第二年,敌寇侵入新化,离我家只有七八里了,嫂嫂她们害怕因为我那些抗战书而惹出什么乱子来,索性打开箱子把我的书全部烧毁,而那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的团旗,她们也用剪刀把字剪掉,仅仅保存了几块红布条。当我从三嫂手里接到这些碎布的时候,真使我难过得流下泪来。
十多年来,我们由西安而成都,而汉口,而北平,而台湾,为了交通困难,什么也不能带,笨重的书,自然更在被抛弃之列;几乎成了一定的现象,每次当我换一个地方时,总有一大批书和杂志送给朋友,他们得着了这份礼物的,自然很高兴,而我的心里每次都要感到酸痛的。
来到台湾,跑到朋友家里去,看到他们藏了许多书,我又羡慕又嫉妒,同时想起了自己的书来,又觉得非常痛心!尽管在这样物价高涨的今天,我仍然忘不了买书,我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把我失去的书全部买回来,只可惜那些绝了版的就永远无法得到了!
售书记
郑振铎
嗟食何如售故书,疗饥分得蠹虫余。丹黄一付绛云火,题跋空传士礼居。
展向晴窗胸次了,抛残午枕梦回初。莫言自有屠龙技,剩作天涯稗贩徒。
以上是一个旧友的售书诗,这个旧友和我常在古书店里见到。从前,大家都买书,不免带点争夺的情形,彼此有些猜忌。劫中,我卖书,他也卖书,见了面,大家未免常常叹气,谈着从来不会上口的柴米油盐问题。他先卖石印书,自印的书,然后卖明清刊本的书。后来,便不常在古书店见到他了。大约书已卖得差不多,不是改行做别的事,便是守在家里不出门。关于他,有种种传说。我心里很难过,实在不愿意在这里再提起,这是一位在这个大时代里最可惜、残酷的牺牲者。但写下他抄给我的这首诗时,我不能不黯然!
说到售书,我的心境顿时要阴晦起来。谁想得到,从前高高兴兴,一部部,一本本,收集起来,每一部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被得到的经过和历史。这一本书是从一家书店里得到的,那一部书是如何的见到了,一时踌躇未取,失去了,不料无意中又获得之;那一部书又是如何的先得到一二本,后来,好容易方才从某书店的残书堆里找到几本,恰好配全,配全的时候,心里是如何的喜悦;也有永远配不全的,但就是那残帙也很可珍重,故宫的断垣残壁,不是也足以令人留连忘返么?那一本书虽是薄帙,却是孤本单行,极不易得;那一部书虽是同光间刊本,却很不多见;那一本书虽已收入某丛书中,这本却是单刻本,与丛书本异同甚多;那一部书见于禁书目录,虽为陋书,亦自可贵。至于明刊精本,黑口古装者,万历竹纸,传世绝罕者,与明清史料关系极钜者,稿本手迹,从无印本者,等等。则更是见之心暖,读之色舞。虽绝不巧取豪夺,却自有其争斗与购取之阅历。差不多每一本,每一部书于得之之时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作用。为什么舍彼取此,为什么前弃今取,在自己个人的经验上,也各自有其理由。譬如,二十年前,在中国书店见到一部明刊蓝印本清明集和一部道光刊本“小四梦”,价各百金,我那时候倾囊只有此数,那末,还是购“小四梦”吧。因为我弄中国戏曲史,“小四梦”是必收之书。然而在版本上,或在藏书家的眼光看来,那清明集,一部极罕见的古法律书,却是如何的珍奇啊!从前,我不大收清代的文集,但后来觉得有用,便又开始大量收购了。从前,对于词集有偏嗜,有见必收,后来,兴趣淡了些,便于无意中失收了不少好词集。凡此种种,皆寄托着个人的感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谁想得到,凡此种种,费尽心力以得之者,竟会出以易米么?
谁更会想得到,从前一本本、一部部书零星收得,好容易集成一类,堆作数架者,竟会一捆捆、一箱箱地拿出去卖的么?我从来不肯好好地把自己的藏书编目,但在出卖的时候,买书的要先看目录,便不能不咬紧牙关,硬了头皮去编。编目的时候,觉得部部书本本书都是可爱的,都是舍不得去的,都是对我有用的,然而又不能不割售。摩挲着,仔细地翻看着,有时又摘抄了要用的几节几段,终于舍不得,不愿意把它上目录。但经过了一会,究竟非卖钱不可,便又狠了狠心,把它写上。在劫中,像这样的“编目”,不止三两次了。特别在最近的两年中,光景更见困难了,差不多天天都在打“书”的主意,天天在忙于编目。假如天还不亮的话,我的出售书目又要从事编写了。总是先去其易得者,例如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类。四部丛刊,连二三编,我在前年,只卖了伪币四万元,百衲本二十四史,只卖了伪币一万元。谁想得到,在今年今日,要想再得到一部,便非花了整年的薪水还不够么?只好从此不作收藏这一类大部书的念头了。最伤心的是,一部石印本学海类编,我不时要翻查,好几次书友们见到了,总要怂恿我出卖,我实在舍不得。但最后,却也不得不卖了。卖得的钱,还不够半个月花,然而如今再求得一部,却也已非易了。其后,卖了一大批明本书,再后来,又卖了八百多种清代文集,最后,又卖了好几百种清代总集文集及其他杂书。大凡可卖的,几乎都已卖尽了!所万万舍不得割弃的是若干目录书,词曲书,小说书和版画书。最后一批,拟目要去的便是一批版画书。天幸胜利来得恰如其时,方才保全了这一批万万舍不得去的东西。否则,再拖长了一年半载,恐怕连什么也都要售光了。但我虽然舍不得与书相别,而每当困难的时光,总要打它的主意,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如果把积“书”当作了囤货---有些暴发户实在有如此的想头,而且也实在如此地做,听说,有一个人,所囤积的四部丛刊便有二十余部---那末,售去倒也没有什么伤心。不幸,我的书都是“有所谓”而收集起来的,这样的一大批一大批的“去”,怎么能不痛心呢?售去的不仅是“书”,同时也是我的“感情”,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心的温暖”!当时所以硬了心肠要割舍它,实在是因为“别无长物”可去。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
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我也有我的打算,每售去一批书,总以为可以维持个半年或一年。但物价的飞涨,每每把我的计划全部推翻了。所以只好不断地在编目,在出售;不断地在伤心,有了眼泪,只好往肚里倒流下去。忍着,耐着,叹着气,不想写,然而又不能不一部部地编写下去。那时候,实在恨自己,为什么从前不藏点别的,随便什么都可以,偏要藏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曾想告诉世人说,凡是穷人,凡是生活不安定的人,没有恒产、资产的人,要想储蓄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只千万不要藏书。书是积藏来用,来读的,不是来卖的。卖书时的惨楚的心情实在受得够了!到了今天,我心上的创伤还没有愈好。凡是要用一部书,自己已经售了去的,想到书店里去再买一部,一问价袁只好叹口气,现在的书已经不是我辈所能购置的了。这又是用手去剥创疤的一个刺激。索性狠了心,不进书店,也决心不再去买什么书了。书兴阑珊,于今为最。但书生结习,扫荡不易,也许不久还会发什么收书的雅兴罢。
但究竟不能不感谢“书”,它竟使我能够度过这几年难度的关头。假如没有“书”,我简直只有饿死的一条路走!
禁书
胡绳
在欧洲历史中有许多关于查禁书报的有趣味的材料,这些材料很多是属于中世纪的,然而关于近代的也有。房龙叙述他在俄国革命前游历俄国时的情形说:“当时我所接到的外国报纸面上四分之一,都满涂着模糊的墨迹,其特别名称为鱼子酱,这墨迹下面的条目,都是关心人民的政府所不愿为其亲爱的子民入目的。当时全世界称这种监察是不可忍的黑暗时代的遗习。”
恩格斯也记载过在19世纪初叶的奥地利,“给予国民的精神食粮也都经过最审慎周密的选择,而在给予时又是尽量地吝啬。教育到处都在天主教教士手里。教士的首脑们像封建大地主一样,深以保存现有制度为有利。各大学是照这样子组织只许它们造就在各种特殊学术部门或许能获得高深造诣的专门家,却无论如何不让它去实行普及的自由的教育,而后者则是别国的大学被人们期望实施的。除了在匈牙利而外,奥地利几乎完全没有报纸,而匈牙利的报纸则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被禁止……在奥地利周围各处的边境上,凡是奥地利各邦与一文明国接境的地方,书报检查的警戒线总是与税关关员的警戒线相并立的,用以阻止任何外国书报会偷运进来。
-书报入境要经过两三次彻底细阅,查明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精神才许放行。”
但是这种检查书报的办法都难收效。在俄国人民间,一切秘密的书报流行得既广而又快。而在奥地利,则在国外的莱比锡及各城市中出版了许多论奥地利事的书籍和小册子。这些出版物在波里米亚边境偷运了进去,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在房龙的《思想解放史话》中还有一段极有趣的叙述:“罗马帝国的最初一百年中,曾有塔西佗宣言反对对于著作的迫害,认为这是‘为书籍登广告的愚事,否则这种书籍必不能引起任何公众的注意’。禁书目录〔注〕证实了这话的不错。……在17世纪中,德国与荷兰善于进取的出版家总有专员驻在罗马,其责任即在等候新出的删订书目。他们既得此种书目之后,随即交与专差,尽速越过阿尔卑斯山,赶赴莱茵河流域,将此种有价值的信息传至他们的店主,不稍迟误。于是德国与荷兰的印刷工场就加工赶制,将特别版本仓猝出版,售价极昂,并由书贩偷运至禁止该书的区域内。”
这种书商真可谓善于投机了。
也注页15世纪中叶后袁书籍出版日多遥罗马教廷成立特别法庭检查一切出版物袁凡被列入禁书目录的书袁其著者与读者都要受严厉惩罚遥注家尧选家和摘家
冯英子
在文学这个领域里,注家和选家是古已有之的。至于摘家,倒是我杜撰的名字。不过近来“摘”的东西实在太多,报有报摘,文有文摘,内部有内部之摘,公开有公开之摘,大至厚厚一本,小到八开一张,真是百手争摘,卓然成家了。虽说杜撰,也非无因。
注家在中国历史上应当说是源远流长的。左丘明的《国语》,就有韦昭的注;战国时的《战国策》,就有高诱的注;司马迁的《史记》,既有裴驷的《集解》,又有司马贞的《索引》,更有张守节的《正义》。坦率点说,先秦两汉的古文,一般是比较难读的,特别是经历了那个叫人数典忘祖,把每一个古人批得一无是处的年代,现在爱读和能读的人越来越少了。不久前某地出版的《古文观止·白话译注本》,就把李密《陈情表》中那句“母孙二人,相依为命”译作“祖母和孙子两个人,掉换着大家活着性命”。可见有些人读古文的水平了。幸而有了那么多的注家,才使我们对当时的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地理方位等等,有更多一点的了解。裴松之为陈寿注《三国志》,搜罗书籍四百多种,注文大大超过了原作。这倒不能不为注家们记上一功的。
不过,后人去注前人的作品,由于时代、思想的不同,有时不免隔着一层,而更多的却是使它为我所用,即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胡三省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很能严敌我之分,明忠奸之辨,有一点春秋笔法。这正因为他老兄生于宋元之际,对于蒙古人进入后的统治术,深有所感所致。李商隐的无题诗,有的说他描写爱情,有的说他讽刺政治,有的说他寄托抱负,大家引经据典,言之凿凿,都能讲出一套理由。可是谁也不可能说服谁。据我想,即使再过千年,恐怕还会争论下去、争论不休的。最典型的还要算十年动乱中冒出来的那些注家们,他们一忽儿“批儒评法”,一忽儿“批水浒”,谬误百出,笑话连篇,如译“陈平盗嫂”是“偷了嫂嫂的东西”等等。如果回过头去看看,那么注“相依为命”之类的笑话,老早可以找出几箩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