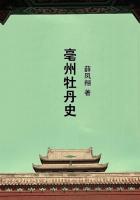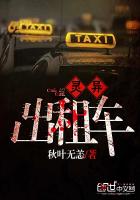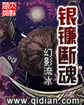人们普遍注意到了这么一个现象,即中国文化重视政治,而薄于宗教。早在20世纪初,章太炎就曾指出:“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因为薄于宗教,所以重视政治;因为重视政治,所以薄于宗教,这原本是相辅相成的一回事。
在其他文化中,宗教往往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西方文化中,无论是希腊的多神教,抑或是基督的一神教,都主张这样一种思想:主宰这世界的,是万能的神,而不是凡人;人们所关心的,不但是相互之间的关系,更是与神的关系;不但是此生,更是来生。
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却仅占有极为薄弱的地位。中国文化主张这样一种思想:人是世界的中心存在,主宰这世界的,只是凡人,而不是万能的神;人们所关心的,只是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和神的关系;只是此生,而不是来生。
那么,为什么中国文化不像其他文化那样重视宗教,而是更重视政治呢?这似乎与中国所处的独特的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章太炎认为:“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急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
尉天骢的《中国古代神话的精神》也认为,世界几大主要古文明的神话对于人和神的不同态度,都与各自所处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得之甚易者可以古代埃及人为代表,其生活所需往往随尼罗河河水之泛滥而垂手可得;人力之可贵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甚少思索之事,故其神话仍然是对大自然所作的泛神论的解释,而甚少‘人’的成分。至于徒劳无功者则可以希伯莱为代表,由于其所处的环境为无垠之沙漠,故虽用尽力气,仍然所获不多,于是因无法克服环境,乃感到人之渺小,而日渐扩大其被自然慑服之情,这样一来,内心中最巨大的形象自然便是那超越现实的大神了。既然无法改进现实,故不禁便将一切希望寄托于‘来生’了。”埃及和希伯来古文明所处的自然环境,使它们各自形成了甚少人的成分或深感人之渺小的神话,而后又发展为具有同样精神的宗教。
但是中国文明所处的自然环境却与它们不同:“中国先民生来没有尼罗河那种天然的易于生活的天地,也没有希伯莱那样的绝境,然而,生活之所需,可由部族之共同奋斗获得。如果依斯宾格勒所说:后一阶段的神是‘力的形象化’,在埃及和希伯莱便是那种人们心目中超越现实的力;在中国,则是要人自己去发挥的‘潜能’了。因为中国人相信人的力量可以胜天,所以在古代神话中,继那些前阶段‘物’象而起的神之后,后阶段的神便是那些对抗大自然,为人们带来幸福的英雄了。”中国古文明所处的自然环境,使它形成了相信人的力量的神话,而后又发展出了具有同样精神的政治。也正因为相信人的力量,所以就不容易发展出甚少人的成分或甚感人的渺小的宗教。
所谓宗教与政治的区别,便也正在于对“人力”的态度上面。那看不到人力或感到人力渺小的,则倾向于宗教;那重视人力的,则倾向于政治。“人类的拯救,不靠神而只靠自己是可能的,这似乎是中国精神的基干。中国的文明,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为主流而发生的。至少就现存文献而言可以这么说。”“由人类自己来拯救人类,它的手段只能是良好的政治,对政治的关心即由此产生。”吉川幸次郎的这些话,便说出了中国精神重视人力的特征及其与重视政治的关系。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儒家哲学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影响之一,是在文学的题材方面。“在西方文学之中,神的惩罚和人的受难,往往是动人心魄的主题……相形之下,中国文学由于欠缺神话或宗教的背景,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人间的文学,英文所谓Secular Literature,它的主题是个人的,社会的,历史的,而非‘天人之际’的。”
影响之二,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因为中国文化把政治,也就是协调人际关系,看得高于一切,因而它早就要求文学一方面要敏锐地反映政治,另一方面又要有利于促进政治。大约出现于汉代的《毛诗大序》,就已经对此作了明确的阐述。这一般被看作是儒家的文学观,但是其实整个中国文化都有这种倾向。
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所谓政治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其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诗歌并不全都与政治密切相关,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也是大量存在的。而在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作品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需要加以辨别。有些作品简单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因而或者流于说教,或者流于枯燥;然而也有些作品中存在着真正的政治正义感与社会责任感,当它们与卓越的文学表现力相结合时,常常带给人们以真切的感动。可以说正是这后一类作品,体现了中国诗歌的政治性特色的优秀一面,蕴含有中国诗人在政治观方面的智慧。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是出于《新约全书·罗马人书》第十二章第十九节的话,全文是这样的:“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显而易见,托尔斯泰认为,对于罪恶的惩罚只应让上帝来实施,而不应由人类(也包括作家)自己来实施。这大概也是西方由宗教传统而造成的一种普遍思想。
可是在中国诗人的心目中,却不存在这样的上帝。他们认为批评社会与声讨罪恶的权力捏在自己手中,这种权力既是社会基于诗歌强大的社会作用而赋予诗人的,也是诗人根据自己作为社会人的责任感而自告奋勇地承担起来的。所以从《诗经》以来,中国诗歌中的社会批评便已形成为一种传统。尤其是在唐宋时代,这种传统更是达到了全盛。法国汉学家认为,唐诗中存在着一种人道主义潮流,“所谓人道主义潮流,就是对辛苦的农民或处于灾难之中的人民表达同情、怜悯”。他们所说的便是同样的意思。而且,其实整个中国诗歌中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潮流。
中国诗人所常用的一种社会批评的方法,是将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加以尖锐对比。在中国,社会公正的思想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力,其来源不是出于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样一种西方的宗教式的考虑,而是出于在同一个社会中人应该彼此平等这样一种社会性的考虑。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几乎都与这种思想有关。在中国诗歌中,这也是一种常见的主题。比如《诗经》的《魏风·伐檀》:“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将不劳而获与劳而不获作了尖锐的对比。汉代诗人梁鸿的《五噫歌》:“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巍兮,噫!民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将帝王的奢侈与百姓的劬劳作了尖锐的对比。杜甫以擅写社会批评的诗歌著称,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因其表达的典型性与对比的尖锐性而广为人知。又如梅尧臣的《陶者》诗:“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张俞的《蚕妇》诗:“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非是养蚕人。”都以《魏风·伐檀》式的手法,表现了社会的不公正现象。而类似的说法,在中国社会中是到处存在的。这种尖锐对比的方法,不仅具有触动人们心灵的思想力量,而且也产生了一种适于中国诗歌抒情特质的极为明快有力的表现效果,可以说中国诗人是相当注意运用这种效果的。
中国诗人在进行社会批评时,往往巧妙地避开皇帝本人(当然在历史上有定评的昏君,如桀、纣、陈后主、隋炀帝之类是例外,对于他们是可以当落水狗来打的)。这往往被人们称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诗人政治软弱性的表现。
不过也许问题要比人们想象的更复杂一些。在中国这样一个皇权延续了几千年的国家里,任何再有影响的诗人也难以与皇权相抗衡。巧妙地避开皇帝本人的社会批评,也许不失为一种维持社会批评传统的聪明行为。否则像梁鸿那样,还只骂到皇帝的宫殿,便已被汉章帝通缉得只能销声匿迹了,社会批评便也就不能有效地持续下去了。
此外,中国诗人之所以在进行社会批评时避开皇帝本人,大概也不是因为视皇权为神圣,而是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中国的皇帝并不像日本的天皇,具有“万世一系”的血统延续性,因而成为民族的凝聚中心,而仅仅是一定的政治组织(某个王朝)的凝聚中心,所以并不具有神圣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之类豪言壮语,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经常可以听到,原因也正在这里。但是正因为皇帝是一定的政治组织的凝聚中心,因而除非到了要改变这个政治组织(所谓改朝换代)的时候,所有的社会批评当然都只能修补其政治组织,而不能动摇其凝聚中心本身(也就是只能“补天”,不能“变天”)。中国诗人在进行社会批评时之所以避开皇帝本人,大抵是出于这样一种潜在的心理制约吧?否则如果摧毁了这个凝聚中心(当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所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那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这个政治组织之一员的诗人,也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中国诗人在进行社会批评时,常会以某种假想的理想政治作为参照体系,而且,他们相信(或装作相信)这种理想政治在上古时代是曾经实现过的。这大概是因为上古时期没有历史记载,可以随便发挥想象;也或许是因为假设理想政治是过去有过的,要比假设它是将来应有的,对于现实感很强的中国人来说,更富于使人信服的力量。凭藉这种假想的理想政治,中国诗人就可以有恃无恐地进行社会批评了。这正如松浦友久所说的:“不管上述哪一种诗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把儒家的政治思想,当作一个理想,或者一个理性概念。不是述说现实政治是否如此,而是述说它应该如此。或者用这种思想以假定、润色的方式来述说现实政治……因为这种儒家思想本身,就是远在古代社会时,便以假定的方式,人为地设定一个政治理想或政治理念的一种思想。儒家文献中所主张的政治状态,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在现实生活中,就从来没有哪一天出现过。”这其实正反映了中国诗人进行社会批评的智慧:用婉转的“理应如此”来代替尖锐的“事实如此”,从而用婉转的引导代替尖锐的冲突。不过说到底,所有假想的理想政治,其实大抵只具有批评现实的功能;如果真的将它们变为现实,那也许反而会成为另一场灾难。
18世纪的一个法国人比奥,曾以稍嫌理想化的口吻,赞赏了中国诗人进行社会批评时那种决无奴颜婢膝之态的气概。埃尔韦·圣·德尼也同意他的看法:“汉诗里有无数进谏诗,是一些忠君的仆臣在流放地写的。他们哀叹自己的失宠,更悲叹皇上的昏庸。比奥先生曾指出一件重要的事实:中国的皇宫里下臣为君效忠决无奴颜婢膝之态。人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在这些倾诉哀怨的诗中,在这些表明自己怀才不遇,力图重新得宠的被放逐者的陈情表里流露着一种清高自尊的格调。里面没有一字降低人的风骨,没有一句表现出卑下的谄媚。”如果这番印象里确有某种真实性的话,那正恰恰说明了中国诗人在臣服皇权的同时,也并未失去出于社会责任感的自尊,以及服务于理想政治的热忱。
类似中国诗歌中的这种社会批评的传统,并非是存在于每一种诗歌里的。比如日本诗歌里便显然缺乏这种传统。即使是对于曾经最受他们喜爱的白居易的诗歌,他们也仅汲取其闲适诗,而拒斥其讽喻诗。而在中国诗歌史上,白居易不仅是以其闲适诗,而且也是以其讽喻诗,也就是社会批评诗而著称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诗歌中社会批评的传统,乃是与中国文化的本质密切相关的。
一将功成万骨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人性(这里是指超越善恶或包括善恶的广义的人性)的表现之一。尽管它以各种名义进行,有各种表现形式,但其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损失,却几乎是大同小异的。在遭到生命与财产的损失时,厌战思想的产生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战争往往又符合人性中好斗、尚武、复仇、杀戮的本能,因而它同样也容易激起英雄主义的情绪。
战争的历史几乎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表现战争的文学也是如此。早在古希腊神话中,战神与文艺女神便已同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在各国文学的开端,我们总是可以发现战争的阴影,比如在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在西方最古老的史诗《伊利亚特》中。
然而对于战争的态度,中国诗歌却与西方诗歌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诗歌对于战争的态度,常常是英雄主义的。西方诗歌的源头是《伊利亚特》,它的主题便是战争与英雄主义。中国诗歌对于战争的态度,则常常是反英雄主义的。当然不是说中国诗歌中不存在英雄主义,但是它只在一些面对外族侵略的时期(比如宋朝),才会表现得比较明显,而总的来说却不占主流地位。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战争与英雄主义并非是其中最重要的主题;相反,对于战争带给人们的不幸,以及对于和平生活的热爱,倒是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对于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从一开始起便表现出来的对于战争的不同态度,埃尔韦·圣·德尼曾作过一个非常有趣而且也很著名的评论。他认为《诗经》中的《魏风·陟岵》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也许在任何其他民族的诗文里找不到类似的作品”。他把这篇诗歌与《伊利亚特》作了比较:“《依(伊)利亚特》是西方最古老的诗,是唯一能用来与《诗经》作比较,以便评价位于有人口居住的陆地两端,在极为不同的条件下平行发展着的两种文明。一边是战争频繁,无休止的围城攻坚,相互挑衅的斗士,是激励着诗人和他的英雄的胜利光荣感,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疆场之上。而另一边则是对家庭生活的眷恋,是一位登山远眺父亲土屋的年轻士兵和他的怀乡之情,是一位斯巴达人定会要扔出墙外的母亲,和一位叮嘱离家人不要顾念光宗耀祖而首先要尽早返回故里的兄长。在这边,人们感到自己置身于另一个世界,置身于一种说不出的安逸的田园生活的氛围之中。”
这种从其源头便已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厌恶战争、热爱和平的思想,后来也一直成为中国诗歌中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比如汉代乐府诗《战城南》,便是一首对后来的中国诗歌发生过很大影响的表现战争悲惨后果的诗歌。在唐代诗歌里,伴随着一个时期的对外扩张活动,这种表现厌战思想的作品就更多了,比如李白的《关山月》、《战城南》、《古风》十四、《古风》三十四、王昌龄的《出塞》、汪遵的《长城》、陈陶的《陇西行》、王翰的《凉州词》、曹松的《己亥岁》、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等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厌战诗歌。埃尔韦·圣·德尼认为:“这些诗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髓……即便这些诗的寓意表现得不那么明确,不那么深刻,只要看一看唐代诗人向我们展示的中国人民的实际生活,便可以了解到唐朝以及唐朝之前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活是根本无法激起中国人进行征战的热忱的。”
这里埃尔韦·圣·德尼提到了中国这些表现厌战思想的诗歌作品“寓意表现得不那么明确,不那么深刻”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曾由其他汉学家指出过,如小尾郊一认为:“中国的诗中没有出现否定战争的反战诗,而只停留在肯定战争的同时表现其悲惨这一步。”这大概主要是由中国诗人的现实困境所造成的,他们一方面不能不对战争的悲惨后果深感震惊,但同时又不能在战争问题上公然对抗国家的权威,因此只能走一条比较曲折的表现厌战思想的道路,这就必然会导致如上所述特点的出现。
中国诗人大致用如下几种手法,在不对战争作明确的否定的同时,对战争作含蓄的否定。
一是写士兵的思乡情绪。正如埃尔韦·圣·德尼指出的,这种思乡情绪实际上是与英雄主义相对立的。如《诗经》的《魏风·陟岵》便是这样,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诗的“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也是这样。
二是写战争所造成的悲惨后果。这种悲惨后果足以使人们消除对于战争的热情。如古乐府《战城南》和李白的《战城南》便是如此。
三是明写英雄主义,却暗含对于战争杀人本质的揭露。如王翰的《凉州词》便是如此:“蒲桃美酒夜光怀,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士兵的豪放的醉态,其实正是由于想到难以生还而引起的。
四是写战争给士兵的亲人、尤其是妻子所造成的痛苦。所谓“闺怨”诗中的很多作品,便表现了这一主题。如陈陶的《陇西行》便是如此:“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诗人首先表现了战争的正当,士兵的勇武,战斗的光荣,战死的壮烈,然后却笔锋一转,写士兵的妻子尚不知丈夫早已成为河边白骨,却还在梦里思念着他,于是前半部分的英雄主义,转而成了一种可笑的愚行。
五是写战争的实际利害问题。如曹松的《己亥岁》诗便是如此:“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指出了将军的功名来自士兵的白骨,也就指出了战争对于士兵的无益。又如高适《燕歌行》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
六是诉诸理想政治中的一些道德教训。如李白《战城南》最后的“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古风》三十四的“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汪遵《长城》诗的“秦筑长城比铁牢,蕃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争及尧阶三尺高”,宋代诗人陶弼《兵器》诗的“是知用兵术,在人不在器……愿采谋略长,勿倚干戈锐”,都沿用了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一章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的传统说法。在这种传统说法中,包含着厌恶战争的道德教训,但又因为是先贤说的,所以效果比较明显而又较少危险。
所有上述这些比较著名的表现厌战思想的诗歌,从表面上来看,都没有明确地否定战争,但是从实际上看,却都含蓄地否定了战争。而且,如果我们不把反战思想仅仅理解为明确的标语口号,那么我们应该承认这些也可以说是反战诗歌。而且更进一步说,由于这些诗歌大都并未明确地否定这些战争的“正当”性或“正义”性,因而其深层的否定战争的意识就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如果连所谓正义或正当的战争尚且如此,则不正当非正义的战争就更不必提了。在这里,中国诗人不直接否定战争的作法,反而带来了否定一切战争的超越性态度。
中国诗人因为对战争持厌恶态度,或至少是持消极态度,从而也就必然会对英雄主义和尚武精神持厌恶态度,或至少是消极态度。鲍拉认为这正是中国智慧的表现之一:“这种伟大的智慧力量,对于中国文明的影响非常深远,而与我们所说的英雄精神背道而驰。”在战火四起的现代世界里,中国诗人对于战争的睿智见解,是否仍不失为一种冷静的忠告呢?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中国诗人经常像这样表现他们的社会批评的意识与厌恶战争的思想。不过中国诗人在表现这一切的时候,常常大都是诉诸个人的体验,而很少诉诸抽象的原则。然而,也正是由于诉诸个人的体验而不是抽象的原则,所以在他们的诗歌中反而蕴含着普遍的力量和象征的意义。这可以说是中国诗歌政治性的表现方法的一个基本特色,也是一些优秀的诗歌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的奥秘之所在。
比如像杜甫那首著名的《春望》诗,便是一首仅写个人的体验,却又蕴含有普遍力量和象征意义的杰作:“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杜甫此诗所写的,全是他在安史之乱中的个人体验:春意盎然的自然与饱受战乱的人世在诗人眼中呈现出的尖锐对比,美好景物在忧愁的心灵中引起的异乎寻常的反应,长期战乱中来自亲人的音讯的可贵,在忧患之中生命的悄然流逝,等等。
但是因为诗人所写的个人体验,对于经历着或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又是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因而此诗就超越了个人的抒情,而成为饱受战争之苦的人们的共同心声。据说,如果让一个日本人只举一首他所喜欢的中国诗歌的话,他们大都会举出这首诗来。当一个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来到被原子弹炸得面目全非的广岛时,他的心里首先涌起的便是这首诗中的诗句,并感慨战争的一般后果是“国破山河在”,但原子弹却使广岛连山河都改变了模样。同样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法国人也“在逃难时经常吟诵”这首诗。
由此可见,尽管安史之乱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时代、性质和规模完全不同的战争,而这些吟诵此诗的人也不属于同一个国家、民族和文化传统,但是他们却都从杜甫这首诗中获得了深切的感动。可见此诗的个人体验中所蕴含的普遍力量与象征意义,已经跨越了时代和国界。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杜甫的《月夜忆舍弟》诗,这也是一首描写杜甫在安史之乱中个人体验的著名诗歌:“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此诗作于759年秋杜甫在秦州时,其时其兄弟分散在河南和山东,而洛阳附近的故居也已毁于战火,可战火却仍绵延不息,使诗人无法与家人互通音讯。
但是此诗给人的感动,却超越了诗人的个人体验。亲人的流离失所,家业的毁于一旦,音讯的难以沟通,结果的难以预料,这一切大都是苦于战乱的人们所共有的经历。因而可以说,此诗以最为个人的体验,表达了全人类的心声。尤其是其中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两句,把战乱中人们“有家归未得”(唐无名氏《杂诗》)的思乡心理,表现得极为真切,而又极为典型。
在巴金的小说《第四病室》中,便写了一个青年工人在病逝前不住地吟诵这两句诗的情景,表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包括那个青年工人,也包括作家本人)对于此诗的强烈共鸣。
类似的共鸣也在一个日本汉学家身上出现,尽管他自觉生活在没有战争的日本,没有负过伤,也有可以寄信的家,家人也没有离散,可是却仍然深受此诗的感动。这是因为他从此诗中感受到了一种超越个人体验的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乃是中国诗歌、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之一。可见此诗的个人体验中所蕴含的普遍力量和象征意义,又已经跨越了战争与和平的界限。
中国诗歌的政治性,至少在一些优秀的作品中,就这样只是通过个人体验的描写,也就是通过个人性质的抒情,来表现的。但是由于其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由于中国诗歌的象征力量,这种个人体验的描写,或个人性质的抒情,却能超越个人的性质,而获得广泛的社会意义。这就是中国诗人对于诗歌政治性的表现方法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像杜甫这样的诗人受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喜爱的一个根本原因。
振衣千仞冈
中国诗人视人生为自然的一部分,视自然为人的安居之地。当他们对政治抱有不满的时候,自然总是成为他们回顾的精神故乡;反之,当他们在与政治的对比中赞美自然的时候,他们常常是以此来含蓄地表达他们对于政治的不满。
左思以“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其一)这样的赞美自然的诗著名,其实在他的对于自然的赞美态度背后,正有着对于政治的不满在起作用。他因为出身贫寒,所以即使再有才华,在那个看重门阀的社会里,也仍然找不到出头之日。在无可奈何之余,他把视线转向了自然,《咏史》其五便表现了他的这个变化过程:“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欻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最后两句乃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可是它的来由却正是由于诗人对政治的不满。诗人将对于不公正的政治的愤慨,化为对于万物自由的自然的赞美。可见这种赞美自然的态度,其实也正是一种变相的社会批评。
对于政治的不满,常常促使中国诗人不仅赞美自然,而且还实际上返回到自然之中去。这种生活态度在中国被称为“隐逸”。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观念,人人都有参与政治的责任,尤其是知识阶层,因而人们用来称赞政治清明时代的一句常用的套话,便是“野无遗贤”;而反之,回避政治而在自然中隐逸,也就成了对于政治的无声抗议。而歌唱在自然中的隐逸生活,则更成了一种虽非直接但却有声的抗议了。
陶渊明便是这样的一个诗人。他喜欢过朴实的田园生活,他的生活理想只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其一)但是他之所以以这种田园生活为理想,乃是因为他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这他自己是一再表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同上)他是以隐居田园来表示对于政治的抗议的。陶渊明的态度,成为后来很多中国诗人效法的榜样,他的诗歌的地位也因此而不断上升。
对于常与政治相伴随的纷争与倾轧,中国诗人每每感到头疼与疲倦,在这种时候,他们也常常以回到自然来摆脱这一切。比如韦应物的《幽居》诗,便很好地表现了这种心理:“贵贱虽异等,出门皆有营。独无外物牵,遂此幽居情。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鸟雀绕舍鸣。时与道人偶,或随樵者行。自当安蹇劣,谁谓薄世荣?”诗人认为,世人无论贵贱,都有功利之心;只有自己已经感到疲倦,所以能够享受幽居之情;幽居有幽居的快乐,那就是与自然接近;这么做只是因为自己无能,而不是因为鄙薄世间的荣名——最后这两句其实只是反话,但也正可看出诗人对于纷争之无谓的认识。
在韦应物的诗里,还有在上述左思和陶渊明的诗里,有着一种对于自然的共同认识,那就是如迈克尔·卡茨所说的:“中国诗画中的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相信大自然有能力使人类心灵恢复那种被实利主义的空虚所毁坏了的平衡。”在西方诗歌中,直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诗歌时期,才开始出现了以赞美自然来批评社会的主题。相比之下,在中国诗歌中,这类主题的历史是悠久多了。而且,即使对于现代人来说,自然不仅能够净化被工业文明所污染了的空气,也仍然能够净化被实利主义所污染了的心灵。“谢灵运认为美的自然是与污秽的人类社会相对地存在的。从而明确地表示由于人事而受伤的心应沉潜于山水之间,并在与环境极端调和之后方能痊愈。”中国诗人的这种充满睿智的声音,也许仍然还有值得我们现代人倾听的价值。
适彼乐土
西方诗人不满意于政治时可以逃向宗教,但是中国诗人却只是逃向自然。对于政治的不满在西方诗歌中化为对于天国的憧憬,中国诗人却没有这样一个天国可以憧憬。但这并不是说中国诗人没有对于理想世界的向往,只不过他们所向往的理想世界仍然只是在地面上的人间世界,而不是虚无飘渺的天上世界。
比如在《诗经》的《魏风·硕鼠》里,诗人就表示过对于理想世界的向往:“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人所向往的这个乐土当然不会是域外文明,而只是一个没有不公正和剥削的地方。这表明即使在上古时期,对政治的不满就已经升华为对于乐土的向往,尽管乐土的具体内容还不太清楚。不过,这个“乐土”从语感上看,仍然是在地上的,而不是在天上的,是人的世界,而不是神的世界。
在中古时期,由于战乱频仍,人们常常躲进深山之中,积累了山中生活的经验。于是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诗》中,乐土便被设想成在某一处人迹罕至的群山之中,通往那儿的只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山洞,只是因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才得以知道它的存在。在那个理想世界中,人们自给自足,与世隔绝,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剥削制度,弃绝智慧,纯任自然,总之,没有现实世界中一切丑恶的东西,而只有符合人性自然的美好的东西:“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
从以上描写可以看出,中国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具有这样几个特征:一是这种理想世界中的生活是顺应自然、弃绝文明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随时而种,随时而收,不要历志,不劳智慧,草木识时,四时知岁。二是这种理想世界中的人际关系也是顺应自然、弃绝文明的,没有维持统治阶级存在的税收,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从这幅关于理想世界的画图中,可以看出中国诗人崇尚自然、相信性善的倾向,这与在西方的文化中只有善人能够进入天国,而恶人则只能进入地狱的思想根本不同。因为中国诗人认为人性本善,使人性变恶的只是不良的政治,只要抛弃了不良的政治,人性就又会恢复其善的本性,从而都能在理想世界里找到一席之地。
陶渊明的这首《桃花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曾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后来有很多以桃花源为题材的诗歌,如王维的《桃源行》、刘禹锡的《桃源行》、韩愈的《桃源图》、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等等,都是源出陶渊明此诗的。而中国诗歌中的理想世界的模式,也大抵是由陶渊明此诗所奠定的。
在中国诗人关于理想世界的幻想中,的确存在着不少天真幼稚的成分。比如在他们描写的理想世界中,人性都是善的,这便是极不现实的想法。因而尽管这样的理想世界为中国人所梦想了几千年,却始终不曾实现过。有时眼看就要实现了,转瞬之间却又为人性之恶所摧毁。而且进一步说,文明正是借助了人性之恶才得以进步的,因而如果一定要阻抑人性之恶,那就只有放弃文明的进步。在中国诗人所憧憬的理想世界中,情形往往正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总是主张在理想世界中应该弃圣绝智,宁愿保留落后的生产方式。然而如果在现实中真的实现了这种理想,那对于人类来说不啻是另一场灾难。
但是,在中国诗人关于理想世界的幻想中,也确有一些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那就是他们不把理想世界放在天国,像西方人所做的那样,而是将它置于人间。这使我们想起了王安石的一首诗歌,其中描写了他一次散步的见闻:“径暖草如积,山晴花更繁。纵横一川水,高下数家村。静憩鸡鸣午,荒寻犬吠昏。归来向人说,疑是武陵源。”(《即事》)诗人看见了一个自然纯朴的村落,便想起了世外桃源,也就是理想世界。这颇具象征性地说明了中国诗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人间性质。这种理想世界的人间性质,也许可以说是中国诗歌对于世界诗歌的一个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