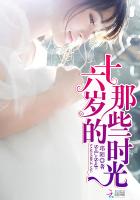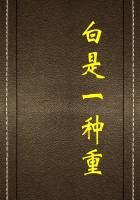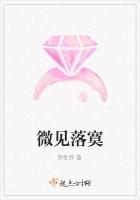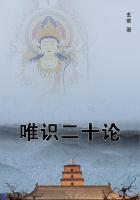岳飞打下陈州后并没有在这里止步,他的百胜之师在一个多月内,攻占了许昌、洛阳、郑州、中牟等地,然后把主力集结在许昌一带,准备寻机与金兵主力决战。在郾城、许昌发生的数次大战中,岳家军“人为血人,马为血马”,仍无一人肯回顾,终于一次次大败金军主力。
为收复中原,岳飞派人在沦陷区做了大量的工作,关隘、渡口的车夫和舵手,饭店、旅社中的店小二,组成了一张岳家军联络网,抗金的“地下工作者”“往来无碍,食宿有所”。到达许昌后,岳飞派遣原从黄河北投奔过来的梁兴、董荣等人渡河北上,联络当地义军,一时间打着岳家军旗号的义军风起云涌,“剿杀金贼,占夺州县”,使金人在燕京以南很多地方的统治陷入瘫痪。
宗泽临死前“过河”的夙愿,极有可能由他当年赏识提拔的部将实现。
但就在这个时候,命令岳飞班师的圣旨——民间传说中的十二道金牌送到了岳飞的手中。不难想象,下达班师的命令,对岳飞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据说,岳飞从郾城、许昌撤军时,当地百姓“哭声遍野”,岳飞也倾洒了无奈的英雄泪。岳家军一撤,沦陷区起事的义军失去依靠,将要燎原的大火顿时熄灭。南宋版“攘外必先安内”
1140年岳飞班师,成为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有人说,岳飞是“愚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干吗听他的?收复了开封再说。
事实上,其他几路大军已经奉命撤退,岳飞已成孤军。如果不撤退,不但得不到粮草供应,甚至可能被视为叛军,那样的话岳家军就很危险了。
有人认为,赵构命令撤军有他的道理,当时宋军没有彻底打败金人的实力。但当时赵构跟金人可能是“麻秆打狼——两头都怕”。宋朝大臣洪皓那时出使燕京,发回密报说:“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史学家多认为,宋金强弱之势已经发生变化,金人宿将大多已经死了,金军整体战斗力下降,如果宋朝诸路大军齐心协力,分路进击,协同作战,则“兀术可擒,汴京可复”。遗憾的是,“王师亟还,自失机会,良可惜也”。清代著名学者王夫之认为,宋军还不具有灭金的实力,但他同样认为,当时宋军收复黄河以南地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秦桧的儿子秦熺在描述1140年前后南宋内部军政状况时,用了四个字:“太阿倒持”。太阿是古代著名的宝剑,所谓“倒持”的意思是,本来应该由皇帝握着对付臣下的宝剑柄,反而握在了臣下的手中。秦熺说,高宗早就有意革除“积岁倒持之患”。或许在高宗看来,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岳飞所想的收复中原、洗雪国耻,而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皇权,避免受到内部的威胁。换句话说,命令岳飞班师,很可能不是担心打不过金人,而是担心岳飞的威望和兵力大得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这算得上南宋版的“攘外必先安内”。
宋太祖曾经“杯酒释兵权”,建立了一套文臣控兵体制。而在宋金战争中,军事才能突出的武将逐渐建立了自己的部队,他们权力很大,不但有军权,还拥有辖区内的民政、财政大权,部队与武将关系十分密切,都以主将之姓为名,如岳飞的“岳家军”、韩世忠的“韩家军”等。
这种状况极大地提高了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使他们在与金人的战斗中逐渐扭转了局面。不过,这种情形绝不是赵构所希望的。
削夺武将兵权的行动,从1132年就悄悄地开始了,只不过当时南宋风雨飘摇,赵构不得不依靠这些大将,不敢骤然重收兵权。1140年发生的一切,让赵构底气足了,他意识到金人已经不能对他构成致命的威胁,于是收兵权的步子就大了起来。
1141年年初,兀术再次举兵南侵,但在合肥附近的柘皋镇被宋军打败,随后兀术在濠州(今凤阳)设伏打败宋军后北撤。他也意识到今非昔比,再与南宋交兵占不到什么上风了,于是,宋金议和再度悄悄进行。
高宗以庆祝柘皋之捷为名,把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召回杭州,任命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副使,看起来是让他们参与最高军事决策,实际是不再让他们掌管军队。高宗又下诏,“凡尔有众,朕亲统领”,解散三大将的统帅部,使他们的军队直接隶属中央,提高军队“中层干部”的权位,让他们分别管理部队,而军队的统帅则临战时由皇帝亲自指派。至此,赵构完成了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岳家军”、“韩家军”、“张家军”统统变成了“赵家军”。
但岳飞、韩世忠威名素著,深得军民爱戴,他们的存在,可能是一种威胁。
韩世忠先被选为打击对象。岳飞被派和张俊一起去原“韩家军”检查工作,岳飞发现张俊竟按照秦桧的吩咐在整韩世忠谋反的材料,他大吃一惊,赶忙连夜派人送信。韩世忠闻讯大惊,他连忙入宫求见赵构,伏地大哭,解开衣服,请赵构看自己身上的刀痕箭瘢。他的手曾中毒箭入骨,两只手只剩四个指头。或许这双残手救了他,赵构此后不再与他为难。而韩世忠从此深居简出,不再跟自己过去的部下见面,喜欢上了佛教和老子,自号清凉居士。偶尔他会带个书童,骑头小毛驴,在西湖边看看风花雪月。
岳飞救了韩世忠,却难救自己。
岳飞的错,就在于他太完美了。作为武将,他不但不惜死,还不爱钱,不贪女色,打胜仗得到赏赐就分给部下。平时什么事都很低调,唯独在收复中原问题上他异常桀骜不驯,“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
或许赵构真的把岳飞看成一个威胁。但秦桧伙同张俊用尽了各种办法,给岳飞定的罪名也就是三个字:莫须有。这三个字,后世成为冤狱的代名词。
岳飞死了,那年,这个河南人年仅39岁。
同时死去的,还有收复中原的希望。
南宋的历史,在和与战之间徘徊。后来,南宋军队曾经两次北伐,但都无功而返,甚至自取其辱。
四 南宋爱国诗词的灵魂
商(丘)永(城)公路南线是一条让所有司机喜欢的路:路基很高,路面直而平整,来往车辆很少。我们走过时,恰逢秋雨迷蒙的时节,路面上的水光,在雨幕中向天际延伸。驾车在坚实的路面上奔驰,很难相信,我们的车轮下曾是滔滔的河水。但考古人员的话又让我们无法怀疑,这条公路,的确是以汴河河道为路基修筑的。
汴河死了,死于南宋初年。其时金兵肆虐,北宋南迁,南北方之间,需要的不再是交通而是阻隔。
在如今中国的交通网络中,这条两年前修筑的路不过是条“毛细血管”,路面上车辆稀少足以说明这一点;而八百多年前,我们车轮下的波涛中舟楫繁多,是全国经济和交通的大动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从隋唐到北宋,载着无尽的繁华和无边的旖旎,汴水滔滔奔流了五百多年。
在路旁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我们自称是“收文物的”,对村民进行了采访。四十来岁的村民李先生说,你们来晚了,两年前修路时这里挖出来的瓷器多了,不完整的卖个五六块钱,好点的卖几十块,当时就卖完了,现在谁还有。李先生告诉我们,修柏油路前,这路就两三米高,跟道河堤一样,传说是神仙娘娘到永城看闺女修的路。李先生说,他们这里就这道埂出瓷器,地里都没有,至于为什么,村里谁也说不明白。很显然,村民们并不知道,他们世世代代就住在古汴河的岸边。
走访考古人员后,我们得知,由于汴河引的是黄河水,因此逐渐淤积,成了高底河(悬河)。虽然后来黄河多次泛滥抬高了豫东地面,但汴河故道还是明显高出地面,修筑商(丘)永(城)公路南线时,就选择河道做了路基。修路时挖出的瓷器特别多,全国各地的瓷器都有,应该是古代一个个从船上掉进水里的。同时出土的还有船只和一米多高的大铁锚。当时偷挖瓷器的人很多,考古人员来回巡逻也不能完全制止,出土的大部分瓷器流失了。商丘市有人搞了个私人博物馆,收藏了上千件完整的瓷器。考古人员说,博物馆开馆时,还有主要领导出席,“真不知道他们学过文物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