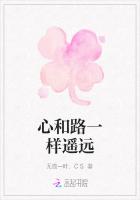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那些因特殊原因而可以光荣移居城市的“中国农民”尚可以寻找到一种作为主人的自豪感;那么,在当下的市场经济时代,尤其是那些刚刚收拾行囊离开土地,随波逐流漂泊到城里来的“农民工”、“打工族”(采取通行说法,不含任何贬义)则是难以寻找到多少自信和骄傲的。这些人密密麻麻,数以亿计,他们拥挤在车站码头,盘桓在街头商店,劳碌在工厂车间,蜗居在各色工棚……对于他们而言,甚至连对自己命运哀叹的时间也没有。古老的比喻还有: 有湖泊,有动物,必然有食肉的大鳄,这叫做“丛林法则”。其实,城市化,对于中国而言,就是集体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民进城博取脱贫致富的机会;而有博取行为,自然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要陷入“城市生存的丛林法则”里,这是所有城市化过程前期中所难以避免的。城市,繁荣和文明仅仅是它的幕布,而真正上演的戏剧往往是——贪婪导致人情的冷漠,竞争导致心灵的防范,尤其是资本大鳄们的张狂与无耻,导致多少卑微生命的摧残和压抑……其实,凡“丛林法则”,不管是存在于原始动物界,还是存在于已经进化到城市化阶段的“人界”,其面貌特征恐怕都是狰狞而残酷的;生存在这样的处境里,恐怕绝不会给人类提供多少“诗意的栖居”的条件。当下中国,城市人要“诗意的栖居”,就必须得首先起来“反抗”这样的生存处境。既然,“我们都回不去了”这已经成为现代进城的“中国农民”的宿命;那么,除了反抗,真的别无选择了。尽管可以肯定,在当前,这样的“反抗”,不管是个人行为,还是集体行为,不管是通过文学创作,还是付诸实际的行动,其结果注定是绝望而悲壮的,但崭新的中国城市诗意将由此而具备了牢固的基础。
所以说,要构建城市的诗意,首先得了解城里的人;更重要的,还要依靠这些城市人。而要谈到可以依靠,则需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这就是这些人都须具备城市公民资格;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城里确实享有自由和权利(法律意义上的),尤其是他们必须具备城市主体人格,也就是他们的人格必须是平等的,并且同样地具有尊严,且这尊严不容践踏。这样,反抗资本的侵吞,去除社会的腐败,解放机器的奴役,宽松制度的束缚,杜绝愚弄和压榨,成为了中国城市化的当务之急。只有把这些任务尽可能地完成了,才可能让那些被“城市化”了的“中国农民”(城市普通市民百姓)拥有一个能自由创造自己城市诗意的平台(环境)。其实,这也是公权政府的使命,是正义文化的使命,当然也必然是所有的城市个体生命审美创作者的使命。城市化了,诗还是会有的;当前关键的问题是,怎样把“诗”的话语权最大限度地“分配”给更多的城市人,不管这些人来自何方,何种身份。总之,人的问题解决了,城市诗意的构建问题才可以提上“议事日程”,否则只能是扯谈。
2. 世俗的个性化选择
确实,对于许多人来说,一旦迈开步伐入城,他们就再也回不去了。鲁迅当年从绍兴的乡下来到上海之后就难以再回去;是的,鲁迅走出来之后是回去过一次家乡,但那是回去卖房子和接他母亲进城的!鲁迅是这样,当下的中国入城者中的许多人恐怕也是差不多的命运。韩少功是可以携妻子退隐原先插队过的乡下山林了,但他的灵魂还是被扣留在城市里,他至少还必须得为城里人做些事情,比如写写散文等;相比而言,韩少功是幸运的,别人则少有能如他这样幸运了。城市以它财富的光环和文明的许诺吸引农民们接踵而来,但刚刚挤进城来的昨日农夫很快便发现自己一下子被抛入经济挤压和文化断根所带来的心灵昏眩当中。从精神层面上说,所有进城的中国农民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但,他们却又都回不去了。物欲的挤压、文化的断根,导致精神的贫血和无所寄托,生命处于不能承受之轻的漂浮状态,这是中国城市人的现代宿命,一种谁也难以逃脱的精神尴尬。既然这是宿命,那么所有针对城市的诅咒和排斥恐怕也都于事无补;必须要做的只能是加紧构建新的城市文化、新的城市诗意,这才是正事。
“新左派哲学家”、“青年造反者的明星和精神之父”——马尔库塞认为科技的迅猛发展已经上升到可以操控一切,并且科技催生新的极权社会,在科技和极权的双重操控下,现代(工业文明时代)人都变成了没有精神层面的“单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也简单翻译为“单面人”)刘继: 《译后记》,[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页204—208…马尔库塞的话也许并不周全(从空间角度看,今天在数字化虚拟环境里生活的现代都市人其实是可以接触更多的人和事的——尽管这些人和事可能始终处于虚拟状态,因此他们可能具备更多副的面孔,而非仅仅“单面”),但他的话语绝对深刻,体现在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表面繁荣但皮肤下暗藏着病灶毒瘤的现代工业社会人的洞察,他独到地揭示了文明的异化问题。据马尔库塞的看法,城市人当然只能就是现代文明的畸形儿——“单面人”了;或许,这是事实。但人总是要冲破宿命而寻找到自己的造化,人的伟大就体现在这里。人类(城里人)既然已经明白自己处境尴尬,必然会起而反抗命运的不堪。
城市化带来人性的恶化,归结起来,大致有这么几条: 其一,欲望的膨胀对人的精神挤压造成的人性痛苦;其二,文明理性制度对自然人性自由伸张的绑缚造成的人的活力窒息;其三,科技物性对自然人性的全面侵袭和替换导致人性大面积退化;等等。如果能找到可以缓解甚至于遏制这些“恶化”的方略,城市人自然也就可以寻找到摆脱自己生存尴尬而不沦落为可悲的“单面人”的办法了。理想的实现也许漫长但终究是有可能的。当然,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所有美好生活的实现都只能依靠人类自己;要改变城市人落为“单面人”的悲剧,只能依靠城市人自己。实现理想的途径其实有千万条,但落实到“审美构建”层面上,关键在于城市人必须敢于面对生存的处境,承认所有合法的或不违法的世俗生活,但又不能拘泥于这样的生活,要对世俗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保持必要的批判和超越,通过感性化(丰富而具体的)创造,努力赋予世俗生活价值意义。简单地,通过个性化的创意,让城市化沿着人化(诗化)的方向发展。
创意,个性化实现诗意,这是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城市诗意产生的必然道理。当然,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美学哲学命题,远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它们也绝不是让人闻而生畏的大道理。简单举例说明,比如,现如今有人说: 今天我们在城市里“吃土鸡”不再是“吃土鸡”,而是“吃文化”;这其中的把“吃土鸡”经营成“吃文化”的创意,毋庸置疑就是一种新的城市诗意。创意,其实是可以无处不在的,由文化部门主持的一次赈灾文艺表演,是创意;城市歌手在地铁出口处为匆匆的路人弹奏一段动听的吉他,这也是创意;就连政治演说,也可以经营成一种文化的创意,比如说,奥巴马的总统竞选和就职演说,就堪称这个城市化时代里最好听的诗歌之一。再者,在城市繁华喧嚣处开辟一片绿地花园,这是不错的创意;把水管设计成好看的藤条,是创意;开一家中国特色化的肯德基店是创意,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等,这些更是容纳了诸多元素的巨大创意;具体到作家艺术家们的艺术创作,更是千面各异的生命创意……这样那样的创意,它们因为浸泡了城市人的心智念想和热情爱意,诗意便由此蓬蓬勃勃产生了。
3. 生态审美理念的时代境界
构建源于观念(或信念)。欲构建适合于这个时代的“诗意”,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人文的文化理念(或信念)。当下,人们普遍认为,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生态时代”;这样的一种时代命名,其实也还是城市化时代的一种人文信念称谓罢了。“生态,从本质上说,是指生命体的生存状态。从人文视野来看,生态是指人适应环境的方式,人与环境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共处的生存状态,包括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层面。现代生态学认为,人、社会和自然是有机联系统一的整体,主张以系统整体的眼光来观察和理解现实世界,承认并尊重自然界中所有生命与非生命体都具有内在均等的价值,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与发展。”彭文忠: 《论韩少功〈山南水北〉的生态意识》,《云梦学刊》2008年第5期。这样说来,在这个时代里,“生态关怀”毋庸置疑要成为最为响亮的时代文化构建的关键词,城市诗意的构建自然必须具备“生态关怀”的时代境界。
所谓的“生态关怀”,具体到城市人来说,大致可以这样表述,它指人应该具备的一种为人情怀,即城市人对于自己与自然共处的世界(以地球为中心)的关心和爱护,对人类生存环境(地球家园)的珍惜,对大自然和一切生命的敬重;一种倡导亲近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人文情怀;主张通过自然生态诗意,让城市化走向自然化、生态化,让城里人可以回归到自然的宁静和舒畅之中,诗意的栖居;等等。在生态时代,“生态关怀”应该也必然要成为除“人文关怀”之外另一种普世的价值论,时代的审美创造必然要传达这样的文化信念。
在城市诗意构建话题上,生态关怀属于审美学——生态审美学话域,生态关怀可以说是生态审美学一个最为核心的术语(或理念)。关于生态美学,在当前已经成为人文社科一门显学,其中原因,倒不完全是学者们追逐时髦,它的提出和施行确实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某种迫切需要。在现代化(包括城市化)过程中,人类曾走过大弯路,受现代人类本位主义的影响,人类曾经对大自然犯下太多的罪行,并且因此陆续遭受大自然的惩罚。生态美学的基本使命其实是有关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大课题。生态审美强调“人要敬重自然,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人类对大自然过分轻视和随意掠取”;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命与生存之源,人类应当对自然怀有感恩之心,不要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自然具有人类难以穷尽的奥秘,人类应当对自然存有敬畏之心,不要认为一切都在人的掌控之中”;认为“天地自有大美”(庄子),“反对以人为之美戕害天地之美”吴廷玉: 《现代人能否实现诗意的居住——宜居城市的人文美学内涵》,《城市发展研究》2007年第3期。;等等。
简而言之,包括“生态关怀”核心价值理念在内的生态审美学有关主张,对于今天在中国城市化的具体语境下构建新的城市诗意,无疑是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值得进一步探讨。
结语: 西西弗斯神话的隐喻
概而言之,这是一个因农民进城而出现的中国问题——城市化问题。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城市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传统的乡村社会在中国城市化的潮流里将逐渐淹没。巨大的城市还在急速增扩、肥大;古老的田园牧歌和永恒的信仰在这里将不复存在。但,城市躯体也并非就一定仅仅是冰冷的“水泥森林”。城市化,不等于必然就要去除文明和文化,去除感情和人性,去除审美和诗意。
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城市的物质性文化在提供人类消费享受的同时也难免要强加其坚硬和威压;城市的制度性文化在给人类秩序和文明的同时也免不了要对自然人性带来某种刻板和束缚;是城市都难免热闹喧嚣,讨价还价使然,但非其如此,城市又哪来的大流通和大便利呢?西西弗斯神话的隐喻人们耳熟能详;文明,或者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但人却没有可以推卸和逃离的机会,人只能担当,不断努力前行。城市化,既然是人类特定历史必然选择,其必然也存在着悖论;但城市人别无选择,能选择的唯有把城市化做得更好。这样来看待问题,至少在心理上可以找到平衡和安慰,不然就只有绝望了。
所以说,如果城市化对许多人来说是无奈的选择;那么,建构新的“城市诗意”以达“诗意的栖居”,则应是城市化了的人的理想选择。城市化,即便像悲观者所言,它意味着传统牧歌的全部丢失,上帝也不再光顾,但城里人也还是想要经营着自己的幸福。在城市化时代,城市人能做的唯有坚持每一个人自己的良心和爱意,执著于世俗欲望的现实当中,疼痛但快乐地创意并栖居于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诗意里——“诗意的栖居”,让身体和灵魂同时舒适安居,这其实应该可以当成是城市化的信念;坚信于这样的信念,并努力施行;“Better City, Better Life”(“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终究是能够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