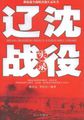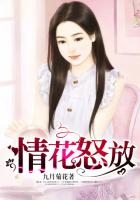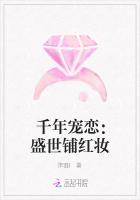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在于作家对于当下人类生命价值状态的疑问、探讨和发现。接受所处时代社会事实,肯定欲望社会的合理性,真诚地走进这个社会,但又不能沉湎于其中,而是努力发现这个社会的局限,以个体生命悲悯情怀,热情关注,去挽救那些在这个时代里不幸被异化甚至于可能被淹没、扼杀的柔弱美好人性,弘扬新的更合乎文明的人性,这是当今世俗时代文学创作能够成为真正的审美创造的理论依据。
审美与欲望是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话语冲突,审美不等同于欲望,但文学创作却不能离开欲望,把欲望抽空了的审美肯定也就丧失了审美本身。以下试图通过对文学创作与生命欲望的纠缠、中国的“当代性”与文学生命的生存处境、“当代性”下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这三方面的阐述,以期对理解审美与欲望这一话语冲突有所裨益。
一、 文学创作与生命欲望的纠缠
文学离不开欲望。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学是人学。文学通过作家心灵反映社会人生,而人生则充斥着各种欲望,生命的目的无非是欲望的实现,这是一种本能的要求,“所谓本能,实际上是一种人类固有的动力,处在它的作用下,人类产生满足自身欲望的要求;在适当的条件下,它升华成为文明的原始推动力”苏隆: 《弗洛伊德十讲》,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页86…无疑,文学成为生命本能实现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
作家是人性灵魂的看护者,他们自由地探讨人性、抒写人性、呼吁人性;他们以提供精神家园作为人类心灵的安居,浮躁和急功近利是不能履行好这一职责的。创作实践证明,伟大作家往往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作家确实不应该背负太多的个人世俗欲望。但就心态而言,真正的作家也一定具备尽可能大的欲望,如果没有对现实个体生命的执著,没有对理想社会的苛求,没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没有巨大的悲悯情怀,那么,真正的文学作品和伟大的作家又从何诞生呢?作家“可以远离奢华,但却不能没有为人的一份宁静、自由,以及蕴含了内在张力的那种创作的激情和欲望”张炜: 《艾略特之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28…所以,远离欲望绝不可能是文学创作本身,只能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前提性心态条件(当然,这样的条件也非常重要)。作为人学的文学,文学生命其实也必须遵循或起码暗合于人的生命律动;文学生命说到底无非是人的自然社会生命的外在表现(以“语言形象”的艺术形式)。自然社会生命律动过程中充斥着人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情感水涨潮落,欲望纠缠不休……在文学生命里,人类的各种欲望和各式情感在作家笔下被浇灌得越鲜嫩、越斑斓多彩,作家创作出来的文本就越会受到读者欢迎,因为读者在这样的文本中可以自由地实现自己的“生命关照”;而这样的关照又成为人类最为原始而持久的生命情结之一——即人类特有的“生命审美需要”其中的重要一种。
因此,笔者认为,其一,欲望本身不是审美,但把欲望抽空了的审美肯定也就丧失了审美本身;其二,欲望多种多样,文学创作生成的审美品质关键在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生命欲望的洞察、占有(想象性的)、归位和处理——即作家驾驭和超脱自然生命欲望的方式和功力。欲望(指自然欲望)不等同于审美,因为审美是非自然的精神性存在;但欲望无疑又成为人类审美构成的基质元素,没有这样的基质元素,审美就会变成没有细胞的躯体,成为不可能。文学生命“根源潜藏于人性的深处;物欲、情欲、智欲共生互动,构成人性的原生态;人性三欲的涨落与外化,生发出人类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也创造了文学”汤学智: 《生命的环链——新时期文学流程透视(1978—1999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当然,从自然欲望到审美,必须经历一个生成的过程。就文学创作而言,其生成机制可以简单地概括为: 创作是作家对生活的一种虚拟性还原。这种还原有的偏于客观,有的偏于主观;前者被称为现实主义,后者则是浪漫主义,当然,还有许多介于两者之间的“主义”。这种还原同样是一个全息的生命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中“应该有的”和“可能有的”一切纷纷归位,一样也不会少,同时,也包括各种欲望和追随欲望生成的各种生命痛苦。例如,曹雪芹创作《红楼梦》,作家对封建末世贵族家庭生活的虚拟性还原: 红楼公子的痴情、红楼女子的哀艳、贾府主子们的糜烂、各式权欲的明争暗斗、各式命运的际遇与痛苦……作家挥洒如椽巨笔,刻画栩栩如生,一切犹如在眼前展现。在这个还原的过程中,创作主体绝非被动、无为,相反,他积极参与,与整个过程共始终。其中又可以分成(只能是理论上分,实际创作中是盐水中盐和水的相融的关系)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创作者对所还原的各种生命欲望生活材料进行艺术语言照顾,使之形象化、个性化,这是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最基本的任务;另一方面,创作者要用感情去浸染、用灵魂去烛照这些形象,即赋形象以文化价值意义,这又成为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最高职责。文学作品的精神质量最终取决于作家的心灵质量。唯有纯正高雅的心灵,才可以创作出震撼世人的伟大作品。《红楼梦》之所以伟大,说到底应归功于曹雪芹对于人类生命尤其是对于女性美丽生命的挚爱。所以,历来人们不仅强调作家的艺术修养,而且也更加强调作家的人生修养,倡导作家的人格独立,讲究“童心”、“真诚”。
二、 中国的“当代性”与文学生命的生存处境文学创作既然是生命律动的外在表现,其发展历程就应该与历史时代特定生命际遇相一致,与人性历史时代特征相吻合。那么,生命的处境——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问题就相应地浮出水面,这些问题,当下文艺理论界往往运用一个非常专业的术语来概括——即“现代性”,有的甚至用“后现代性”。
学者们曾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拉康、福柯、哈贝马斯等人那里搬来一套套“话语”,并对其作了许多精彩分析,但也难免有时陷入“言不及义”或“言不由衷”的尴尬局面。为此,有学者提醒:“有关现代性问题……可能会滑入另一种陷阱。”蔡翔: 《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阅读札记》,《回答今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82。其实,中国文化问题最终只能回到中国现实的土壤上来方有可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真正答案,“生活在别处”(卢梭语)式的文艺批评家,其理论往往是隔靴搔痒,抓不到关键处。
中国的“当代性”(也称“现代性问题”)可以这样简单地描述: 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时期。其改革发展的内驱力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刚刚被解放出来的“人欲”中的“物欲”,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地表现在改革开放前期阶段;延期到当下,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当然,这是历史的无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被动的选择。正是这种被动的选择,使得中国的“当代性”(仅特指问题方面)产生了: 精神下滑,理想出轨,价值紊乱,人们被欲望驱使前进,重建新理性秩序社会任重道远。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将这个时代命名为“欲望时代”(也有称“世俗时代”或“物化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