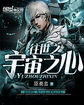故乡系丘陵而非大山,但那半坡浅土层下或裸露的坡壁仍是坚硬的、沉默的、无情的石头。
于我而言,故乡石早已不足为奇。父老乡亲们将石头打成块,用来铺在泥泞的小路上,用来安放在池塘边作洗衣石,用来垒猪圈,用来做磨子,用来盖房屋。盖房屋,不仅仅是作地基用,而且用石头来做墙体,甚至还有用来做房顶的。记得小时候,村里古董寺半坡上的一长排猪圈就是整个用条石头修建的。而且那个屋顶不是平坦的,被设计成了由一个个小拱形组成的波浪形。当时觉得挺新鲜的,别是一种风味。后来,兴起上山下乡热潮,城里来的姑娘小伙没住处,便安排在这里,猪圈一下就变成了知青场,非常热闹。后来,我社社长也照葫芦画瓢,一模一样,全用石头建造了一幢新房。相比之下,我大哥的石头房就一般了,屋顶既非石头,也非拱形。不过,在分家后能单独建此新房,在我眼里也是不简单的了。后来,我大哥将此房转让给了二哥。大哥到哪里去了?到城郊去了。大哥之所以要走,能走,不为别的,只为他能打石头,能将一礅礅的条石变成一块块的金砖。
故乡很穷。父老乡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辈接一辈都在修理着地球:播种、栽秧、割谷、收获、播种……后来,学会了种菜。尽管种菜技术好,蔬菜收获丰,可因附近没有工厂、没有城市,只有座小小乡场,需求量小而回报菲薄。不知是谁发现了埋藏在黄土地下的石头的价值。于是,村里就有了石塘口,一天到晚回荡起叮叮当当的打石声,还有那呀依嗬的号子声。我的三个哥哥因年轻力壮,便先后加入到了打石队伍,成了打石匠。
打石头那可是个真正的体力活,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天打下来,尽管人年轻,可还是有些吃不消的。我是家里的老幺,很是享福,既没顶着烈日栽秧搭谷,又没为生计半夜三更去田里捉黄鳝泥鳅,当然更没握过钢钎铁锤打石头。尽管如此,我还是能体会那打石头的艰辛。不但艰辛,而且很危险。有时,需要站在高高石壁上挥起重重的铁锤喊着号子使劲向脚下插进半壁石缝里的楔子砸去。倘若重心不稳,就有可能一头栽下石壁,那可是不堪想象的事情。那年月,饭一般都吃不饱,有一点米也只能煮成稀饭。对父母给卖力气的哥哥们将饭勺得稠一点,我是理解的,一点也不认为父母偏心而生气。至于石头怎么卖,价钱多少,卖到何处,用途是啥,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因为我把心思都放在了读书上。我只知道因打石头,有点经济来源,家里还算过得去。有时还能吃上肉,打上牙祭。后来,大哥因为亲朋好友的帮忙,离开故乡,独自闯荡,在城郊开辟了一方新天地:还是打石头,当上了小老板。有了自己的事业,越干越顺趟,越干越红火,建了楼房,娶了媳妇,媳妇还是村长的女儿呢。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
春节回家。一家四兄弟又见面了。大哥二哥笑呵呵,只有三哥一脸愁容。他说,他差一点见不着我们了。我们一听,吓了一跳。咋啦?在欢乐的气氛里乍听这种话,心里不是滋味。他说,他前两天打石头,差一点从崖上摔了下去。他摇头叹息道:老了,真的老了。以前从来都没这现象。还有,一天他去整修漏雨的屋顶,两眼一花,也是差一点从屋顶摔了下来。我们都好言劝他:年纪大了,别像年轻时那样逞强了。打石头等重活、危险活,有的让下一代去干,有的请人不就得了。曾经英俊潇洒而今却有些苍老的三哥望着前方山坡上母亲的坟墓,眼里有些湿润。我的母亲过世后,前两年才垒的坟。一堆黄土在我大哥的亲自料理指挥下,变成了一座全部由石头砌成的有些富丽堂皇的坟冢。坟前还竖着一块镶刻着儿孙姓名的花岗石墓碑。坚硬的石头,不但可以作生人温馨的房屋,而且可以成为逝者永久的住处。虽有些冰冷的石头,却充满感情地伴随着父老乡亲们度过一生一世,来生来世。
故乡石,你像黄土一样,终身与人相伴,一身全部奉献,并非冰冷无情物!故乡石,你不就是父老乡亲的化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