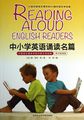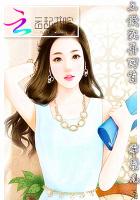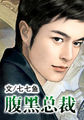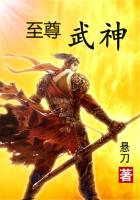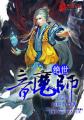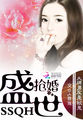童年,我是在锦西、锦州和葫芦岛三地度过的。在锦州的时间最短,而且似乎是在五岁左右完全懵懂无知的时候,因此,对锦州的记忆也极其模糊。
记得头两次去锦州,是在正月里,由姥爷、母亲带着我由锦西乘火车去给太姥爷拜年。
太姥爷个子不高,胖胖的,脸膛像紫铜盆似的流光溢彩,还有两撇灰白的八字胡,整日穿着古铜色缎面皮袍子,不苟言笑,显得冷峻威严。
不知怎么,姥爷很少跟他说话。当然,刚见面时,头是要磕的,但很少说话。好像姥爷乘火车大老远赶来,仅仅是为了给太姥爷磕三个头似的。白天,太姥爷在他的小屋里盘腿打坐,而姥爷则躲到别的屋里翻看闲书,或者在灰墙合围的庭院里踱来踱去。以后,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中,我才知道太姥爷对姥爷管教甚严,有时甚至不免粗暴,可能因此姥爷才离开锦州,跑到当时还很僻静的锦西去寻找自由的生活吧?
在太姥爷家,我过得也很寂寞。爆竹和灯笼是有的,但没有同龄的小伙伴。连平日很疼爱我的姥爷,也不大和我亲近。晚上,我怀里装着爆竹,打着纸灯笼,在院里的雪地上四处奔走,摔得满身都是雪。
过了正月十五,姥爷便带着妈妈和我,郑重地向太姥爷辞行,对太姥爷的种种吩咐诺诺连声,然后便拎着太姥爷送给妈妈和我的大包小包,钻进去火车站的马车里。车夫鞭子一响,车轮滚动了,姥爷的脸上也就欣然有喜色了,好像他刚从囚禁之中被释放了出来。
不久,父亲从锦西邮政局调到锦州邮政局,我和妈妈也随同去了锦州。
我们住在一幢红色砖房里。窗外有一个整整齐齐、四四方方的小院子,没有树木,没有人迹,只有墙根下钻出一丛丛绿色的小草,冬天铺的满满的白雪。
不知为什么,小院的门经常锁着。我几乎整天憋在屋子里,很少外出,对一个学龄前的男孩子来说,这大概是最大的不幸。
有一次,妈妈上街了,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
正是春天,小院里洒满阳光,明亮、妩媚、和煦;小草绿茵茵的,挺着细嫩的身躯迎接阳光的照拂;透明的空气里好像漂浮着四月原野上的芬芳。我实在经不起这美妙春光的诱惑,勇敢地推开窗户,爬上窗台,“咕咚”一声跳了下去。我在院子里奔跑,像小草一样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迎接阳光的沐浴……
日常生活,是百无聊赖的。岂止百无聊赖,还有一种当亡国奴的惊恐之感压在大人们的心头,小小的我,似乎也能感受一些。
那一年中,我们的饮食十分粗粝。早晨常常喝一种颜色浑浊的稀粥,味道很不好;下饭的只有一碟切得筷子粗的萝卜咸菜。当我对这种单调粗劣的饭表示孩子式的抗议时,妈妈就悄声警告我:大米,中国人不能吃;偷吃犯法,会被日本宪兵抓起来!我不知道日本宪兵什么模样,但从大人们谈虎色变的神情里,我猜想得出,那一定是一群凶神恶煞。
夜间,家里点的是蓝色灯泡,像一个长茄子;窗户上挂着厚厚的黑布帘子;是防空用的。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而这时,街上卖夜宵的小贩的叫卖声,在木头梆子单调的伴奏下,就显得格外苍凉、悠远。那凄切无望的味道,好像现在我还能回味得出。
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跟着父母离开东北,在北京定居了。每当乡愁缭乱之时,我想起锦西清浅的北河,葫芦岛巍巍的东山,也想起锦州的古塔和夜晚街头苍凉悠远的叫卖声,我愿意说,我童年的岁月,有一部分交给了锦州。
“文化大革命”后期,有一次我乘火车从北京去哈尔滨。上车时,我提醒自己,车过锦州,一定要到站台上踏踏锦州的土地,聊慰多年思念锦州之情。可一觉醒来,列车早已驰过锦州了。
近两年,我一直想去看看锦州,有一次,我甚至已经下定决心,但临行前又不得不改变主意。前些天,我在给辽宁一位作家的信中,又谈到这个愿望——我也只能说,但愿今年能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