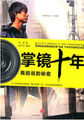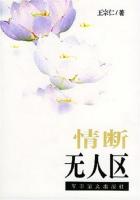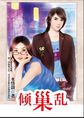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王朝。元朝的统治阶层一向看重实利,鼓励商业,对传统儒学虽有所利用,但终究不是很重视。同时,元代前期一度废止科举,对文化人的生活道路更带来严重的影响。按明代方孝孺的说法,是“元以功利诱天下……而宋之旧俗微矣”(《赠卢信道序》)。
随着大批文化人失去仕途希望,他们也摆脱了对国家对政权的依附。而由于城市经济造就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消费需求,他们可以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获得对真实人生的亲切的理解。就这样,元代社会造就了一群杰出的非传统类型的文人,他们开始具备自由职业者的某些特征。
元代文学正是因此而呈现出异常的活力。像杂剧、说话、讲唱等通俗性、大众化的市井文艺形式,在民间已经流行了很久,它虽然内蕴着生机,但在尚未有杰出的文人参与创作时,并不能产生优秀的作品。到元代,我们看到众多富于天才的作家投入到杂剧的创作中来。像关汉卿、王实甫诸人,他们的原创性才华绝不逊于文学史上任何其他大家。由于这些人的加入,中国戏剧很快走向成熟并呈现出辉煌的光彩。
元杂剧的体制
元杂剧是在宋、金杂剧的基础上糅合了说唱艺术“诸宫调”
的多种特点,并从其他民间伎艺中吸取了某些成分而形成的,它是完全的代言体。
元杂剧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以四折、通常外加一段楔子为一本,表演一种剧目;只有极少数剧目(如《西厢记》)是多本的。一“折”意味着一个故事单元,同时也是音乐单元;每一折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组成(元代流行的宫调有九种:仙吕宫、南吕宫、正宫、中吕宫、黄钟宫、双调、越调、商调、大石调)。“楔子”是对剧情起交代或连接作用的短小的开场戏或过场戏,通常只有一二支曲子。
元杂剧通常限定每一本由正旦或正末两类角色中的一类主唱;正旦所唱的本子为“旦本”,正末所唱的本子为“末本”。
一人主唱的规定对合理安排剧情和塑造众多人物形象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元杂剧的脚色,可分为旦、末、净、外、杂五大类,每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以此把剧中各种人物分为若干类型,以便于带有程式化的表演。
女人的命运
一种新的文艺样式需要伟大的作家将它提高和定型。对于元杂剧来说,最重要的奠基人是关汉卿。关汉卿由金入元,是创作年代最早的作家之一,所作杂剧见于载录的共六十六种,现存十八种,作品数量和类型最多,艺术成就也最为杰出。
《窦娥冤》是关汉卿的名作之一。剧中主人公窦娥是个弱小而善良的女子,母亲早亡,父亲因欠下高利贷无力偿还,将她卖给蔡家作童养媳,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地痞张老儿、张驴儿父子欺负蔡家婆媳无依无靠,赖在蔡家,逼迫蔡婆婆嫁给张老儿、窦娥嫁给张驴儿。蔡婆婆软弱怕事,勉强答应了,窦娥却坚决拒绝。
张驴儿怀恨在心,偷偷在窦娥为蔡婆婆做的羊肚汤里下了毒药,想毒死蔡婆婆,再以此逼窦娥成亲。不料汤却给张老儿喝了,中毒身亡,张驴儿遂把杀人的罪名栽到窦娥身上。
楚州知府桃杌是个昏聩的贪官,被张驴儿用钱买通,百般拷打窦娥,最后将她冤杀。在刑场上,窦娥满腔悲愤地咒骂天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
《窦娥冤》具有强烈的悲剧特征。作者从两方面加以强化,使戏剧中的矛盾冲突显得极其尖锐:一方面,窦娥是个毫无过失的弱女子,具有社会所赞同的一切德行,而另一方面,剧中所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包括窦娥的父亲和她所孝敬的婆婆,都或多或少、或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窦娥无穷的不幸,而地痞恶棍加上昏庸贪婪的官僚,最后把她送上了断头台。这一结果彻底颠倒了普通老百姓所信奉所要求的善恶各有所报的法则。而且,这个故事不仅仅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平,由于善良的被粉碎是绝对化的,这引导人们以超越具体事件的态度来看待人类的秩序,在观众心理上,掀起了巨大的感情浪涛。
尽管作者没有能够把悲剧的力量维持到底,最后她的经科举做了官的父亲平反了冤案,从而缓和了剧中的激情,但它仍然使人们感受到极大的震撼。王国维认为将《窦娥冤》放在世界伟大的悲剧中也毫不逊色(《宋元戏曲史》),并不是夸张之谈。
中国戏剧从其形成过程来看,以滑稽、调笑的方式取悦观众一直是主要的特点,像《窦娥冤》这类悲剧的出现,极大地扩张了戏剧的艺术力量。
《救风尘》则是结构巧妙的喜剧,它和《窦娥冤》有意无意地成了一种对照。剧中三个主要人物性格鲜明,配合得恰好:同是风尘女子的宋引章和赵盼儿,前者天真轻信、贪慕虚荣,后者饱经风霜、世情练达;而另一角色周舍,则是个轻薄浮浪又狡诈凶狠的恶棍。宋引章被周舍所骗,赵盼儿利用周舍好色的习性,以身相诱,将她救出火坑。剧中周舍作为恶势力的代表被放在受愚弄的地位上,他由于自身的卑劣品格而受到诱骗,终于大倒其霉,这无疑给普通观众带来很大的快感。而通常为社会道德所不赞同的色相欺骗,成为代表正义一方的必要和合理的报复手段,这显然反映出市民社会的道德观念,剧情也因此变得十分活跃。像赵盼儿对周舍指责她违背咒誓时的回答:“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 ”那真是理直气壮,泼辣得很。与窦娥的悲剧相比,赵盼儿的故事似乎证明了,在险恶的世界里,你要比恶人更强悍才能保护自己。
关汉卿杂剧的题材、内容、风格是多样化的,总的说来,这些作品显示了根源于作者自由的个性与博大的胸怀的活跃而强大的艺术创造力。而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集中反映了弱者的生活遭遇和生活理想,既揭示了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也反映出他们顽强、机智的斗争精神,有力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
墙头望见白马郎
人周德清《中原音韵》一书中将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并列,后人因而称他们为“元曲四大家”。其中白朴是唯一的出身文学世家的名士(其父白华是金朝名诗人),他留下两部剧作:《墙头马上》与《梧桐雨》。
《墙头马上》的素材源自白居易新乐府诗《井底引银瓶》。原作写一名少女与情人私奔而最后遭遗弃的故事,其主题在诗的小序中明言为“止淫奔”,是为道德教化而作的,但诗中又将私情故事写得颇为动人。后人在沿用这一素材时,却改变了故事的主旨。尤其白朴的《墙头马上》,热情赞美男女间的自由结合,主张私奔有理,和白居易原诗的立意针锋相对。
《墙头马上》的情节与白诗大略相似:洛阳总管李世杰的女儿李千金在花园墙头看到骑在马上的裴尚书之子裴少俊,二人一见钟情,李当夜随裴私奔,在裴家后花园暗住七年,生一儿一女。裴尚书发觉后,逼裴少俊休了她。后裴少俊中状元,以母子之情打动李千金,夫妇才得重聚。
李千金是剧中最重要和最具有个性的人物。她一出场的唱词便大胆表述对于满足情欲的要求,说是愿有“风流女婿”,与之共度人生好时光。在见到裴少俊后,她不但一开始就主动约他幽会,而且自始至终,都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私奔行为辩护,用泼辣的语言回击裴尚书等人对于自己的指责。在“大团圆”的庆宴上,她还将自己和裴少俊之事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之事相比,宣称:“怎将我墙头马上,偏输却沽酒当垆。”
总之,通过李千金这一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剧本对自由的爱情、非礼的私奔、男女的情欲都作出率直袒露、毫无畏怯的肯定和赞美,这个形象是过去文学中所没有的。从中可以看到金、元入主中原以后中国文化有趣的变化。
《梧桐雨》取材于白居易的诗《长恨歌》,在描述唐明皇与杨贵妃之爱情悲剧的过程中,着重刻画了唐明皇的内心世界:由于政治上的失败,他从权力的顶峰跌落,失去繁华辉煌的生活,失去美如天仙的杨妃和如痴如迷的爱情,在孤独与苍老中感受着美好往日如梦消逝以后的寂寞与哀伤,一种对盛衰荣枯无法预料和把握的幻灭感。幸福是脆弱的,生命最终归于悲哀,这是剧中所传达的主要情调。白朴本人经历了金朝败亡、家族沦落的变故,这种描述显然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世沧桑之感。
《梧桐雨》是一部抒情诗剧,比之《墙头马上》的世俗化倾向,它更多地表现出文人化的趣味,尤其以典雅优美、富于抒情诗特征的曲词著名。特别是第四折,全部二十三支曲子几乎都是唐明皇的内心独白,写他的忆旧、伤逝、相思、愧悔、孤独、哀愁等种种心情。其中后十三支曲子,通过对秋雨梧桐的描写,反复地以凄凉萧瑟的环境与人物的心境相互映照,彼此交融,获得强烈的抒情效果。
皇帝他只会哀愁
马致远剧作今存六种,以《汉宫秋》最为著名。
此剧敷演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这一故事本来就有许多传说成分,马致远再加虚构,把昭君出塞的原因,写成匈奴引兵攻汉,强行索取;把元帝写成一个软弱无能、为群臣所挟制而又多愁善感、深爱王昭君的皇帝;把昭君的结局,写成在汉与匈奴交界处投江自杀。这样,《汉宫秋》成了一种假借历史故事而加以大量虚构的宫廷爱情悲剧。
马致远的杂剧写实的能力不强,也缺乏紧张的戏剧冲突,其长处在善于写优美的抒情性曲辞。其语言不像《西厢记》、《梧桐雨》那样华美,而是朴实自然与典雅精致的结合,前人对此评价甚高。当我们想起元杂剧是一种歌剧时,不难体会其中的道理。
浪漫在西厢
以单部剧作而言,王实甫的《西厢记》实为元杂剧中最为精彩和影响最大的一种。
《西厢记》的故事起源于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叙唐贞元年间有一自称“真好色”的张生于蒲地的普救寺与远亲崔氏女莺莺相恋、私通,而最后“忍情”相弃的经过。后世研究者认为小说所写实为元稹本人的真实经历,只是人物的姓名与身份经过虚饰。
由于《莺莺传》包涵了一个浪漫爱情故事的雏形,因而受到后代文学家的珍视。金代董解元的说唱文本《西厢记诸宫调》对《莺莺传》作了根本性的改造,故事的性质演变为争取自由恋爱与婚姻的青年男女同恪守礼教的家长之间的冲突,最终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王实甫《西厢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使故事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人物性格更为鲜明。它不仅热情赞颂了年轻人自由恋爱的美好动人,还成功地刻画了爱情心情,因而成为中国古代爱情文学的经典。
元杂剧以四折一本表演一种剧目和只允许一个角色唱的体制,对剧情的充分展开和多个人物形象的刻画造成了很大限制。《西厢记》则是一种规模宏大的多本剧,共五本二十一折(第五本可能是他人续作),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它因而突破了上述限制。
在情节上,全剧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解脱孙飞虎兵围普救寺的危局,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
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他们与老夫人是戏剧冲突中对立的两方,而同时,在同一阵营的三人之间,也存在因性格而产生的内部冲突。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他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成为剧中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莺莺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红娘在剧中是格外活跃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她虽只是个小小奴婢,却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所以她在精神上总是充满自信,居高临下,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词驳斥。
由人物性格的冲突推动剧情的起伏变化,是《西厢记》一个杰出的优点。
优美的语言也是《西厢记》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和关汉卿杂剧的“本色”风格不同,《西厢记》有一种华美的诗剧风格。
它的曲词广泛融入源于古典诗词传统的语汇、意象,与鲜活的口语巧妙地结合起来,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描述得风光旖旎,情调缠绵,声口灵动,格外动人。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又像“长亭送别”一折中莺莺所唱的《端正好》: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前者写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后者以秋天之景衬托离人之情,语言十分漂亮。我们在《红楼梦》中看到宝玉、宝钗、黛玉等人都曾偷读《西厢》的情节,自然会感受到它在爱情受到礼教禁制的时代所具魅力。
坚忍与复仇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是一部强烈的悲剧杰作,也是最早传入西方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伏尔泰曾将它改编为《中国孤儿》。
此剧主要根据《史记·赵世家》所记春秋晋灵公时赵盾与屠岸贾两个家族矛盾斗争的历史故事敷演而成。剧中的屠岸贾被描绘为极其凶狠残暴的“权奸”式人物,他不仅杀害了赵氏全家三百余口人,连刚出生的孤儿也不放过。赵朔门客程婴将赵氏孤儿偷带出宫,奉命把守宫门的韩厥不忍小儿被杀,遂放走程婴,自刎而死。继而屠岸贾下令杀死全国出生一个月至半岁的婴儿,程婴与赵盾友人公孙杵臼商定计策,以己儿冒充赵氏孤儿,然后出面揭发公孙收藏了他。公孙与假孤儿被害,真孤儿得以保全,长成后程婴向他说明真相,终于报了大仇。
《赵氏孤儿》的故事带有“忠奸斗争”的意味,但其真正感人之处,是突出描写了一群具有正义感的人对残暴势力的反抗。他们或杀身成仁,或忍辱负重,以最大的牺牲履行自觉选择的使命,使人格在高尚的境界中得到完成。如年老的公孙杵臼觉得救孤而死,比无聊赖的生更令人欢喜和兴奋,高唱:“大丈夫何愁一命终?况兼我白发蓬松!”而程婴为了救孤抚孤,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毁弃名誉,承担了更大的危险和精神压力。总之,剧中主要人物是在与强大的外部力量的对抗中实现其个体意志的,因而戏剧冲突尖锐激烈,矛盾连续不断,气氛始终紧张,呈现出典型的悲剧美感。
只有灵魂是自由的
郑光祖剧作今存七种,以《倩女离魂》最为著名。此剧据唐人陈玄祐传奇《离魂记》改编而成,写王文举与张倩女原系“指腹为婚”,彼此相爱,文举因张母嫌其功名未就,被迫上京应试,倩女之魂化而为二,其一离开躯体去追赶王文举,与之相伴多年。王文举中状元后,携倩女魂归至张家,离魂与留在家中的倩女重合为一。
这一剧作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利用荒诞的情节更深入地写出旧时代女子在礼教扼制下的精神生活。一方面,倩女的离魂为追求爱情,违背礼教,大胆地追随情人,表现得十分坚强和勇敢。可以说,离魂代表了这一类妇女内在的欲望和情感的力量。而另一方面,留在家中的倩女辗转病床,苦苦煎熬,当王文举寄信到张家,说要和妻子(即倩女的离魂)一同回来时,她以为他另有婚娶,不由得悲恸欲绝。这一倩女形象则反映了妇女在婚姻方面受制于人的事实。
郑光祖杂剧的曲词语言精美、抒情色彩浓郁,显示了较高的文学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