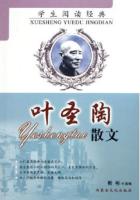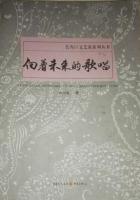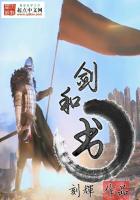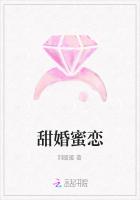1801年6月,耶拿大学讲坛举行博士论文答辩。
这是一场明显不公平的答辩。考官们存心要与博士候选人过不去,他们中的一位辩驳人,态度倨傲侮慢:“IN TRACTATU TUO EROTICO LUCINDA DIXISTI……”(拉丁文,意为“至于你那本色情的《卢琴德》……”),答辩人则当众称辩难人为“蠢货”作为回敬,以致全场哗然。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里载录了这段往事。这位博士候选人便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当时德国最有创见的批评家和作家。
弗·施莱格尔的长篇《卢琴德》受到指责的重要原因,据说因为通篇是个人色情心理浓厚的自白。但据勃兰兑斯称,后来叔本华以《性爱形而上学》为题所写的几页文字,要比《卢琴德》包含得更多,言下之意,《卢琴德》实在算不得色情。《卢琴德》遭人攻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不得不归咎于它在写作上的别开生面。
在我看来,《卢琴德》堪称二百年前一次意味深长的综合性写作的尝试。在这部作品里,所有的文体归类原则被搁置在了一边,作者拒绝任何单一写作向度的统摄,他有意识地将种种非小说的因素糅杂进来,里边既有编年纪事、哲学沉思,也有猜想飞逸的书信和长段抒情诗。诗与散文、哲学与修辞、各类异质性成分直接聚集在一起。无所不包、囊括一切而又言辞含混的写作,使之成为一部追求包罗所有写作向度的浪漫小说。
这一两百年前的综合性写作,显然基于作者对文学的特殊思考。弗·施莱格尔看出,各门艺术和各门科学的全部历史,最终将构成一个秩序,一个有机体或一部“百科全书”,并认定这个秩序是适用于所有有创意的批评的源泉。他心目中的文学,乃是“一个巨大的完全连贯而又经过有机组合的整体,在统一性方面,可以包孕许许多多的艺术天地,而它本身又构成一部独特的艺术作品”。显而易见,弗·施莱格尔对一种“普遍”的文学和写作更感兴趣。
《卢琴德》意欲穷尽所有写作向度的乌托邦冲动,究其原委,还与施莱格尔兄弟当年所倡导的美学史上著名的“讥讽”(ironic)说直接有关。在他们看来,世界就其本质而言,是似非而是的,因而只有凭藉一种矛盾反论的态度,才有可能抓住它互相抵牾的“总体性”。“讥讽”与反论相关,是一种反论形式,亦此亦彼,依违不定。“讥讽”态度是对无际无涯一团混乱的世界的清醒意识,同时也是高度的自我意识和“自由心境”。世界和人生总是显得那么矛盾重重、纠葛离奇,一个作家要是只会恪守门户,坚持用单打一的向度写作,终将无力深入这团哑谜内部。质是之故,作家须得以“讥讽”的态度对待作品,并以此不为任何形式所滞泥,永远从一种形式飞越到另一种形式,充分享受自由。这一“讥讽说”,后来在黑格尔和克尔恺郭尔那里曾一再受到非难,他们不约而同地指责这是施莱格尔兄弟俩信奉费希特自我哲学的结果。还是批评史家韦勒克在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时,针对黑格尔、克尔恺郭尔的责难,替施氏兄弟说了比较公道的话(见杨自伍译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二卷)。
《卢琴德》并没有获得什么享誉身后的福分,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历史上那些超前实验的前驱者的命运大抵如此。但隐潜在《卢琴德》背后的那种尽可能包容多种写作向度的诉求,还是遗传到了后世,并在20世纪作家身上有着不绝如缕的回响。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即是一例。依照法国文论家热奈特《叙事话语》中的说法,《追忆逝水年华》中议论之于故事的鸠占鹊巢,随笔之于小说的反客为主,叙事话语之于叙事本身的攘夺和干预,以及对传统小说的疏离和对宗教文学的某种亲近,使得这部巨制长篇体现出一种相当混杂、互渗的性质,拓开了人们重新理解写作的思路和界域。
自然,卡夫卡更是无从绕过的一个巨大的存在。记得好几年前,诗人王家新的《卡夫卡的工作》一文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内心突然有了一种被尖锐之物深深扎了一下的疼痛之感,我一下子清楚地意识到,在此之前,我们之于卡夫卡的种种高谈阔论是多么的不着边际。这种强烈的阅读印象,我在1997年夏季匆匆写就于武夷山的《坚持在差异中写作》一文中多少有所记述:
这几年间,从欧洲归来不久的诗人王家新,为我们写下了包括《卡夫卡的工作》《另一个维特根斯坦》在内的一系列因强烈地释放着内心尊严而令人感到惊异的文字。在这些文字的背后,诗人置身在生存的裂隙、边缘和差异处,那深度搜寻的眼神和沉静于思考的身影,因闪烁着思想在掘进中的力度和锋芒而显得格外的清晰动人。我想说,王家新这几年的诗文,是我近年所能读到的诗人之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状况最为深刻的剖析和警示之一。在《卡夫卡的工作》一文中,王家新向我们出示了一个在此之前一直为我们所忽略的问题,即卡夫卡的“难以归类”。在另一个地方,他将他的这一独见作了这样集约性的表述:“在卡夫卡那里体现出的‘存在的勇气’,在我看来还意味着敢于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从而在一种艰巨的历险中体现出叙事的可能性。”他接着诘问道:“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试一试?为什么我们总是画地为牢,而不让文学呈现出它本来的自由?”正好前一段日子,彭燕郊先生寄赠我一册他自己印制的长诗《混沌初开》,这个似乎有意违拗诗的整饬体式而写就的长篇巨构,同样激起了我内心一种持续的、隐秘的惊喜。如此迥然分属于两代的诗人,却在当今之世不约而同地做出了殊途同归的选择,这一事情的本身就足够让人寻味的了。这与其说是有意识的、精心的选择,不如说是诗人无条件地听命于早已深深植根在生命中的诗性原则召唤的结果。诗人无须像奥德修斯那样,将自己捆绑在船桅上,以抵御内心的呼唤。
把诗写得不像诗,或者不在乎自己写的是什么文体,只要足以保证自己是在一种明显确切的差异状态中对这个世界说话,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对他们说来,再也没有比这样一种足以保持精神高度自治的言说方式更具吸引力的事了。坚持在差异中的写作,是一种因心灵始终保持本质上的独特而显出令人欣羡的多面性和无限性的写作,这种写作如同写作者的思想和生命,永远逸出在现成的言说罗网之外,没有一张现成的有关诗的地图可以有效地标出它的位置。它使诗对世界的解释,自始至终具有一种复调的性质,而使一切意在将之纳入某种固定程式中的惯性力量归于失败。情况正如布罗茨基所言,在一个不再拥有中心文明的时代,保存文明的工作总是由身处边缘的人们来默默完成的。与人们一直深信不疑的情形正好相反,“边缘地区并非世界结束的地方——而正是世界阐明自己的地方”(《潮汐的声音》)。……与他们的写作相比,也许当代不少写得很像诗的东西,往往与真正的诗距离更为遥远。那么究竟谁更是诗呢?答案显然已不言而喻。
当时我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当代诗歌精神之于“差异性”的诉求上,可以说是别有会心。现在,为了着手写这篇短文,我再次将《卡夫卡的工作》细读一过,发觉上面的记述只是对王家新对于卡夫卡相当深入的诠释做了有限的截取,印象是不完整的。王家新独具慧眼地看出,卡夫卡身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对艺术家命运的承当精神,致使他的作品内部、他的整个文学工作,呈现出一种巨大而晦暗的性质,正是这份异于常人的承当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性质,有力地拒绝着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简单的归类。他敏感地发现,卡夫卡的日记、书信、随笔和小说,其实都是在不停地叙述着同一个故事。他进而对这种致使原有的文体分类原则“失效”的卡夫卡式的写作加以揭秘,指出这种写作的企图不在别处,而只是为了有可能“对整个文学说话”。这就是说,他把卡夫卡逸出单一写作向度之外的写作,再度提升到了追求“文学普遍性”这一精神乌托邦层面上来加以强调,从而无意之中提醒了我们,使我们恍然意识到,有一种内在的精神线索,隐潜和贯穿在弗·施莱格尔《卢琴德》以来,包括普鲁斯特、卡夫卡和博尔赫斯在内的众多写作巨子的幢幢身影之间,以便我们进一步就此做出一种家族谱系式的勾勒和梳理。他深信,在这样一种偏离规范、无法归类的写作中,反倒更能深刻地体现我们这个世纪文学对自身的意识,用他的话来讲便是,“随着原有的文学分野的瓦解,文学自身的性质突出了出来”。
我不清楚王家新这样一种说法在别人那里是否灵验,但在他自身,应验的迹象则是非常明显的:潜心研究一位作家的秘密,终将演变成为对自身的一种重新设计。正像我在两年前已说过的那样,近年王家新的写作总是逸出既有的言说罗网之外,由他自己命名为“诗片段系列”的那些诗作,如《反向》《词语》《另一种风景》《游动悬崖》……,往往很难找到一张现成的有关诗的地图可以有效地标出它们的确切位置。(与此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尖锐地存在于西川的《近景和远景》系列、陈东东的《词,名词》系列以及于坚的《O档案》之中。)另一方面,后来被他收集在一本随笔集子里的《饥饿艺术家》《卡夫卡的工作》《另一个维特根斯坦》……,像这些远离诗歌特定文体的写作,却又有着对诗境异乎寻常的深入,其内在的强烈诗意,反倒是我们在通常的诗作中难得遇见的。透过这些包容了众多向度而界域一时变得模糊未明的写作,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卡夫卡式的整体承当气魄、一种拒绝分类的综合性写作精神正在王家新身上悄然生长。由于得到了不同于以往的开阔语境的支持,90年代的王家新得以成为有力应对和处理当代现实,直入事情核心,避开了捉襟见肘的窘迫的写作者之一。对90年代诗歌稍加关注的读者将不难发现,这一综合性写作精神并非只是发生在一两个诗人身上的偶然特例,事实上,追求诗性的包容力,急切觅取汲收和整合现实经验的种种可能的方式,正是90年代诗歌谋求自身生长和确立自我意识的重要支撑之一。
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一些新的、原先陌生的因素被综合进了诗的躯体。其中人们议论得最多的大概要算是“叙事性”了。日常性的故事、事件和场景,不仅成了孙文波、张曙光诗境中的关键构架,即使在看似玩世,骨子里却相当专注严肃的90年代的肖开愚,以及格外倚重诗意理性在具体经验与冥想沉思间敏捷穿行的臧棣的一些诗境里,也时常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很难想象,剔除了肖开愚的《北站》、臧棣的《戈麦》和《未名湖》等诗作中的“叙事”因素之后,我们面对的会是怎样一种尴尬的局面?)而从现代分类学讲,叙事性本该是小说的专利。陈东东长诗《喜剧》对喜剧因素的利用,在坦然接纳一个严峻时代的同时,又将其异质的一面做了使人震惊的反讽性提示;翟永明90年代对复杂晦暗的人性的深入和洞悉,则完成于她对旧式戏剧装置的模拟和复制之中(见《道具和场景的述说》、《脸谱生涯》);西川更是在不同场合表示,1989年海子、骆一禾的死使他突然领悟到了真理的全部悖论性质,诗歌将无法回避悖论,由此他意识到,诗的大门必须打开,真正的诗应当是能够“容留”“不洁”的诗,他提到了“偏离诗歌的诗歌”的说法(《答鲍夏兰、鲁索四问》)。在另一处他这样说:
1989年使许多诗人在写作上转了方向,我也在思考怎样才能使我的写作与时代生活相较量。直到1992年,我开始从纯诗退下来,或者更进一步说,我把诗写成了大杂烩,既非诗,也非论,也非散文,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我不要那么多界线。(《与弗莱德·华交谈一下午》)
与80年代相比,当代中国进入90年代后,社会条件、现实性质和思想状况相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及文学的行为、职能、作用也发生了变化,知识分子的知识构型,他们与国家政治、与大众生活的关系,他们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批判精神,都随着现实境况的变化而出现了不少疑问。已有的诗思结构开始显得悬浮和无力。如何将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路一脉相承下去,从历史渊源和现实维度上沉着应对外部世界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化,有效且有力地表达诗人对于现实和自身心理的微妙体验和沉痛之感,便再度成为具体的问题。
谨以王家新近作《回答》为例。这首三百多行的长诗,一开始,诗行的推进显得相当的游移和踟蹰,笼罩在这样一种迟疑不决的气氛之中:
要回答一首诗,需要写出另一首,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
回答一首诗竟需要动用整个一生,
而你,一个从不那么勇敢的人,也必须
在这种回答中经历你的死,你的再生。
在当代中国,即使你只想谈论一个特定的个人的生活命运,也将不得不涉及那种逼人的复杂和广阔,那些与时间的整体性和包容量直接相关的东西,对之做出梳理,往往是一首抒情诗所难以承载得了的。我们多少有点意识到,抒写者一上来的逡巡不安,恐怕与此有关。接着长诗中又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虽然伟大的史诗尚未产生,
你却仿佛已走过了远远超过一生的历程。
个人的生命经验有其各自不同的结构和色彩,长诗的抒写者很清楚,一切虽是在早已远离了史诗时代的当代世界中发生着的,但你若想完整表达出这一生命经验,就不得不与“史诗”重新建立起一种关联。请注意,这里提到了“史诗”一词。
一般说来,影响一个诗人对写作方式具体选择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性格上的,心理上的,趣味、学识和抱负上的,感性直觉和生命体验上的……但诉求于打破现有诗歌界域的综合性写作,以开阔的语境主动接纳并承受起空前复杂的现实事务和人性动机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却在90年代成了观察、经验、想象和诗意理性各自不同的诗人们之间一种高度自觉的追求,成了他们“家族相似”的重要标识物之一。90年代诗人从各自不同的方向和立场合力促成的这一令人瞩目的局面,在我看来,是对诗本源的一次回溯。
说到诗的本源,它的初始、幽远状态,不能不上溯到“史诗”。我相信,王家新在长诗《回答》中所提到的“史诗”一词,肯定不是指我们以往熟稔了的那种意识形态的倡导物,即将整个民族的本质都指望通过写作来完成的那种“宏大叙事”性写作,也不会是指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诗所热衷的诗人对于历史文化那层神秘的先验关系的沉溺,而主要着眼于诗在未经分化的时代那份浑然庄重的精神气度,那种无所不包、大有统摄当时整个世界、包容其大部分学问的开阔之势,那种集所有写作向度于一身的写作精神。
知识分化和学际分科,是近代知识文化发展的标记和结果。迄今为止,知识的各个分支已得到了空前的开掘甚至极限性的深入,但知识的统摄性力量也随之而日渐消失,以致对生存经验整体说话,早已成了人们对遥远时代的一缕回想。诗是广义上的知识,它的演化自然也脱不开知识学的一般进程。历史地看,诗的演进就好比一道不折不扣的减法算术题,舍弃成了它被注定的命运。先是将叙述割舍给了戏剧,后来又割舍给了小说,它还把说教和训诫割舍给了鼓动家以及后世的政论和社会评论……在原有的无与伦比的包容性被一一蚕食殆尽的过程中,它守住了对抒情和诗意玄思的迷恋。尽管抒情诗也可以包括表达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的较大篇幅,诗中的观察、思辨、记忆和感情过程也可以用相当复杂的方式加以组织,但毕竟远离了包容所有写作向度于一身的“史诗”写作精神。它在达到净化自身的目的同时,也大大削弱了自己全面表达的能力。现在,则是需要它重新反思,开始思忖重新接上综合性写作源头的时候了。
对于承当着空前巨大的现实压力的90年代诗歌来说,返溯“史诗”精神无疑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提示。诗歌要获得开阔的视野和坚实的根基,就有必要恢复它多方面的能力,有必要敞开语境,将分离既久的种种写作向度重新接纳到诗境之中。举凡历史、伦理、语法、修辞……,所有与存在有关的,也即与诗有关。
西哲史上有此一说: 迄今为止的全部西方思想学说,都无非是对柏拉图永恒真理或永恒价值说的一次次回应。柏拉图是西哲系统的开端,整个西方思想的发展始终绕不开柏拉图这份遗产。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同样也无法绕过包容所有写作向度于一体的“史诗”这宗巨大的遗产。作为一种特定的诗体,“史诗”自然早已随同孕育了它的原始初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作为一种写作的精神性基因,它却有着生命永在的一面。至少,对90年代中国诗人而言,在应对空前的现实压力之时,他们并未陷入孤立无助的苦厄之境,因为至少还有“史诗”这一包容众多向度的写作精神,这份巨大的遗产,可供他们依循。
1999年5—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