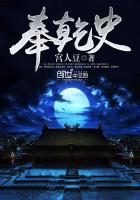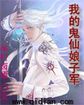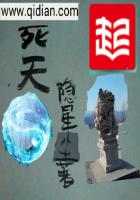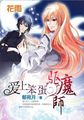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最搞笑的甚至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使用汉字而非拼音文字。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去研究拼音方案,搞出了好几十种,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改进兵器。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但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那些搞拼音方案的,甚至认为只要用拼音,轮船就能比国外造的高,枪炮就能比国外打的准。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7、康梁式的“改革派”
主流的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当年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远离他所说的康梁“小人”。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几乎材料都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研究戊戌变法的严肃的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大量的论述。
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中央的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这两人尤其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
在海外,康梁和孙中山是完全竞争关系。国民党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也是一厢情愿,康有为他们眼中这样的“反革命”筹钱也是靠华侨,那岂不成了华侨也是“反革命”之母?华侨固然是爱国的,但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整天忙于三刀(菜刀、剃刀、剪刀),讨生活。
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那就要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整天在那里拜,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入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吗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当了教主后就成了富豪,走到哪里都换一个二奶,而且还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强娶了一个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爱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8、革命帮会
同盟会在海外,首要目的也还是筹粮筹款、维持日常营运,时机成熟了,才雇佣些帮会人员回国搞点恐怖行动。这是我们之前对这类“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蔑视和批判。
帮会出身的革命者的确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怎么有效怎么整,怎么快捷怎么整,充分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李鸿章曾动用过孙文去暗杀康有为,酬金是10万两,孙文答应了,当然,最后没行动。
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天,李鸿章派广东赌王刘学洵去香港海面去接人,接谁,接孙中山。他们两约定在广东举行秘密会谈。孙中山的想法是鼓动李鸿章做大总统,两广独立。这一年,同盟会在日本人的大力扶持下,举行惠州起义,策应日军登陆并占领厦门。但日本内部局势变了,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重新出任首相。伊藤博文是个稳健派,他严令日军从厦门退出、不得支持中国的反叛势力,并且将孙文从台湾驱逐。断了日援,惠州起义就失败了。孙文派人到上海去找刘学询,让他出资,孙文在亲笔信里说:请大哥捐点钱,作为回报,你来坐江山,可以直接称为大皇帝。
这是记载在国民党的正规党史里的,他们解释说,这是伟大的总理的革命策略,蒙赌王一下,蒙点钱出来。但后人看到的,的确是革命者要拥立一个大皇帝的海誓山盟。
9、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保皇党、同盟会或许真有些理想,只是选择了帮会道路和痞子手段。但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中央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速成的、赚外汇的野鸡学校,。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剑、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几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几乎都成了建设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最后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当年如果洪秀全家里有点钱,给他捐个官,或许历史也会不同了。
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中央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10、审视自我
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开放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踩在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去,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的折腾,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流行宪政我们就拼命喊宪政,共和又时髦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做坐导者的位置,我做了是不是比他做的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谁坐金銮殿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但前提是,不能总想着我来当老大,而且要把前老大给灭了。以革命的思维推行理想,在推翻上一个狼人的同时,它的基因就会潜入你的身体,你就成了下一个狼人。
中国有种受害者万能的情结,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受害放大,同时将自己对他人的加害缩小。文革结束后,似乎只有巴金一个人在说:我要忏悔!其他人都推说是受了万恶的XXX的蒙蔽、裹挟等,似乎自己还是天使。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继续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