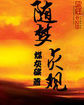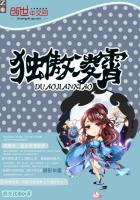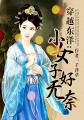在财政制度上,宋代吸取唐五代节度使拥有财权,造成与中央分庭抗礼的经济实力的教训,在路一级设转运司,通过它将州郡财赋集中到中央,以消除形成地方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在明代,以户部统领全国财赋,下设“十三司,各掌其分省之事,兼领所分两京、直隶贡赋,及诸司、卫所禄俸,边镇粮饷,并各仓场盐课、钞关”,府县几无财权,这种做法也是直接继承宋制而来。
在司法制度上,宋代收了州郡的司法权,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皆需通过路一级的提刑司复核,死刑疑案更需向朝廷奏裁,才得以判决执行。明清司法,大致亦类此。
此外,在对待权臣、宗室、外戚以及宦官等近习势力的弄权和可能威胁到皇权这一重大问题上,宋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大都为明清两代所继承。
宋代所以重要,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是又一个突出的方面。在当时,无论是各类学校的增加,书籍的广泛流布,文学艺术的繁荣,学术思想的活跃,科学技术的进步,或是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等诸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宋学的产生,像一朵奇葩,散发出夺目的光彩。这一切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着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复必振。”作为一部政治史,虽然不可能对宋代文化有过多的涉及,但是文化与政治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宋代史时,不能忽略宋文化与唐文化的不同及它对政治生活所产生的诸多影响。
宋代政治,不仅是官僚政治,而且是文人政治,是在君主独裁体制下文人掌权的政治。虽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其言行就是法律的一部分,但他们不能为所欲为,其行动多少受到儒家君主观的束缚。在先后出现辽、金、蒙元的严重威胁面前,也迫使他们的任性和腐败有所收敛,一旦收敛不住,最后必致亡国无疑。与此同时,在宋代政治生活中,我们可以不时地看到士大夫(包括一般知识分子)的身影,他们或在埋头读书,或在赋诗吟唱,或在传道解惑,或在参加科举,或在着书立说,或在履官行政,特别是连篇累牍的章奏递进,对和战问题的慷慨陈辞,对君主的规劝谏议,对官员腐败的揭发抨击,因政见或利益不同而相互间论辩争斗,以及在地域社会中的各种活动,更是充斥于国史、实录、文集、野史、方志、笔记等各类史籍的记载之中。自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年间,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有像宋代知识分子那样的.所欲言,那样的关心政治,那样的对国家、对民族抱有认同感,这就是文人政治的充分表现。
文人政治,也就是所谓“文人掌权”的政治,或者说是帝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其产生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从赵宋统治者来说,尤其是太祖兄弟及其子孙,皆为好文之君,他们充分认识到读书人在治理国家方面所起的作用,重用他们相对来说也比较安全。宋太祖有言:“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就是他对知识分子认识的真情表白。重用士人,更是为了力矫唐末五代武人政治之失,以文臣驭武将,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宋代主管军政的枢密使基本上由文臣担任,对文臣采取不杀少辱的方针,原因都在于此。从士人方面来说,随着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官僚政治的最终形成,他们的命运已与赵宋政权完全结合在一起。在唐代,门阀势力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一些世家大族即使没有皇权保障,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一样可以延续下去。恩荫得官者升迁迅速,官至宰执大臣者时有所闻,还出现了不少恩荫世家。士人一旦成为品官,不仅领有俸禄,而且还可享有六十顷至二顷不等的永业田。官员致仕或挂冠而去,依然可以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至宋代则不然,士族门阀已退出历史舞台,恩荫授官虽众,但所授多为选人小官,升迁起来困难重重,要通过恩荫世代保持特权已不可能。宋代官员的俸禄,除宰执大臣外,并非十分优厚,又无永业田可授,他们一旦失去官职,就会有生计之虞。南宋人周煇《清波杂志》卷一一《常产》条载:“煇顷侍钜公,语及常产。
公云:‘人生不可无田,有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有田方为福,盖福字从田、从衣。’虽得此说,三十年竟无尺土归耕,老而衣食不足。福基浅薄,不亦宜乎。”周煇生于靖康元年(1126)十二月,钜公者周煇之父邦,他以恩荫得官,入仕三十年,竟不能获得“尺土”。可见,在宋代,官僚并非一定能成为地主,读书人只有走科举入仕之路,才有前途可言,否则难保不陷入贫困。因而,他们自始至终离不开皇权的恩庇。再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一贯遵循“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重文政策的推行,更加增强了他们对赵宋政权的忠心,这就是为什么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名训,像“公事如家事,官物如己物”的官箴,像“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或出于宋代士大夫之口,或受到宋代士大夫推崇的原因。
赵宋统治者所施行的怀柔政策已达到了绝高的水平,他们对敌国施以怀柔(常以岁币换取和平),对农民起义施以怀柔(剿抚并用,招安为上),对士大夫同样施以怀柔(笼络以为我所用)。故文人政治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怀柔政治。从表面上看,宋代皇帝、宰相的权力都受到制衡,有所谓“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一说,实际上,士大夫所掌之权,全受皇权的严格限制,只允许他们在“铁笼子里施展拳脚”。以言官来说,看似有“风闻言事”的权力,甚至可以对帝王提出严厉批评,但基本上是为了监督和揭发各种危害皇权的事情,完全是帝王意志的体现。如果言官稍有不顺,或直接触犯到帝王的切身利益,轻则弹章会“留中不出”,重则将被撤职罢官,所谓的言事权也就迅即化为乌有。即使像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样的权臣,他们的专横跋扈也只能在皇帝的首肯下行事,在皇帝面前一样要俯首听命,不敢有半点怠慢。《朱子语类》说:“秦太师死,高宗告杨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这条记事,既不见于正史,又与高宗朝实际政治情况不合,作为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中兴”之君,岂会在武臣面前将自己说得如此懦弱!难怪朱熹也疑惑地反问:“但到这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这种道听途说的程度,几与“泥马渡康王”一样不可相信。
赵宋统治者倚重士大夫,很有点“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样子,但实际上对他们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除利用言官加以监督外,其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防官员结成“朋党”。宋真宗曾说:“唐朝朋党甚盛,以至王室卑弱。”故而宋代皇帝对官员结“朋党”一直很忌讳,凡是大臣被指斥为朋党者,不是撤职罢官,就是赶出朝廷,决不姑息,台谏官也以监察臣僚结成朋党与否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加之宋代帝王亲自掌握了取士大权,知贡举失去昔日的权力,使科举朋党也难以形成。时人所谓因“煕宁变法”而出现的“旧党与新党”、“元佑党人”和南宋宁宗朝出现的“庆元党争”之类中的“党”,虽然不无个人利益方面的考量,但多数是由于政治观点的异同,对和战看法的异同,学术观点的异同而形成的派别,这就是宋人所谓的“君子之党”和“小人之党”。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党”,而是故意给对立面扣上去的政治帽子,以便引起帝王的猜疑和不满。因而,宋代并没有类似于唐代中后期那样甚至帝王也难以控制的朋党,也决不允许出现这种朋党。若言朝廷中的派性,当然很不少,但这与结成朋党既有程度上的不同,也有性质上的差异。二是实施“异论相搅”。也就是在宰执大臣之间不能只有一种声音、一股势力,而是要适当扶植对立面,以使他们的权力互相监督,互相牵制,及时揭发对方的“不轨之行”,以便自己可以“垂拱而治”。天禧元年(1017),宋真宗拜王钦若为宰相,两年后,又用与王钦若严重不和的寇准为相,“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此即为“经典”一例。从此以后,“异论相搅”便成了赵宋王朝的祖宗家法,并为历代统治者所继承。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政治手腕,是造成连绵不断的所谓“党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宰执大臣权力不专,他们动辄遭到牵制和弹劾,即使才能出众者,也难以有所作为。于是,朝廷里苟且之风大盛,多数时候是暮气沉沉,偶有慷慨激昂的争论,多是空话连篇的说教,到头来于政治一无所补;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体制得到强化,无论宗室、外戚、宦官、权臣,乃至农民起义,都不能对赵宋王朝构成威胁(外族入侵是例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的安定,即使暗弱之帝,也不足以影响他的统治。
这当是赵宋政权所以能“长治久安”在政治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以上说的是中央政治,至于地方政治,则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胥吏世界”,二是士绅社会。所谓胥吏世界,就是“吏强官弱”之谓。宋人以为:“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财用不给罢者,吏未尝过而问也;官有以刑名而罢者,吏未尝过而问也。官有罪,吏言之,有司治之惟恐后;吏有罪,官按之,则相疑曰:‘岂宽纵致然耶?’故任职者,官以不案吏为得计。宜其所在奸吏专权擅势,大作威福。”这种情况,又因官员频繁调动,视官舍为传舍,不恤地方政事,由科举和恩荫出身的官员不能胜任州县繁杂的事务,事事依赖胥吏而变得更加严重。胥吏世界的出现,是造成州郡地方政治黑暗腐败、百姓赋税负担更加沉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士绅社会,是指宋代通过扩大科举取士,培养了一大批及第或不及第的士人,在地方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孝宗淳煕年间(1174-1189),“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建宁府亦不下万余人”。理宗景定年间(1260-1264),严州(浙江建德)每次参加发解试的士子也有七千余人。在上述参加发解试的人中,最后能考取进士的不过十几人,绝大多数士人留在乡间,与赋闲在那里的官员一起,构成了相当庞大的士绅集团,他们以从事进士业的地位和文化优势,往往扮演了地方领袖的角色。在这些人中,固然不乏为富不仁者和“哗鬼讼师”,但也有许多人热心于学校教育、兴修水利、防灾抗灾、救荒赈济和社会治安等诸多方面的地方事务,起到了各级地方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由于所受教育和利害关系,士绅们在政治上与朝廷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成了赵宋王朝在地方上的重要支柱。士绅社会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胥吏世界”的危害性,巩固了赵宋政权对地方的统治。
《景定严州续志》卷三《贡举》,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本。
总之,宋朝政治体制的巩固,并不是单纯依靠专制和暴力所得,而是通过对各种政治力量的监督和平衡,使其形成了一种互相制约的机制,即使有权臣擅权,其势力也不足以动摇皇权;通过集中兵权,以及用文人驱武将之法,有力地防止了武人势力的崛起;通过重用和优待士大夫,使士大夫们在莅官行政、着书立说中将维护赵宋皇朝看成是人生天经地义的大事,其影响所及,直到普通的庶民百姓。以上三个方面,使得赵宋政权在内固方面几乎达到了臻于完善的地步,如果没有外来军事势力的入侵,其国祚将会更加绵长。
但是,宋朝还是灭亡了。北宋灭亡于金人,南宋灭亡于蒙元,究其原因,女真、蒙古军事力量的空前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外因,而两宋政治上的腐败、军事力量的弱小却是一个重要的内因。内因的产生,又与实现内固所采取的那些政治措施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上却完全符合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