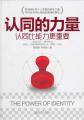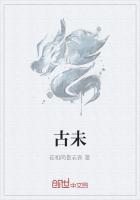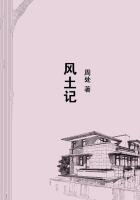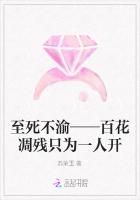蒋福亚在《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一书中说,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沙、豫章(今江西南昌)、夏口(今湖北武汉)、浔阳(今江西九江)等地都可称作一方都会,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都有发展。以豫章为例,《隋书·地理志》说:“豫章之俗,颇同吴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衣冠之人,多有数妇,暴面市廛,竞分铢以给其夫。”而永嘉(今浙江温州)等地,“其俗又颇同豫章”。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都已可观,妇女还大都是从事小商贩的能手。
至北宋沦亡,宋室南迁,温州一时成为南宋临时的首都,后来虽然定都杭州,但温州作为地近中央的陪都,得以迅速发展。而在宋代,商业发展的成就非常引人注目。千余年来对商业经营的诸多限制在宋代被取消,商业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机会。宋以后的元、明、清三代,商业进一步发展,但只是沿着宋代的轨迹继续扩展其规模。(鲁亦冬,1994)在宋代温州因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大批工农业产品投入市场,商业交换随之频繁起来。温州作为浙南城乡货物的集散地,商业呈现一派繁荣富饶的景象。北宋时,温州的商业发展已具规模。其时,乡村中的集镇已相继兴起,城市中夜市已经出现,原来的坊市旧制也开始崩溃。宋室南渡后,北方人口大批南下,店铺林立,商业更趋繁荣,温州遂成为浙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20世纪80年代,温州一度贫穷。“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当年,此类层出不穷的民间歌谣,传递出的都是温州人一穷二白的无奈。
1957年,温州工农业总产值仅7.6亿元。从1957年到1976年,温州市工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仅1.98%。而人口猛增的现实使穷得没有办法的温州人,开始被迫到外地谋生。
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温州人就跑到中国的角角落落,钉皮鞋、裁衣服、理发、开饭店、卖小商品等,形成了千家万户搞经济、跑市场的局面。
温州人创业意识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温州人通常能够通过敏锐的市场感应力比别人早一步发现商业机会。例如,早在美伊战云密布的时刻,各地各界都在关心、预测“美伊战争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批新买了汽车的“小康”人家在为油价上调不时发出抱怨,而温州人的眼前却出现了商机,在最没希望的“盲点”上,魔术般地看出了新的商业利润的“生长点”。一批温州商人纷纷冒险奔赴中东,特别是伊拉克周边的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土耳其等国,为抢占商机提前布点。2002年整个温州对中东地区的出口贸易额达2.3亿美元,这些商品主要出口到伊拉克的周边地区。温州仅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出口贸易量就达到1.5亿多美元,为温州市对外贸易的第五大市场。
温州人创业意识的背后,是一种温州精神在起作用。郑元豹创建人民电器集团就是典型的一例。凭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从一个渔民变成着名企业家。现在,他所领导的人民电器集团旗下拥有12家全资子公司、85家控股成员企业、800多家加工协作企业以及1800多家销售公司,集团总资产达50.99亿元,名列世界机械企业500强。2006年,经世界品牌实验室测评,“人民”品牌已成为中国500家最具价值品牌之一,价值达41.25亿元。
1958年3月,郑元豹出生在温州乐清柳市镇。由于家境贫困交不起学费,他在15岁时辍学了。他选择的第一份谋生职业是打鱼,每天与惊涛骇浪搏斗,获取的收获是每天五毛钱。到17岁,他选择了第二份职业——打铁。
不久后,郑元豹又先后从师孙中山的保镖刘百川父子和温州名师金得福练武,天天打拳。在名师指点下,郑元豹的武功十分了得,不久就声名远播。他在温州乐清柳市一边开铁铺,为当地人加工农具和五金产品,一边创办武馆,招收学员。
到1976年,他通过熟人引见,承包了杭州飞鹰机电控制厂,开始了小作坊式的生产。据了解,在1979年,乐清柳市涌现出2000多家低压电器厂,在全国推销低压电器产品的温州商贩数以万计。一番顽强地拼搏,小企业生存并发展起来。此后,郑元豹奋斗的脚步加快了。1982年,他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南汇机电设备厂;1986年,又在温州创建了乐清东海五金厂。1988年5月,又与友人合作,投资3万元接管只有12个人的“乐清人民低压电器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乐清人民低压电器厂”就是“人民电器”这个大品牌的前身。
当时这家企业规模很小,年产值只有10多万元。
1992年,他与总经理叶玉森一起果断地买下了乐清人民低压电器厂51%的股份。在他的倡议下,人民低压电器厂从地处一隅的温州乐清黄华搬迁到范利祥:《温州商人欲抢伊战后重建商机,秘密酝酿集体动作》,《中国经营报》2003年04月09日。
乐清柳市,并兴建了占地2700平方米的办公大楼,购买了中国电器城4~6层大楼作为生产场所,还在黄金地段设置了多家产品经营部。从1976年到1992年,从开始接触低压电器这一领域,到最终形成一个较具规模的企业,郑元豹用了整整16年时间。
1995年,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吞并了66家企业,并于1996年组建成立浙江人民电器集团,当年实现产值1.8亿元。1999年,一举整合了34家国有、集体企业,以后,陆续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投资、兼并。目前,中国人民电器集团产业横跨能源、城市化建设、现代物流、造船业、商贸以及进出口贸易、投资、电子信息技术等多元领域。
三、迁移性与闯荡个性
温州海洋文化具有迁移性与牟利性特征。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
温州人的经商意识与海洋文化关系密切。温州人以海为生,当不离渔业与经商。《越绝书·吴内传》有一则记载很有价值:“越人……方舟航买仪尘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须虑者,越人谓船为须虑。……习之于夷,夷,海也。宿之于菜,菜,野也。致之于单,单者,堵也。”这本书原只是考证越方言,却透露出在西周之前,瓯越人便进行“方舟航买”的经商活动了。他们善于造船“治须虑”,习惯于在近海远航,天黑了就在海岸住宿,到了码头就是终点。“单”,为堵,堵其实就是“堵水台”,即人工垒筑的水码头。(胡太玉,2002)据历史记载,吴越国的海外贸易一直就比较发达。当时来往于中日之间的船舶都是吴越商船,仅据日本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从900年至959年的半个世纪中,往返于双方之间的海上航行就达26次之多,几乎两年一次。吴越与日本的官方公文与礼品馈赠往来,都是由吴越航海商人转递的。高丽和大食的航海贸易商也出入于明州、杭州等吴越港口,将香料、珍犀以及“得之于海南大食国”的猛火油,源源不断地输入江浙之域。据《宋史·吴越传》记载,自乾德元年(963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十五年间,吴越进贡给北宋王朝的南海舶来品,就有香料17万斤、乳香8万斤、苏木1万斤、犀角象牙近500株、玳瑁玉石器具不计其数,则其自己留用的海外输入商货,数量还更多。
北宋时海外贸易迅速扩展,规模远远超过前代。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北宋时期,温州与境内青龙镇港已有海上贸易往来。鸦片战争前,温州为南洋航线上与上海往来的商埠之一,每年有数百只木帆船(主要为宁波船)往来于申瓯线,运载南北土产百货。清光绪二年(1876年),温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
地理环境与航海事业的发展,为温州人提供了漂洋过海的方便,一些温州商人随商船去国外经商,有的则客居在那里经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温州人纷纷漂洋过海到日本、东南亚、欧洲诸国经商谋生,到新中国成立前有华侨3.8万人。温州750万人口中在外经商办企业的就有200万人,其中在海外谋发展的有50万人。在外闯荡的温州人将“温州”这个词无限扩大,并不断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文化价值内涵和新的精神要素。
温州人的出国之梦从来没有中断过。据《南方周末》报道,温州人在美国有9.5万;温州人在欧洲,法国10万、意大利8万、荷兰3.5万、西班牙1.5万、德国0.5万、奥地利0.5万、比利时0.3万、葡萄牙0.5万、北欧(丹麦、挪威、瑞典)0.5万、匈牙利等东欧国家1.5万;在新加坡有1.5万;在巴西等南美洲国家有0.5万。
温州人四处迁徙,把店铺开到全世界各地。在巴黎市区或罗马火车站出口,成百上千家店铺绵延数十里,驻扎着清一色的温州兵团。仅巴黎地区,温州移民的数字就是15万。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纽约法拉盛人气最旺的超市,老板几乎是清一色的温州人。目前在美国约有24万温州人,他们以经营小商品、开餐馆等行业起家,投资领域已涉及贸易、房地产开发、服装制造及销售。
温州商人具有超凡的商业头脑。在温州人眼里,无论各行各业,只要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就有钱赚,关键在于你如何去发现与赚取。《南方周末》撰文说,强烈的赚钱欲望可能是温州人成功的第一要素。没有一个温州人试图掩饰他们血液里始终兴奋着的发财欲望。然而,光有头脑与欲望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坚韧不拔的精神才是温州精神的本质。
李建新是1980年代初来法的温州人之一,那时温州人几乎要借钱买机票的境况,注定了他们无一例外地要从皮包厂和餐馆的苦工做起。
他刚到巴黎时,有整整5年的时间没见过太阳,早晨天没亮开始做工,晚上上了法语课以后还要做工。他至今都记得那个场景:夜里12点多了,他拎着饭盒收工回家,常常与其他同乡在街头碰到,大家只是疲惫地互相点点头,然后擦肩而过。
起初他们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带,别人卖15块,温州人卖12块。“中国犹太人”以吃尽天下苦的不二法则吓退了犹太人,成功挤进巴黎市场。这种温州精神恰恰是温州模式孕育与发展的动力,是温州人成功的秘诀。
参考文献
1.唐长孺.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
2.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江西泰和农村宗族形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3.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席龙飞编.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曲金良.海洋文化与社会.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
6.周群.刘基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7.费君清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越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胡太玉:温州商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9.鲁亦冬:百卷本中国全史,第11卷,中国宋辽金夏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陈桥驿.史前漂流太平洋的越人.文化交流,1996(22)
11.何灿浩.吴越国方镇体制的解体与集权政治.历史研究,2004(3)
12.刘宗贤.近现代中国儒学地位与社会转型的思考.东方论坛,2005(7)
13.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3(5)
14.陈乃刚.海洋文化与岭南文化随笔.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5(4)
15.张明富.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1(1)
16.蔡克骄.温州人文精神剖析.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9(2)
17.张苗荧.温州文化双重品格对温州模式的影响.商业时代,2003(13)
18.张苗荧.温州文化的消极因素及其对温州模式的影响.华东经济管理,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