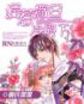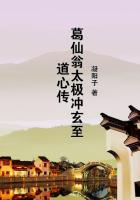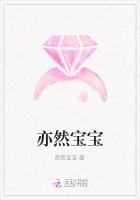第二条铁道出现在江南。时间是光绪二年(1876年),空间则由吴淞口到上海,修建者是怡和洋行(英商)。铁路全长14.5公里,单线,轨距0.762米,钢轨每米重13公斤,机车仅重15吨,牵引小型客车,时速24-33公里。目的很明确:商用赢利。
似乎是得益于长期与洋人共处,这一次的铁路建筑及火车通车,在当地并未引发如京师民众的惊骇性骚动。但是,在官府看来,这是公然践踏大清国的内政完整性。英商当然也知道在大清国是不允许外国人修铁路的,所以修建时才以修筑马路为名掩盖。明知故犯,罪加一等。
可洋人在中国横惯了,如何收场,颇费踌躇。一时从中央到地方,众说纷纭。可说来说去,横竖不出一个“买”字。先花钱买下来,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那么,究竟如何处理呢?
李鸿章算是大清国较早意识到铁路重要性的高级官员。在沈葆桢不敢,左宗棠反对的时代,李鸿章就对铁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事实上,早在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就曾写信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弈欣,“极陈铁路利益”,并请先建清江至京师的干线,“以便南北转载运输”。恭王的回复读来却令人心寒:“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此事”,“两宫太后也不能定此等大计”。从事后的发展看,恭王说的真是一点没错。但李鸿章建铁路的想法却并未就此消沉。
这一次,他大胆地主张交由华商集股经营。结果又是一场官僚集团内部彗星撞地球般的大吵大闹。最终的决定是由总理衙门与英商交涉,以28.5万两银子买下,然后将铁轨、火车一律拆毁。拆毁之后,用轮船载到遥远的台湾,往太平洋里一沉了事。
李鸿章也只有摇头叹息。
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老部下丁日昌出任福建巡抚。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丁以新官上任的魄力,上书中央,奏请在台湾试建铁路,以安内攘外。对此,李鸿章、沈葆桢达成共识,予以大力支持。又由于台湾地处偏远地区,保守势力的反对也不像以往那样激烈。中央遂顺水推舟,于第二年批准了丁日昌的建议。但话好说,钱难筹。户部困难,地方也不容易。台湾改革,百废待兴,处处要钱,丁日昌再厉害,终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李鸿章却已等不及了。
在李鸿章看来,北方的俄罗斯,东方的日本,无不是大清国的永远大患。而自强运动搞了这么多年,陆防、海防还是一无是处。不修铁路,自强终无转机。
于是,李鸿章在光绪三年(1877年)采取了行动。他对外宣传是建一条“快速马路”,实际是建起了大清国自己的第一条铁路。起点是唐山,终点是胥各庄(今丰南县)。直接目的是运输开滦煤矿的煤炭,解决运输问题,降低成本。长远看,这个看似平淡的筑路计划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李鸿章的一个宏大构想。即以此投石问路:如果波澜不大,那就加快步伐,将这条运煤铁路兵分两路,分别向山海关与天津扩展,先固京师根本,再一步步向外发展成经略八表的战略铁路网。
看上去很美,干起来却是难上加难。
因为伊犁问题,大清国和俄罗斯的边境矛盾骤然升温。光绪五年(1879)冬,发生了俄国铁甲舰来华示威的大事。一时京师振恐,朝野大惊。光绪六年(1880),太后特召淮军宿将刘铭传入京陛见,共议自强大计。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西乡大潜山人,算是李合肥的一个小老乡。因脸上有麻子而被称为刘麻子。刘麻子年少时正赶上太平天国战争,淮上一带呈现出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地带。地方豪强乘机崛起,纷纷打着“保家为乡”的旗号,组建私人武装。或乘机割地称雄,或夹在清军和太平军之间做墙头草。“少有大志”的刘铭传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自然无心于科考,而也欣欣然的做起英雄梦来。
刘铭传十八岁那年,一个地方豪强辱了他的父亲刘惠世,铭传“追数里杀之”,一时声威远扬,也开始组建起自己的队伍。时日久长,刘麻子不甘心窝在山沟里当土大王,于是决定走出大潜山,纵横四海。当时正值太平军在安徽战场占据上风之时,据说,刘省三的本意也和当时的很多地方武装一样,是打算投太平军的,不料,刘麻子半途先遇上了正在招兵的李合肥。人生的命运,有时就决定在这转瞬之间。
此后小刘跟着李鸿章,剿发剿捻,屡立奇功,他的“铭军”也就成了李鸿章的主力部队。但由于刘个性太强,与上级同僚矛盾太多,遂于同治十年告病归乡。此次重蒙召见,既是“天心重老臣”,更是老上级李鸿章上下活动的结果。
按常理,大清国里官面文章多了,既然是铁甲舰问题,就捡清流们喜欢的“人心”、“士气”谈谈,再加点枪炮子药、铁甲战舰,不就皆大欢喜了吗?不料刘铭传不提海军,却大谈起铁路来:
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今日之多且强也。一国有事,各国环窥,而俄地横亘东、西、北,与我壤界交错,尤为心腹之忧。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又将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此时之持满不发者,以铁路未成故也。
不出十年,祸且不测。日本一弹丸国耳,师西人之长技,恃有铁路,亦遇事与我为难。舍此不图,自强恐无及矣。
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
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中国幅员辽阔,北边绵亘万里,毗连俄界;通商各海口,又与各国共之。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且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徵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方今国计绌于边防,民生困于厘卡。各国通商,争夺利权,财赋日竭,后患方殷。如有铁路,收费足以养兵,则厘卡可以酌裁,裕国便民,无逾于此。今欲乘时立办,莫如筹借洋债。中国要路有二:南路一由清江经山东,一由汉口经河南,俱达京师;北路由京师东通盛京,西达甘肃。若未能同时并举,可先修清江至京一路,与本年拟修之电线相为表里。
后来才知道,这个奏折虽以刘铭传的名义上奏,也包含了他的一些想法,但实际主笔者却是李鸿章的又一个重要智囊,从曾国藩的遗留幕府资源中吸收过来的吴汝纶。后来李鸿章去世后,就是此人主持编修了《李文忠公全集》。
这倒给西太后出了道大难题。因为西太后关心的首先是自己的权力地位,所以她要笼络好各派力量,新政派不能开罪,保守派也要维持关系,而且还要让他们互相斗,互相牵制,这样自己的地位才巩固。可是,在铁路建设这个敏感问题上,双方对立得实在是太激烈,太尖锐,稍微一表态都会削弱西太后的控制力与发起政治斗争的主动权。
于是还是老办法:事下督抚廷臣议覆。
这也算是大清国处理此类敏感问题的惯用手段了。既显得中央从谏如流,广纳博采。又变相地将皮球踢给下面。虽然失去了改革的主动权,但却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主动。
对此,大清国的官员们自然心知肚明。但李鸿章却又一次把官样文章写成了战略分析。于是才有下面的检讨。
李鸿章当然是大力支持修铁路的。在十二月初一的奏议中,他一口气说出了铁路的九个好处:
一、有利于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推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有利于全国军政的统一;
三、有利于京师的安全和经济发展;
四、灾年跨区调动物资,可以有效平衡物资,有益于“民生”;
五、有利于漕运;
七、有利于邮政;
八、有利于偏僻地区的经济发展;
九、有利于“行旅者”(交通——笔者注)。
其中二、三两条可谓与国防直接相关,也与本文的主旨相合,故不厌其烦,详引于下。
李鸿章说:“从来兵合则强,兵分则弱。中国边防、海防各万余里。若处处设备,非特无此饷力,亦且无此办法。苟有铁路以利师行,则虽滇黔甘陇之远,不过十日可达。十八省防守之旅,皆可为游击之师(即机动部队——笔者注)。
将来裁兵节饷,并成劲旅一呼可集。声势联络,一兵能抵十兵之用。此便于军政者,利二也。”
“京师为天下根本,独居中国之北,与腹地相隔辽远,控制极难,缓急莫助。咸丰庚申之变(第二次鸦片战争——笔者注),议者多请迁都,率以事体重大,未便遽行。而外人一有要挟,即愈撼我都城。若铁路即开,万里之遥,如在户庭。百万之众,克期征调。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则有警时易于救援矣。各省仕商,络绎奔赴。远方粮货,转输迅速,皆愿出于其途,藏于其市。则无事时,易于富庶矣。不必再议迁都,而外人之觊觎永绝,自有万年不拔之基。此便于京师者,利三也。”
为了唤醒沉睡的同僚,李鸿章还特别强调了日、俄两个邻国不断加深的地缘威胁。他说:“即如日本以区区小国,在其境内营造铁路,自谓师西洋长技,辄有藐视中国之心。俄自欧洲起造铁路,渐近浩罕、恰克图等处。又愈由海参崴开路以达珲春。中国与俄接壤万数千里,向使早得铁路数条,则就现有兵力,尽敷调遣。如无铁路,则虽增兵增饷,实属防不胜防。”
总之,“处今日各国皆有铁路之时,而中国独无,譬如居中古而摒弃舟车,其动辄后于人,必矣!”
至于刘铭传提出的“筹借洋债”一节,李鸿章略有意见:“而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
可保守势力的反击仍占了上风。其中刘锡鸿表现最为活跃,他以前外交人员的身份大谈据说是建立在外国实地考察基础上的铁路问题,一口气说出了整整二十五条反对意见。面对双方的激烈辩难,西太后虽然不明确表示反对李鸿章,但是沉默也就等于搁置。
既然铁路难建。刘铭传也只有再次回籍养病。李鸿章则继续等待时机。
一眨眼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唐山-胥各庄”铁路工程终于竣工。铁路全长9.7公里,采用1435毫米的轨距和每米15公斤的钢轨。但由于反对之声太强(“轮车所过之处,声闻数十里,雷轰电骇,震厉殊常,于地脉无不损伤。”
加之东陵就在附近,火车的噪音被认为是对先帝们的不敬),李鸿章也只好作出一个迫不得已的妥协:“铺轨,但不设机车,以骡马拉煤车。”
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事情才又有了转机。这一年,李鸿章给西太后和光绪帝修成了一条全世界罕见的袖珍版宫廷铁路。
这条由法国承包商负责的法式窄轨轻便铁路,南起中南海紫光阁,经时应宫穿越福华门(即今中南海北门),再经北海阳泽门(即今北海西南门)沿北海西岸北行,至极乐世界转向东,又从龙泽亭转向北,经阐福寺、浴兰轩、大西天抵达镜清斋(现名静心斋)前的码头坞。全长1510.4米。在北海小西天东南角亭和五龙亭的滋香亭之间,还专门架设了一段铁路桥。
在这段铁路上行驶的是一列做工精良、陈设华美的特制轻便小火车。这列小火车包括了六节乘客车厢(上等豪华车厢一节,上等普通车厢两节,中等车厢两节,行李车厢一节),一台火车头,“陈设华美,制作精良,器具材质光洁,对面坐两列,容二十八人”。真可谓小巧玲珑,巧夺天工。
造了这么一个既美观又耐用的珍品,总该卖个好价钱。可是,法国人一共只给李鸿章要了6000银元,而且是包括铁轨在内的要价。这个钱,连从法国到中国的运费都不够。之所以做这个近乎全额赞助的折本买卖,全在于法国人想借此机会做一个大广告,为他们日后承办中国的铁路工程预设伏笔。结果才让李鸿章捡了个大便宜。
工程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开始动工,光绪十四年(1888年)竣工。
西太后坐上去转了一圈后,表示感觉不错。
这就是李鸿章需要的东西——改革的信号。其实,早在西太后批准建设这条铁路时,信号就已经放射出来了。现在,信号的强度达到了波峰。
五个月后,清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兴办铁路的正式文件,内称:“(铁路)为自强要策,必应通筹天下全局……但冀有益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
那么,又是什么让西太后在五年内改变了对铁路的态度呢?何以在五年前还不敢公开表态的她,这个时候却先是默许在宫内修铁路,然后又亲自乘坐,甚至终于表示公开支持了呢?
说来让人叹息,原来大清国又在新一轮国际较量中吃了大亏。痛定思痛,也才有了这么一点改变。
其实,早在慈禧之前,就有一个人先行作了一个急转弯式的转变。这个人就是光绪帝的生父,时任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和海军衙门总办的醇亲王奕譞。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春,他忽然一改其保守立场,深刻反思自己以往“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复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铁路实为目下中国应行举办之务。”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建言,清廷才同意延展唐胥铁路,同时批准将原先的开平铁路公司易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慈禧也才能够在一年后波澜不惊地批准西苑铁路的建设。
而促成这些转变的正是醇亲王提到的那场“前岁战事”:中法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