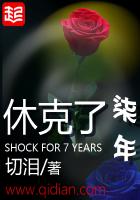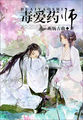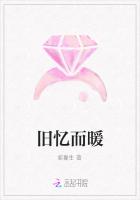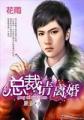竹添接书后,不置可否。清军久等无回音,遂会同亲华的韩军左右营入宫,但旋即遭到乱党射击,激战随之展开,枪声一响,王宫大乱。混战中,竹添与乱党头目忽然震惊地发现,韩王不见了!这可真是个致命失误。竹添深知大势已去,遂喊上乱党中坚撤退。不料洪英植却执意要去找韩王,竹添争执不过,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洪英植飞奔的身影消失在弥漫的浓烟中。
混乱中,洪英植左转右找,还真就在玉流泉北面的关帝庙,找到了避乱的韩王。他箭步上前,拽住韩王的手,强迫韩王随他去追竹添。韩王执意哪都不去。
双方正争执不下,清朝联军已杀奔进来,洪英植就这样成了乱刀下的肉泥。一听说找到了毫发无损的韩王,吴、袁二人大喜过望。非常时刻,谁也不敢保证宫中没有乱党潜伏。所以二人当即决定,请韩王陛下屈尊暂离皇宫,先到趟清军大营暂住。
就这样,清军带着韩王,一路凯旋回营。同时,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则随竹添逃往日本。战乱一起,朝鲜军民自发攻击日军,结果,日本使馆二次被烧(一说为竹添撤退前自行烧毁,以敲诈朝鲜),日侨30余人被杀。消息传出,吴兆有与袁世凯深感事态严重,遂于二十日急电北洋请援,同时送上韩王发给李鸿章的乞援国书。于是也才有了前文中超勇、扬威停止南下,转发朝鲜的一幕。
中方的迅速反应,再次及时克制了动乱的扩大。日本内部和战难决,遂先派出全权谈判大臣井上馨带兵船三艘,载兵两千余人赴朝,先绕开中国压迫朝鲜。
十一月十六日(1月9日),井上馨一行抵达仁川港。十七日入汉城,形势再度紧张。经谈判,日朝双方于二十四日签署了《日韩汉城条约》。该条约规定:
一、朝鲜国修国书向日本道歉;
二、朝鲜赔偿日本11万元善后金;
三、捕捉杀害日本驻韩教官矶林大尉的凶手,“从重正典刑”;
四、日本使馆另迁新址,地基由朝方无偿提供,并支付2万元工程费。
五、日本继续保有朝鲜驻兵保护使馆侨民的权力,并规定“公使馆所附属土地,为日本护卫兵队之营舍”。
日韩纠纷至此告一段落,但如果中日不能达成公识,甲申事变还是不可能真正解决。在东京,激烈的争论已经爆发。一批文武大员力主乘此机会向中方作武力摊牌,乘中方南北洋两线作战,无法全力对日的时刻,一举拿下朝鲜。而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另一派则持相反意见,他们承认现在确实“有机可乘”,但更指出,归根结底,中日实力对比在根本上仍是中方占优。倘日方乘机突袭朝鲜,中国恐怕就会宁肯丧失更大利益于法国,也不会坐视日本吞并朝鲜。于是,中法议和,大清腾出手来全力与日本交战,纵然朝鲜攻得下,又如何守得住?打了半天,国家元气大伤,体面大损,得到好处反而是法国人!这样的折本生意,有什么价值?相反,若日本持和平态度,利用中法矛盾,作有限的外交争取,必可有所斩获。这就叫借力打力,也可说是借法打中。与前种行动下的替法国火中取栗正相反。而战胜中国的根本之途,还是在于自强与发展。
这一番分析,令急战派暂时沉默了下去。天皇遂命伊藤博文为全权大臣,赴华与中方协商朝鲜善后事宜。
正为中法战争焦头烂额的李鸿章,虽明知分身乏术,但中央已经决定,李负责与日本的谈判,地点就在天津,日使无需进京。李鸿章也只有勉为其难,于万难中挤出时间,和伊藤协商韩乱善后事宜。
双雄初会
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伊藤与全权副使西乡从道离开了东京。二十八日,伊藤一行抵达天津。三十日,李伊第一次见面。伊藤首先进京呈递了国书,然后便于二月十七日返回天津,并于第二天与李展开正式谈判。
谈判从二月十八日开始,直至三月初一始结束。会商的结果,就是三月初四(4月18日)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该条约内容共三条:
第一条规定,中方由马山浦撤走驻韩清军,日方亦同时由仁川港撤走护卫使馆之兵弁,“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
第二条规定,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选雇他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暗藏纠纷的是最后一条。
事实上,正如前文多次提及的那样,朝鲜问题的根本解决途径就是“以退为进”。即赶在朝鲜国民觉醒之前,放弃那个不合时宜的宗藩关系,同时扶植朝鲜国内倾向中国的革新派,推行中国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如此一来,只要朝鲜不亲俄,又开放商务利益,英国就不会破坏也不会允许别人破坏东北亚的均势。这样中国就可以从众目睽睽下脱身,在“和戎”的前提下“变法”,有领土野心的日、俄则将成为众矢之的。若日、俄勾结,中国就与英国结盟。若日本坚持联英,中国就做英俄两大势力之间的制衡筹码,维持东北亚均势,静待欧洲战火燃烧,再定攻守大计。至于朝鲜,则将作为中英俄日四大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获得一个长久的和平环境,从事于内政改革。如果这个方案可以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李鸿章就可以向伊藤建议,在相互撤军的基础上,相互承诺永不出兵朝鲜。如此就短期言中国所失多,日本所失少。但就长期论,中国所得多,而日本所得少。两相抵消,大局上对中国还是有利的。
但可惜的是,这个计划从不曾被提上过议事的日程。因为太后不会同意,皇上不会同意,清流党也不会同意,就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现代外交。
当然,大清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坚持只有我方有出兵权,而日本没有,但现实中的战争,与法日同盟的潜在可能,大大动摇了大清国的底气。于是也才有了三月初一的上谕:“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
原来北京方面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
一、朝鲜绝不放弃,为宗藩关系不惜动武,所以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二、既然日本的野心是不变的,在大清强、日本弱的前提下,双方约定都可出兵,但出兵前要相互通知,这样他奈我无何,我却可以避免日本再搞突然袭击!
但很可惜,就目前讲,当然是大清强而日本弱。可发展潜力呢?十年之后呢?
同时也不应该忘记,任何约定双方都有阐释权。对于这个《天津条约》第三条,日本是另有理解。至于它是如何解释,十年之后自见分晓。
伊藤走了,李鸿章的心情却无法平静。在他密呈总理衙门内部参考的书函中,如下一段话,特别引人注意:该使(伊藤)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摹仿,实有治国之才!专注意于通商、睦邻、富民、强兵诸政,不欲轻言战事,并吞小邦。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
十年后的纪年是甲午。
幸哉,不幸哉?
沉船迷案
不管幸与不幸,朝鲜问题至此算是告一段落。它造成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北洋水师无法南下,从而形成了南洋分遣舰队的独自南下援台。而此时法国海军已做好拦截准备。
2月7日,孤拔率领“巴雅”号等7艘军舰北上搜索南洋5舰,经过5天的巡弋,仍然一无所获。2月13日清晨5时半,法国舰队正要掉头南归,却意外遭遇了南洋水师的5舰。
孤拔下令:准备战斗!
吴安康也下令:立即转舵,撤退!
5舰之中,以驭远速度最慢。其设计速度本为12节,但此时由于年老失修,只能勉强达到10节。此时吴安康一声撤退,五舰的距离也就随之拉开。
吴安康眼见驭远越来越小。澄庆说快不快,恰足以拖累二南与开济三快船;说慢又不慢,恰恰甩开驭远。吴遂命澄庆留下保护驭远,而自带其余三舰全速逃往镇海口避难。
澄庆、驭远也不傻,自然不会慢以待毙,遂掉头回驶,乘涨潮又驶入了石浦口,7艘尾追而来的法舰,由于不明水道,并未急于暂未深入,而是分作南北两队,3艘在南、4艘在北地堵住出口。同时派出陆战队控制近口小岛,架设火炮。
鱼雷舰队则试探性前出,一面探明水道,一面作出偷袭的准备,以对华军形成强大的威慑。然后,法军就开始等待,等待“两只老鼠”的投降或灭亡。果然,就在这天晚上,法军终于听到了两声期待已久的巨响。可那却并非法军鱼雷艇的功劳。
原来,自看到追击而来的法舰的那一刻起,陆上的居民们就炸开了锅。他们集体抵制两舰的停留,以避免本地遭受战火的蹂躏。同样的观念也存在于石浦岸防守军的心中。海军别无选择。
那一刻,澄庆舰的管带蒋超英沉默,驭远舰的管带金荣也沉默。
沉默的结果,就是两声巨响:自沉。而时间则定在了万家欢庆的除夕之夜。
但命运总是出人意料。就在两舰已决定自毁的2月14日夜十一时半,法国的两艘鱼雷汽艇偷偷潜入了港中。为了这次偷袭,法国人可谓煞费苦心。他们特意选择了除夕夜采取行动,行动时又将鱼雷艇漆成黑色,并遮住发光的仪表。但很快他们就会发现,这一次他们可算是白忙活了。法军的第一轮鱼雷攻击,成功击伤了驭远的尾部。但接下来的事情就让法国人大跌眼镜了。还没等他们发射第二轮鱼雷,受伤的“驭远”与毫发未损的“澄庆”,就在他们眼前沉了下去!
难道大清国的军舰竟有潜水功能?但很快,法国人就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正如负责指挥此次偷袭的“巴雅”舰副舰长戈尔敦中校所言:“此次夜袭任务之完成,有一部分是由中国人自己执行的。”
巴德诺也已隐约想到了一些东西:“很可能实情就是如此:澄庆号舰长想找借口逃到岸上,并想把自己船只沉没归咎于我们的鱼雷艇,遂与他的船员串通,自动把船弄沉了。”
澄庆如此,驭远何尝不是?
连老外都看透的把戏,大清国那么多聪明人会看不透?所以说纸包不住火。
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石头出来谁倒霉?当然是责任人倒霉。于是乎,圣旨一道,蒋、金二管带革职发往军台效力。
皇恩浩荡声中,至少还保全了两船水兵与一帮百姓。也算是大清国特色的人道主义了。
大崩溃
台湾海峡的封锁没能打开,越南战场又传噩耗。
十一月,雨季提前结束。中法双方同时选择了进攻。
这段时间清军方面有两件事值得一说。一为国人瞩目已久的王德榜军终于突破重重关山到了一线,二为张之洞重新启用了退休在家的老将冯子材。
冯子材的复出,很大程度上缘于当时复杂的派系斗争,即张之洞等人对淮系失望,想借重冯子材取代潘鼎新。如此一来,潘鼎新对冯子材的复出,自然充满警惕无,形中制造了不必要的麻烦。但这些都是后话了。
回头再看一线。
西线清军继续围困宣光,但很显然,如不能解决重火器问题,宣光难以攻克。但是,这些技术问题恰恰是大清国官僚系统最易于忽略的环节。张之洞从不曾进入越南半步,简单地认为意志力可以克服装备不足造成的战术难题。至于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们,更是不关心此类实际问题,整日袖手空谈,让岑毓英效法邓艾之入蜀,取道泰国老挝,间道出奇,偷袭西贡!前线诸将也只有苦笑的份。
东线清军则部署如下:苏元春所部增至18营约9000人,负责防堵船头一路法军北上;前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率12营约6000人驻扎观音桥;王德榜率10营5000人,防守那阳,警戒郎甲、船头之敌迂回谅山;王德榜的副将马盛治部6营3000人,驻扎太原之新街,俟宣光攻克后,即与西线滇军会攻太原;潘鼎新自率淮军6营3000人驻守谅山,兼作预备队以备策应各路。
十一月下旬,南下的清军与北上的法军,在丰谷、纸作社一线全面遭遇。清军原计划是以苏元春与王德榜两部分进合击,夹攻船头。不料,苏部因“新募三营粮械不齐,须暂缓十日方能拔进”,遂造成王部孤军深入的态势。十八日,作为生力军的王德榜部,在离船头30里的丰谷、梅苏一带,与法军遭遇,激战两天后,法军以85人的伤亡,毙伤清军近千人(内记名总兵黄喜光等33员将官阵亡)。王德榜被迫率军退回板峒,后又退至距那阳80里的车里。
因为时值阳历元旦前后,遂为法军称为“新年奇捷”。法政府决定,自十一月二十二日(1月7日)起,越南战事正式由海部转为陆部负责,并决意再追加1000万法郎军费,另为来春战争准备4300万法郎军费。
反观清军,攻已乏力,退则为中央不许,于是只有死守,死守最后就是守死。受制于脆弱的后勤,清军不仅动机力极差,而且被迫将各军分散就食,各把要隘,这就造成了兵力的严重分散。在对法军下一轮主攻方向的判断上,清军同样犯了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