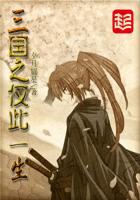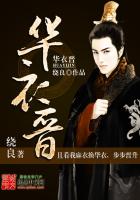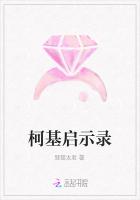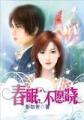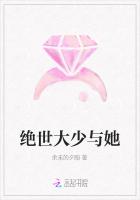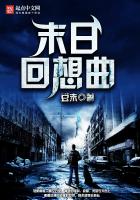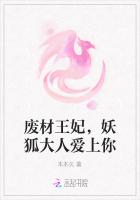李鸿章转向持久战
由于高升号的被击沉,李鸿章的南北夹击计划宣告破产。但在日军已控制汉城的情况下,北路清军却平安入驻了平壤,牙山孤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也全师而退,千里转进,得以与主力会师,最终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之局,也可谓不幸中的一大幸事。难怪盛宣怀要以手加额,庆幸:“倭兵早到大同江……平壤居然不失,诚国之福!”
但新的难题也随之产生。
困难来自于未来的战场的独特性。
中日即将展开较量的战场,从朝鲜半岛始,经辽东半岛、直隶平原,至山东半岛终,环绕渤、黄海,其东端是此战双方争夺的直接目标:朝鲜,西端是大清国的重心:京师,南北两端则分布着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与威海。
在这个战场上作战,陆军的进退与海权的消长密切相关,侧后的安全重于正面的进退。这种独特的地理特性,为中日之间的大战的展开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平台。
可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战场:交通,朝鲜长期闭关锁国,缺乏现代意识,一公里铁路也没有修筑,交通原始落后。北部多山,大军行止、物资转运,尤觉困难。
至于大清国,虽然李鸿章早在同治朝就开始呼吁修筑铁路,但受制于强大的反对势力,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偌大个大清国,用了20年的时间,一共仅修建了约400多公里铁路。其中,刘铭传在台湾修了107公里,张之洞在大冶修了28公里,其余就是李鸿章的功劳了。
而日本在1893年就已经有了2039英里铁路。出九州就是釜山,便于登陆。
从直线距离上讲,从汉城到釜山,与从汉城到平壤,均为500华里。但北部多山,气候恶劣,清国铁路向朝鲜方向只通到山海关,出了关清军就只有徒步行军开往战场。辎重转运全靠畜力。所以清军的交通困难大于日军。
相形之下,海运即快捷又高效,但在双方海军战力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开战后,双方都不敢轻易在朝鲜西海岸展开大规模海运。但日本以其地缘优势,可以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外的朝鲜东海岸登陆,更可趁机袭扰北洋沿岸各战略要点。清军却限制于作战基地和后进保障,既无法作同样的机动,又难于打击日本本土。
通讯
朝鲜有两条电报线,北线为中国修造,由仁川至汉城经平壤过义州,入中国东北,连接于北洋。南线为日本修造,由汉城至釜山,由海线通日本。表明上是平分秋色。但前述局势的发展迅速打破了双方之间微妙的平衡。由于日军先入汉城,这就等于控制了朝鲜通讯网的心脏。六月二十二日,日军攻占中国驻朝电报局,平壤以南讯息全断,牙山叶志超部彻底成为孤军。“须俟大军到平(壤),兵进一步,线通一步,方能守护”。
后勤
当时入朝清军的后勤基地有二:一为天津,一为奉天。交通线则有四条:一由大沽海运经旅顺、大孤山至大东沟;一由大沽海运至营口,再转陆路至九连城;一由天津以铁路运至山海关,再由陆路经锦州、牛庄、辽阳至九连城;一由奉天陆路至九连城。所有四条线过鸭绿江后汇为一路,经义州-宣州-定州-安州陆路至平壤。
换句话说,在朝鲜境内,平壤守军等于“只有一条陆路联络线。且其一部接近海岸,故在平(壤)(清军)诸将深感其危险。”
同样糟糕的是,中国用银,朝鲜使用本地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每两仅易制钱七百有奇”,仅相当于国内购买力的一半。“所有添营、购械、转运各费不可胜计,与内地用兵情形迥异。战事既开,利钝迟速,均难预期。而各项开支,刻难停缓。”以至于大战在即,李鸿章不仅要忙着部署军事,还要从国内运铜去朝鲜就地铸钱,以平衡物价。
上述两点合在一起,就是李鸿章的一句话,“悬师远征,道路险艰,转运之费尤巨。”
当然,清军也有清军的优势。
在这个战场上,清军最足以自豪的就是李鸿章倾25年之力,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防系统。这一系统,以(天)津(塘)沽、旅(顺)大(连)、威海三大要点为依托,守则拱卫京师门户,进则保护朝鲜,威慑日本。
所以李鸿章才说:“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急可恃,即甫经创办海军,就现有铁快各艘,助以蚊雷舰艇,与炮台相依辅。似渤海门户坚固,敌尚未敢轻窥。即不增一兵,不加一饷,臣办差可自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
当然,这两个军港也不是没有缺陷。以威海论,本来还该有第四期工程,即加强后方的对陆防御。但由于财政制肘,未能兴办。旅顺的情形也大体相仿,这样一来,两港对海防御虽然固若金汤,可陆上的后方安全却成了他们的阿克琉斯脚踵。不过,只要北洋水师在,日军不敢作两栖登陆,北洋沿海就是金汤铁城。
这个独特的战场决定了李鸿章所能选择的战略。
李鸿章的方略是,北洋水师的主要任务不是和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主力会战,而是依托北洋海防工事,作攻势防御。即战略上避战,取守势,战术上伺机巡游渤、黄海,威胁日军海上运输线。这样日军忌惮北洋水师,在取得制海权前,不敢轻易在三个半岛的侧后登陆,清军就可以逐步动员全国陆上力量,与之作正面的持久消耗。用李鸿章自己的话概括,就叫“保船制敌”。保船就是保住海上有生力量,取老子“控而不发”的智慧,威慑日军的软肋。然后将战争导入持久战的轨道。因为当时的日本经济实力有限,连年扩军,负债累累,其土货多销往中国。只要中国将经济战与军事上的持久战相结合,“檄行各(海)关,暂停日本通商,日货不准进口。”这样日本虽有快船快炮,却已无用武之地。
那么,李鸿章的这个计划对不对呢?敌人的档案记录,最有权威性。
日军计划
就在七月初五,日本大本营敲定了他们酝酿已久的“作战大方针”。
日军的作战计划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先派第五师团出朝鲜,以之牵制清军。在国内以陆海军守备要地,并作出征准备。此间,我舰队进而扫荡敌之水师,尽力取得黄海及渤海制海权。”
第二期作战则根据第一期中制海权争夺结果的不同,细分为以下三种选择:
甲方案:若能完全掌握制海权,“则逐步输送陆军主力于渤海湾,进行直隶平原大决战。”
乙方案:鉴于“清国四个水师之舰艇,其只数及吨数均凌驾于我海军”,北洋水师尚有我所没有的铁甲巨舰,故“胜败只数遽难逆料。”如我未能控制渤海湾,但敌亦不能取得我近海制海权时,“我则陆续派陆军进入朝鲜,击退敌军,以达扶植韩国独立之目的。”即主要依赖陆战争取一个有限的战争目的。
丙方案:“若我海战不利,制海权全归敌有,我则唯有尽可能援助(在朝之)第五师团”,尽可能维持朝鲜的据点,牵制清军,同时“在国内整饬防卫”,准备登陆作战。
很显然,日军利在速战。其陆战的进退又取决于海战的胜败。所以关键就在海战能否速战速决。
李鸿章的“保船制敌”虽然看似消极,却正针对日军的战略而发。
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是较早弄清李鸿章战略意图的日本人,也是较早认清其危害性的日本人。
情报传到东京,日方大为震惊。因为当时的日本经过23年的维新努力,尤其是近十年的对清备战,手中的剑已是非常锋利,无奈经济实力有限,所以日本要力争速决。要速决,首先要争得黄海的制海权。不然,因为战场地貌特殊,一切兵力输送、后勤转运、后路掩护均无从谈起,真要是让陆军从朝鲜半岛在原始的后勤线上向北京作陆路推进,必然要打成持久战。
针对李鸿章的战略,宗方小太郎建议,日方只需派军舰“突入渤海海口”,作一个武装游行,快来快走,不与交战,北洋水师自会舍弃北洋防御体系,走向大洋,到时日方便可寻机与之“一决雌雄”。这里,宗方对光绪及其背后的激进派们的心理无疑把握得很清楚。
日本海军几次入渤海湾游击,果然令清国君臣情绪失控,群臣对北洋水师交相弹劾,光绪龙颜大怒,连下严旨,逼北洋水师出战,甚至闹到要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革职拿问的地步。全靠了李鸿章的力保,才改为“戴罪自效”。
但是,让日军无奈的是,无论他们如何挑衅,也无论光绪如何连发严旨,北洋水师在李鸿章的严密掌控下,就是不给日本联合舰队主力会战的机会。而从海上,日军根本无法突破李鸿章经营二十多年的北洋海防工事。如此一旦拖到冬季到来,渤海湾就会封冻,鸭绿江两岸的气温也将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届时,日军不仅完全无法在直隶平原登陆,在朝鲜的作战也大为困难。
有鉴于此,日本大本营在七月十四日(8月14号)决定修改原定作战次序。
在没有取得制海权的情况下,增派第三师团提前入朝,与已经在汉城集结的第五师团会合,组编为第一军,由明治维新的元老山县有朋任军长,兵分三路北上,合围平壤。寄希望于陆军能在清军完成战略动员前,重创入朝清军。并争取在陆战中寻求扑捉北洋水师进行主力会战的机会。
其陆上攻击计划可以说是照搬毛奇之外线战略,可是,在朝鲜却并无铁路可供日本快速运兵。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日本利用了朝鲜半岛特殊的地形,以海运代替了铁路。在南线日军自汉城分三路北上的同时,再海运一支奇兵,由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迂回到平壤北面背击清军,完成四面合围之势。
此招可谓狠辣。在朝鲜这样一个狭长而多山的半岛战场上,海权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价值。从汉到隋唐对朝鲜的东征,再到明朝的抗日援朝,胜利者无不是能控制海洋者。甚至直到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麦克阿瑟不也还是要靠仁川登陆翻盘吗?除非守方能以绝对优势的陆军填满东西海岸,不然很难对付海权力量的两栖闪击。而朝鲜战争初期的北朝鲜军恰恰没有这个优势兵力,光绪二十年的叶志超同样没有。
日本大本营指导战争的灵活与高效,皆非大清可比。但此时的日本参谋本部毕竟还处于初创期,甲午战争是参谋本部成立后策划实施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
所以其军事行动的保密性还有很多问题。事实上,早在六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就得到了日军有在元山登陆,袭击入朝军后路的消息,但一开始他并未重视这个情报。因为大清国有太多比作战层面更高更困难的问题,等着他提意见呢。
进退两难
丰岛偷袭后,李鸿章的元老级幕僚周馥向李建议:“日本蓄谋已久矣!北洋之力,能抗彼一国耶?必筹足兵饷三年,而与之持,或稍有济。其要有四:一、勿与日本决裂。彼挑战急,我宁忍受,得和且和。二、除原有劲旅整备外,宜速募兵三万,驻直隶,精练之,以待东发,仍速招三万以为续备。三、斯役用淮军居多,两淮宿将,今惟刘省三爵抚在,宜急起用。四、水陆宜节节速筹转运,奏请重借国债应之。待四事备齐,将逾年矣。日人如必不和,则出师扼鸭绿江以待。”
为什么周馥强调“勿与日本决裂”呢?因为大清的近代化军火主要依赖外购,自光绪十七年“南北洋停购外洋枪炮船只机器”至开战,清军再未储积军火,日本却反是。一旦正式宣战,西洋列强援引中立法,大清不仅买军火难,运军火更难。只要走漏半点风声,日本人在沿途运货船停泊的任何一个港口提出外交抗议,当地政府就有权截扣军火。好不容易联系到智利愿意售舰,不幸又因日本的外交干涉而破产。军火价格更是一涨再涨,不厚积财力,是无法长期作战的。
但事实上这四件事,李鸿章一件也干不成。
首先,第一条“忍字诀”就过不了舆论和太后、皇上、帝师的关。
第二条是要用大把银子的,户部本来就闹钱荒,老太后的六十大寿又耗费无度,去哪搞钱?李鸿章在六月初四倒是曾上书中央,称如果不能再增加20到30营陆军,募集200到300两白银的军费,对日作战很难展开。虽然第二天中枢就决定由户部和海军衙门各负责筹集150万军费,可是却再没了落实的下文。
第三条又头疼,刘铭传死活不出山,李鸿章拿他什么办法?
第四条大借外债更难以获得批准。因为若前所述,太后早在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就明发懿旨:“主战”但“不准借洋债”。讽刺的是,此前为了颐和园工程大清曾多次巧立名目地借外债。总之,可以借外债修园林,不可以借外债打日本。也算是大清特色的和平主义了。
于是,周馥进一步指出:“是必败!中堂一生勋业,从此堕矣!当思曲终奏雅。”
这已等于是暗示李鸿章要么急流勇退,要么赶紧为他日的失败预留后路,但这又不符合李鸿章的性格。果然,李鸿章既没有多解释,更没有申请退休,而是继续硬撑。
七月初一(8月1日),光绪皇帝颁布对日宣战上谕。同一天,日本天皇也发布了对清国宣战诏书。
七月初四(8月4日),李鸿章开始向旅顺与山东的新募军发放北洋库存的精锐武器。全国各省水陆军亦随之进入戒备状态。
七月初五(8月5日),上谕令户部、内务府与北洋大臣速修战备,并决定将西太后六十大寿庆典的部分费用紧急挪作军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