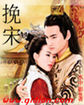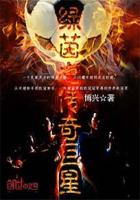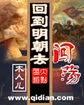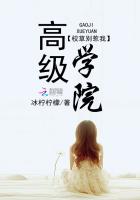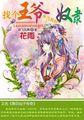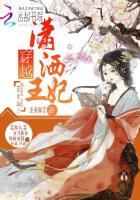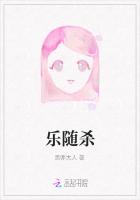一个年份,两件大事
大清国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年。在太平洋的两岸,各发生了一件注定将为一代又一代史家反复提及的大事。
在太平洋的西岸,《马关条约》尘埃落定。
在太平洋的东岸,美利坚的GDP总值第一次超越大清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前者标志着李鸿章时代的终结,更标志着中国丧失一次宝贵的现代化机遇,同时,伴随着台湾的丢失与巨额赔款,大清国成为一个地缘残疾国,日本却由小东洋初步具备了大日本帝国的形态——东北亚权力格局彻底改写。
后者则标志着全球权力转移的新趋势。
两个GDP世界第一,含金量却完全不同。大清国的GDP世界第一,是一个纯粹的量的累积,而这个量本身又大有问题。
首先,大清国是一个标准的农业文明国,它创造的财富带有严重的闭锁性,往往GDP的大部分就地产生又就地被消耗,无法集中为生产性资本,也无法转换成现代军事实力。
其次,大清国又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君主专制国。没有现代化的管理,又缺乏独立的检察机构,腐败已成为普遍现象,大量社会财富被不清不楚地消耗,而官僚系统的统计数据却多不可信。
所以,大清国的GDP世界第一,转换不出生产力的世界第一,转换不出人民生活水平的世界第一,更转换不出战斗力的世界第一。
而美国则不同。
从疆域上讲,美国与大清国不相上下。但与大清国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庞然大物。这样一来,它所聚集的财富与能量就太惊人了。想一想英吉利与低地国家,再看一看法兰西与德意志,我们就该明白,美国的崛起不同一般。第一次,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工业化大陆国。一个早在1850年就拥有了15000公里铁路,雄踞世界第一宝座的大陆国。原有的地缘格局,因之而土崩瓦解。
今天回头望去,不能不说美国是一个异数。
新霸主的崛起
诚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周边国家带来的威胁大于相距遥远的国家的威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更可能为了对付周边国家而不是相距遥远的国家而选择结成同盟。”所以欧洲列强相互制衡,东亚中英俄法日五强博弈。它们就是这样在相互制约中维持出和平。在这种体系里,“拿破仑”是所有人的公敌。
原则是一句话:绝不允许出现超级大国。
而美国是如此的幸运,它是罕有的“离岸性”(offshore)大国——远离欧亚大陆的边界。英、日离岸但太小,中、俄很大但不离岸。美国两样全有。它的两翼是大洋,北面是富而不强的加拿大,南面是弱而好战的墨西哥。所有这一切,为美国提供了这个世界上空前优越的安全性。生活在这个空间里,美国人几乎不用考虑国家安全。因为在非核时代,只有一种国家可以威胁美国,那就是同时兼备陆海双强的超级大国。但在当时,这样的国家根本没有。英国是海强,但陆军太袖珍。法德俄是陆强,可却没有将地面力量投送到北美的海洋支援。
更主要的,冷静回顾一下过去3000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主要的大国与文明几乎全分布在亚欧大陆上。而美国拜“离岸性”所赐,远离这一战场,既避免了大量战争威胁,也减少了很多威胁别人的机会。所以美国力量的壮大很少引发欧亚大陆上各强国的注意。相反,它们之间却往往因为一些风声鹤唳而剑拔弩张。最终能制衡美国的只有它的邻国,但墨西哥不能,加拿大根本不想。大家不要忘记,直到21世纪初,加拿大依然没有自已独立的国家战略。最初,它依辅于大英帝国,后来又依辅于北约,今天则渐渐依辅于北美安全体系。这样安于当镙丝钉的邻居,比之日、俄,真是美妙万千倍不止。
在这个近乎试验场的空间内,美国在政治上逐渐形成了19世纪最为完善、稳固的民主宪政制度。在经济上则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一举反超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霸主大英帝国。至于战略与军事层面,美国确实没有产生俾斯麦这样的战略巨星,也没有率先发明参谋本部制度,但最终美国却超越了俾斯麦与参谋本部制度。
俾斯麦的战略确实高明,但这个高明的战略完全建立在俾斯麦个人的天赋与独特经历之中,别人无法模仿,甚至无法学习。相应的,当时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中,也都是只有国际关系史,而没有国际关系学。所以人亡政息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美国的幸运在于,得益于“离岸性”的庇护和主持国政者的稳健作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那些深刻困扰俾斯麦的战略难题,美国根本无需面对。等到美国深深卷入国际事务之中,必须面对此类难题时,美国的知识精英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20世纪,正是在美国,率先出现了现代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新学科:国际政治学。从此之后,外交战略人才可以经过教育培训产生。同时得益于美国开放的社会结构与完善的政治制度,美国不仅可以吸纳全球人才以为己用,而且可以实现政界精英、军界精英和民间战略学者之间高度灵活性的互相合作与身份转换。这样就使美国能够以无数无名之“俾斯麦”成一“巨型俾斯麦”,而又避免了人亡政息的悲剧。
在参谋本部制度建设领域,德国的参谋本部制度是有其固有缺陷性的。由于德国地处中欧,缺少海岸线,所以德国的武装力量近乎纯陆军,结果直到二战期间,德国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三军总参谋部。
日本效法德国最为成功,但也只是效法成功。直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海陆军还是缺乏有效的协调与合作。不仅如此,在日本,参谋本部逐渐成了激进势力的大本营。由于日本宪法的固有缺陷,日本陆海军直接听命于天皇,结果就与政府形成了不正常的平行关系,并最终将日本拖入军国主义的深渊。以甲午战争为例,天皇组建了战时大本营,身为国务总理的伊藤博文却未被列入名单。因为军人认为开战后无需文职官员插手,如果插手既是外行干扰内行,更是破坏天皇统帅权的完整性。只是因为伊藤个人的独特地位、资历,及其人脉(尤其是和明治天皇之间的高度亲密关系),伊藤才最终以特邀嘉宾的形式列席其间,并多次校正军人们的无知做法。但是,伊藤不常有,而战争常有,这就为日本武人乱政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德、日的问题在美国都不存在。美国以参谋长联席会议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以其完善的宪政民主制度和国防部长文官制度有效地抑制了后者。
所以说美国是一个异数。
首先,在美国之前,民主国家全是小国,甚至一度有人称赞“只有小的才是美的”。美国的崛起打破了这一谬论。
其次,美国之前,陆强与海强是截然两分的。马汉也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既是陆强又是海强,这位被很多后人迷信为海权至圣先师的学者,在写这话时却不会料到,他的国家马上就会成为这样的双强,日后更要成为陆海空三强,乃至陆海空天电五强。美国的崛起不能用单纯的海权或陆权来阐释,它开启的是一条综合性强权之路。美国将英国揭示的海权崛起的历史经验,与德国开启的陆权复兴的时代风潮,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通过一连串的扩张,将大陆国的美利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世界岛”。开启了一道由陆而海,由富而强,以强促富的新强权之路。
再次,无论美国的力量如何膨胀,只要“离岸性”仍在发挥作有,美国就不会引发像当年的拿破仑与后来的希特勒所引发的那种集体反制行动。所有这一切,铸就了美国新时代霸主的地位。1895年的那个GDP超越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最终获得20世纪全球性主导地位的国家,不是英法,不是中俄,也不是德日,而是这个美国。貌似不可思议,实则势所必然。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甲午、日俄两场战争中获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两个对手都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而且都无法全面动员与日本一战。关于这一点,二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修《大本营陆军部》时,亦不讳言。一旦当日本遭遇美国这个对手时,日本本土狭小,缺乏战略纵深,人口有限,资源匮乏,激进思潮横行干扰理性战略筹划的弱点立时暴露无遗。
只是对李鸿章的时代而言,还要再等五十年,所有这一切才能水落石出。但敏感的观察家,应该已经能听到新的地缘带断裂产生的历史之音。
历史多情,它要让李鸿章亲耳听到这个声音。历史又残酷,它要让李鸿章在自己的母国跌落到五千年来最低谷的前夜,亲耳听到这个声音。
联俄迷梦一场空
《马关条约》刚刚签订,李鸿章就开始向光绪呼吁变法:“敌焰方张,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混耋,实无能力。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条约签订三个月后,李鸿章在给着名的儒家基督徒李提摩太口译的名着《泰西新史揽要》作的序言中,再发惊人之语: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以天下为公;赢秦而降,以天下为私。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夏后传子,汤武征诛,则由公而私始矣。而通道四海亦肇端于此矣。天欲与中国以大一统之势浸淫二千余年,至我大清,海禁大开,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此剖判未有之奇,圣贤莫测之理,郁泻勃然而大发,非常于今日,殆将复中国为公天下之局。
在这里,李鸿章将夏朝之前的中国说成是天下为公,诚然有些过于尊古情怀,但他敢说秦之后是天下为私,是君主而非民主,并说西力东渐是一个超越人身体验之上的大历史机遇,是要让中国恢复天下为公的传统,这却不免让后人和时人一起震惊。
很快,李鸿章又有事做了,西太后让他公款环游地球。
这一行,前后190天,行程9万里。表面上清廷是让李鸿章考察各国情势,实际上是给了他一个秘密外交使命:联俄制日。
所谓联俄制日就是与俄国签订针对日本的军事同盟性质的密约。
虽然李的几位幕僚,如薛福成、严复、黄遵宪均早就指出,中国的根本威胁在俄罗斯。但是李鸿章还是承担了联俄制日的外交使命。结果是灾难性的。俄国口口声声叫喊的日本威胁只是个幌子,它的真实意图在于攥取东北筑路权,改善沿海州的孤立地位,并谋求辽东半岛上的海军基地。
李鸿章天真地认为联俄可保20年太平,不料却引狼入室,将整个东北拱手让出,更沦为日俄角力的战场——正因为中俄的接近,逼迫英国加大扶植日本的力度。琅威理当初的预言至此可谓彻底逆转:不是中英联手对抗必将出现的日俄同盟,而是英日结盟对抗中俄不可思议的结合。日本终于借此东风奠定其世界五强之一的地位。
用下围棋比喻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以来的政治生涯,他的起手势很是高远,但很快就受到了各种盘外因素的制约,先是在序盘战中被强制在老定式的框架内行棋,坐失良机。接着在中盘战斗中,被迫在极其不利也极不情愿的情势下进行第一次大战。只是靠了一连串的巧妙腾挪和好运气才避免了崩盘。但紧接着就在更加不利的情势下,被迫展开第二场激战,这一次终于彻底战败。但直到这时,李本人尚未主动走出致命性的败招,于是接着依然还能继续收官。但就在最终失败的前夕,忽然犯下了致命失误,全盘皆输,实在让人费解。
有人说,这是一种赌徒心态。反正是死马当活马医,不如孤注一掷、出奇求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