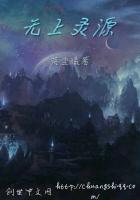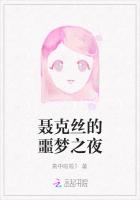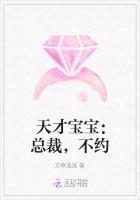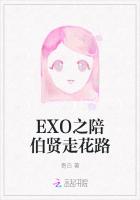急先锋登场
宫古岛贡船事件的消息在明治五年七月十四日(1872年8月18日)传到了鹿儿岛,该地参事大山纲良力主兴师问罪。驻鹿儿岛的熊本镇鹿儿岛分营营长、陆军少校桦山资纪在接到通知后,立即亲自出发上报镇台。他于七月二十五日离开兵营,在二十七日下午三时二十分抵达镇台。由于当时熊本镇台的司令官到广岛分营出差,桦山资纪在与相关留守军官商议后,决定由镇台汇报司令官,他则不去广岛,而是亲自前往东京,直接向陆军卿汇报。
显然,在桦山的眼中,这是大事件。他不顾酷暑,在二十七日当天晚十时离开镇台,十二时经过植木。二十八日下午六时三十五分经过久留米,连夜前进,二十九日下午七时到达小仓,投宿于住吉屋等待船只。三十日正午十二时乘船离开小仓,下午二时抵达马关,再次因等船儿顺带稍事歇息。八月一日晨七时乘船,九时十五分出发。八月三日到浪花,等船两天,五日下午三时到便船,六日上午五时出发,七时抵达神户港,下午四时从该港出发,八日下午一时抵达横滨,五时出港,七时进入品海湾,登陆后入住村田屋。桦山如此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当时,顶着酷暑,急行军般14天,终于到了东京。那么,桦山资纪如此急如星火,究竟是要干什么呢?
这个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
八月九日,稍事休整的桦山首先拜访了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随后于上午十时抵达陆军省,拜见了西乡隆盛那位小十六岁的弟弟西乡从道陆军少辅。为方便工作,他又从村田屋搬到桥区一石桥三河屋居住。而拜见的内容是一样的:陈述此次事件,并主张借机出兵攻略台湾!
十三日,桦山资纪再次拜见西乡隆盛,建议派出台湾生番探险队,对台湾进行详细调查,为出兵作准备。对这一建议,西乡隆盛大表支持。稍后,大山参事派出的汇报官员才到达东京。桦山与之协商后,向陆军省递交了“探险台湾生番意见书”。
此后,桦山又对外务卿福岛种臣、新式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等数十名朝野要员进行了游说,并多次拜见西乡兄弟。
大约也就在此时,日本当局开始在琉球问题上打擦边球,摸起大清国的底牌来。
就在明治五年,明治天皇亲政,强招琉球派使到东京朝贺。十月四日,琉球王子及三司官来到日本。十六日,当他们谒见日本天皇时,被闪电般告知:琉球已被正式册封为日本藩属,等同本土诸侯。国王尚泰列为华族,并在东京赐府第令其居住。三十日又宣布:琉球事务由外务府管理。
对琉球而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而日本更关注清国的反应。在看到清国没有反应后,日本军政高层的胆子更大了。
明治六年(1873年,同治十二年),天皇宣布琉球等同本土府县,事务由内务府管理,并废除国王。结果,大清国还是没反应。日本军政高层激动了。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征台派的微妙变化。
美国大使加剧中日冲突
正如柳原前光曾经提到的那样,早在日本使节赴华之初,欧美列强便担心中日会否结成东方同盟,共同对付西洋列强。美国驻东京公使德朗尤其害怕出现一个以中日联盟为核心的远东阵线,进而搞对内互通有无、对外排斥欧美商业集团的封闭市场。所以他在1871年7月6日呈递国务院的文件中主张:“日本与中国有所不同,我们应欢迎日本成为一个盟友。当与中国有冲突时,文明诸国应视日本为一伙伴。”
今天的读者不免会觉得这位德朗先生多少有些神经质,中国怎么可能和日本结盟呢?但在当年,却并非全无可能。首先,在日本方面便存在着呼吁和清国结盟的舆论声音。甚至有人声称:“今日之日本,求唇齿之邦于宇内,舍满清殆无有也。”(会泽泊语)所以当年的美国国务院对德朗的担忧也是深以为然,国务卿费雪在8月24日亲自指示:“应把握所有可能机会,设法诱导日本尽可能地远离中国,而与其他强权势力在商业与社会上结合。”
德朗接到这个通知后,即于11月15日诘问日本外务省,中日条约是否不同于日本和西方各国签订的条约。日本答以并无不同。
待到前述《中日修好条规》出台,其第二条声称:
两国既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
此文一经公布,果然成为一大外交话题。说起来,《中美条约》第一款说的就是“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大清国与美利坚可算不上“一衣带水”,更称不上“同文之国”,可不也就这样白纸黑字地写下来了嘛。何以同为东亚国家的日本写了类似的话反而成了一大外交话题呢?问题正出在双方的“一衣带水”与“同文同种”,从而造成了西洋列强的猜忌。
而当时的日本军政当局正谋求“脱亚入欧”、“文明开化”,适当地借助清国制衡欧美则可,但如被认为是所谓东方集团的一部分,则大违日本的根本利益导向与价值观认同。
日本政府的底牌德朗大使并不清楚,正因为不清楚,所以才越来越担心中日同盟的出现。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得知了琉球漂流民事件,他更知道日本正在谋求将琉球“内化”,并不断声称琉球在日本的主权范围之内。于是,这位德朗大使敏感地意识到,这次事件或可成为瓦解中日联盟的关键转机!
没想到,机会居然主动送上门来。
原来,在北京谈判的柳原前光通过“京报”看到了闽浙总督上奏清朝的有关琉球漂流民遇害事件的报告,当时便意识到是个机会,乃于1872年5月转报时任日本外务卿的福岛种臣说:“琉球人在清国领土台湾被杀害,为鹿儿岛县参考。”
并附送该报为参考资料。但并没有引起外务省的充分注意。7月,柳原与英国上海领事会谈时,对方趁机挑唆,称如果是欧美国家遭遇如此事件,即刻就会派遣军舰前往,追求责任并索取赔偿金。柳原更觉机不可失,乃于8月回国后再次向外务省建言,终于引起日本外务省的高度重视。
受此影响,福岛种臣于9月23日约见德朗,讨论台湾问题。
在这次会晤中,德朗提出了三种策略供福岛参考:
第一,是否要立即派遣问罪之师?如按此案行动,等于将生番杀人劫货等同于海盗船事件。
第二,是否要与土着交涉,以订立今后之管理方式,以保障日本人及琉球人抵达时不再被施暴?如按此案行动,等于将此问题当做一法律问题解决。
第三,若承认生番问题属于国家统治权问题,是否要向清政府交涉要求处置?如按此案行动,等于承认中国对台湾生番的主权。
对于这三个提案,福岛并未表态,相反,他更感兴趣的是德朗带来的大量关于台湾的图文资料,尤其对于番汉界线的存在极感兴趣,并向德朗试探性地询问:“图中……记号界外是清国管辖之地吗?”德朗答道:“虽然是清国管辖,但其政府指令不行,故无法保护人民。”德朗认为,与其与清国交涉,不如直接和番民交涉。并指出了在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之处。
福岛对此不置可否,转而大言不惭地声称,早在荷兰占据台湾之前,台湾就是日本的一部分了,“称之为高砂岛就是一例”。又问德朗:“台湾为我瞩望之地,贵国意见如何?”德朗立即表示:“美国向不占有他国土地,但我友邦如占他国土地而大力进行殖民事业,则符合美国利益。”德朗甚至称:“若贵国派舰船到台湾,我方军舰有该处之海岸地图等,虽然能力有限,但愿为帮忙。”还表示美国驻北京公使可以帮助日本办理外交手续,“万事尽力协助。如拿定主意,请及时告知。”
对此表态,福岛自然是喜出望外,便也顺势提出自己的三个构想:“第一,请清国政府处罚杀害琉球人之土着,若不能则,采取第二案,即希望清国与日本戮力处罚土着。如此案也不能行,则采取第三案,即不通过清政府,由日本单方面出兵台湾问罪。”福岛虽然表示了三者的次第关系,只有前一个无法实行时才能进入下一个方案,但他接着又说:“我方有可能采取第三方案。”即不经过清政府,直接派出问罪之师。并声称哪怕只是普通的策略,也应该派出一万名士兵去台湾。
10月16日,福岛又约见德朗,询问美国1867年出兵台湾的经验,并索取美国海军所有的台湾地图和相关资料。
对德朗而言,这可真是福音。他意识到,此举将有效破坏清日同盟的出现。
问题是,资料何在?没想到,很快就来了献地图的美国张松。
“美国张松”献地图
这位“美国张松”不是别人,正是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的李让礼。
这位李让礼本是法国名门之后,出生于1830年8月26日,巴黎大学毕业,后因与美籍女子结婚而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还以义勇兵身份参加了南北战争。战后以武转文,于1866年12月当上了美国驻厦门领事。就在他到任的第二年的3月,发生了14名美国海难漂流民在台湾被生番所杀的“罗妹号事件”。
根据中美《天津条约》第十三款规定,美国船只在中国洋面遭风触礁搁浅,遇盗致有损坏受害者,地方官一经查知,即应设法保护,并加抚恤。“罗妹号事件”发生后,美方反应不一。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态度较为客观中肯,他一方面认为地方官反应迟钝,行动不力,负有责任。但又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帮助中国完善内部组织,并扩大官府在台湾岛内的有效施政范围,逐步消弭生番的祸害。但美国驻港领事阿伦则向国务院建议出兵占领台湾。
李让礼的立场与后者相同。他在4月1日得到消息后,一面与中国官府交涉,一面于4月11日亲乘亚士休洛号前往台湾活动。并进而鼓动美国亚洲舰队司令柏尔出兵台湾。李让礼诡称,中国官府在台湾的控制地只有西部沿岸、琅峤以及东北部的苏澳等地,其余东部及东南部,全为生番居住地。柏尔遂决定率领哈德福号与怀俄明号征讨台湾生番。
途中柏尔挑选了181名精锐水兵组成了登陆部队,配属5门榴弹炮,120支步枪,以及充足的弹药和足够4天用量的口粮与饮水。
6月13日上午八点半,两舰抵达台湾南部海域。九点,在哈德福号舰长柏乐内的指挥下,登陆开始。当地生番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战术,逐步将美军引入密林地带。美军在恶劣的天气和地形中艰难跋涉,到下午两点便自动丧失继续前进的力量。就在此时,生番利用密林掩护对美军展开火枪狙击。警戒部队的指挥官麦肯基(哈德福号副舰长)当场阵亡。美军根本找不到敌人所在,只有顶着酷暑狼狈撤退到滩头。随后感觉到在滩头过夜也是很危险的,只有再撤回到舰上。为了挽回颜面,美军准备火烧当地的密林,但因为季节原因,火一直没有烧起来,最后只有无功而返。
这次行动的失败令柏尔意识到,台湾生番问题的解决成本太高,最好的方法还是帮助中国官方逐步向南扩大控制力,并以大陆移民逐步取代沿海地区的生番。
根据这个方针,美国又转而与台湾地方官府接触。李让礼参与了当地官府组织的南征,趁机搜集了大量情报。并借势与当地的原住民进行了直接接触,最后达成了救助美国漂流民的四点协定:
一、生番对杀害罗妹号船员一事表示悔过,美方不予深究。
二、嗣后船员遇风漂至该处登岸,生番妥为救护,移交琅峤地方转送。
三、船只人员如拟友善登陆生番地方,应举红旗为号。
四、生番地区不得设立灯台。但可于熟番区域择地设立。
当琉球漂流民被杀事件发生后,李让礼又于1872年2月29日抵台,先后赴打狗、枋寮、射寮等地打探消息。地方官员以礼相待,并告知此次事件中没有欧美人受伤,表示此前并没有保障琉球人的条文,故而不负责任。李让礼在确认没有美国人遇难后,顺道再次搜集了台湾地区的大量情报后准备回国接受新的任命。
当李途经日本回国时,便成了德朗与福岛的及时雨了。
洋高参谋划偷袭台湾
1872年10月12日,李让礼辞去厦门领事职务准备回国接受新职。一周后,李让礼抵达日本。福岛不惜屈尊降贵,带着日本外务省的美籍顾问史密斯从东京跑到横滨,于10月24日拜会了李让礼。
李让礼一看有机可乘,便取消回国机会,给福岛上了一堂扫盲课。
为了呼应福岛关于日本对台湾主权的谬论,李让礼居然以他曾经在台湾见到过日本刀剑为根据,响应福岛的歪论。福岛慌忙回应道:“昔日日本人巡行台湾东方时,汉人尚未来到此地。”李让礼立即回应:“确实如此,最初日本人渡航到印度附近时,曾经巡行该处。”并妄称:“大陆与台湾虽然距离近,但汉人并未能前去。日本虽然距离远,却在史籍上可见曾航渡到此。汉人发现台湾是在1400年,而日本则在此以前就来过此地。此事应该强调。事实上清国并未领有台湾,荷兰人占领之后,后来才交给清政府的。”福岛便再次提到“高砂国”的问题,并说:“高砂大概是因为沙地多才如此命名的。”李让礼说:“原来如此。后来汉人耕作,沙地就少了。只有河口才有沙地。”
如此这般一番互相呼应之后,二人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李让礼对日本外务卿居然如此缺乏对台湾的了解深感“震惊”。而福岛也对李让礼的“渊博”
和情报之珍贵而深感震惊,特地设盛大宴会款待,并说他与李是“相见犹恨半日之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