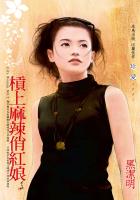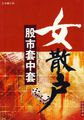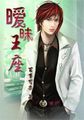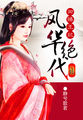1
桥堰镇坐落在靶台山的一支余脉上。
余脉缓慢沉降,又岔出两根末梢。从靶台山俯瞰下去,两根末梢更像老棉裤的两条裤筒,臃肿、窝囊、疲软,长短也不一般,仿佛是从山上随手丢下来的破烂。桥堰镇只能顺着两条黑糊糊的裤筒布局,抻得平展的这岸叫南桥堰,抽搐成一堆褶皱的那岸就叫北桥堰。一股红水顺着裆间淌下来,红水血淋淋的,有着可疑的温度和黏度,冬天不结冰,好像真有一个霉烂的子宫,埋藏在靶台山峪那看不见的深处,长年四季,潺潺不绝。
扒岭桥横担在南北桥堰中间,是两堰人货的来往通道。
传说,汉刘秀落难,曾窜伏到桥堰,在山里屯兵练武,靶台山的名字便由此而来。靶台山上有一座刘秀庙,庙院筑在二营盘。靶台山上有二营盘,却没听说过有“大营盘”。类似的传说还有扒岭桥南岸的桥头庙,桥头庙没名号,不能和老君庙观音庙相提并论,有记载说它建于洪武二十年,本来是桥堰人给一个郎中搭建的生祠,郎中的姓名失传了,于是生祠变成了庙台。
一山不出两宝,到了桥堰地界,偏偏就会屙金尿银,用桥堰的老话说,“凿开靶台山,又是硫铁又是炭”。其实远不止这两样,山里还有凿矸采汞烧石灰炼硫磺挖铝矾土的。这些宝藏也给桥堰带来一害,就是河槽里断断续续的这口血水。早年,桥堰人都叫它“矾水”,矾水是采矿过度污染了的地下水,水面上那层带着腥味的血红,就是氧化铁的颜色。这矾水自然是不能吃、不能洗,就连地也不能浇,是一股地地道道的废水脏水臭水。每年的夏季来临,雨水行动,山上的水跑下来,把猩红的水面抬起来往两边赶,仿佛上游有个巨大的屠宰场往下放血,有数不清的猪脖羊腔在往出控血。这时候站在扒岭桥上俯瞰河槽,那红流涨腻,不起波澜,展宽的河面,犹如一块漆了朱红的棺材板,狭长,巨大,凝练,厚重,逐渐盖严了河滩。没人见过河水褪色,就是连下三场豪雨,也不见水流清淡。大水过去后,红水又收缩回原初曲折隐晦的身条,一副用行舍藏的模样。这个时候,再看河槽里的乱石,滚满河川,就像刚砍下来的人头,被染得通红,站在桥堰两边往下看,人头滚滚,有些瘆人。
有人想把桥头庙改成河神庙,遭到桥堰百姓的反对:矾水这么龌龊,怎么可以劳烦河神爷来看顾呢?
两岸黑,一川红,便是桥堰镇的基本色调。
南桥堰地势比较平缓,住着桥堰的大户人家,像袁家垴的袁和尚家,勺坪的陶家崔家,都是开煤窑的,都有一座四水归堂、几进几出的好宅院。一道青石板铺砌而成的街衢,串联起十几家临街的小商铺,有粮油店布匹店,铁匠铺箍桶摊,豆腐坊蒸馍铺,染坊小肉铺,小饭馆小客栈,还有花圈店棺材铺。这些店东的底气都不够厚沉,只能依靠本地百姓的零星生意维持光景,真正能和袁陶两家比肩摽膀子的,就剩徐家堡上青砖雕花大门楼里的徐家,徐家是开炉炼铁的,丁财两旺,高大厚实的门垛上,总是拴着六七匹膘厚口轻、溜光水滑的骡马,从来没下过这个数儿。
北桥堰的住家光景疲羸,住在低洼处的人家,还有一圈乱石垒叠的虎皮门墙,半坡的家户多数都住在暗窑里。这种暗窑就坡趁崖,切出前墙,然后直接在山体上掏洞,没有砖石垒砌的前墙,顺着北岭坡一层一层往上摆摞,形成大大小小的台阶,叫出的地名也都带“台”字,像大圪台、二圪台、垴畔圪台、小铺圪台。这些家户们稠一堆儿,稀一片儿,傍崖靠山,趁坡就梁,散布在老棉裤褶皱里。鸡飞狗跳、人来人往,仿佛寄生在这窝囊臃肿的棉裤里的虱阵虮行,细腻的煤尘长年累月在桥堰的天空中沸沸扬扬,四处飘浮,落在屋顶房檐,落在炕头灶台,落在鼻子眼窝,落在鸡冠子狗鼻尖猪耳朵羊尾巴上,落在老棉裤的角角落落……
桥堰人慨叹,书上说“人杰地灵”哩,咱这地方窝囊,人也跟着窝囊了。
桥堰煤窑多,不下窑的男人们稀少。桥堰周边的人经常笑话桥堰的男人没出息,说他们活一辈人,就钻三个窟窿;从红窟窿爬出来,就钻进黑窟窿,从黑窟窿爬出来,就钻进土窟窿。有外人编排,桥堰老婆们的那个窟窿也算上的话,就成了四个窟窿。
桥堰人窝囊在不离窝儿。民国之前,桥堰人挑着担子到平东县城纳一次粮,就算出远门了,临走的头黑夜,一家人还要关起门来抱头痛哭一场的,哭得房倒屋塌,能荷起重担出门送粮的,哪个不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啊,一家人就朝生离死别的方向哭,就朝一去不返方向哭。实际测算一下桥堰到平东城的路程,也不过七八十里,但是,没见过世面的桥堰人怕事啊,到七八十里外给官府送粮,不得和官家交言搭语吗?万一出了差错咋办?惹下官司谁搭救?这事故不敢细想,又不能不想啊,七八十里,一跬一步,一步一跬,消息传回来,家人赶过去,施救都来不及啊,最多能见个人头落地。七八十里,死丧在地,活人们咋给死人收尸?因为怕出门,桥堰没出过“大人物”——人都下窑挖煤去了。
桥堰镇也有一件体面的宝物,就是扒岭桥,扒岭桥是一座独拱石桥,桥长八丈,宽丈八,拱高三丈有余,卷拱的拱石都是两拃厚,两拃一尺,站到桥底下就可以量数出来,十八个并拢的拱圈支撑着厚重的桥面。从砌基础铺桥面的条石,到卷拱用的弧形拱石,料石裁磨得中规中矩。拱圈的东西两侧,各有斗大一块浮雕,刻着一个眉目狰狞的龙头,有镇压吸纳和吞吐自如两层意思。扒岭桥通体使用黄玉色的石材,这些石材来自靶台山一个叫做黄炉谷的深涧,从扎在河槽底下的根石,一直砌到桥顶头,不掺灰夹泥,全靠石材自己拿劲,严丝合缝,缝隙严密得刀刃不进,结构紧凑得浑然一体,宛如从全石的肚子里脱胎出来的天然石桥,直接落巢在桥堰镇了。这种石材的肉里还沉淀着些许粗颗粒的石英晶体,乍看质朴粗糙,触之手感绵软,或许是年代久远,锋芒收敛。桥栏柱头雕刻着狮虎兽头,姿态各异的兽头,已被行人的身手磨蹭得溜光水滑。白昼,桥身还会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线,这些炫光来自石材的肌理那些石英颗粒。若从远处观望,扒岭桥还会自生烟霞,像是带了几分缥缈的仙气。赶上雨过雪融,洗尽灰尘,天光润色,山色陪衬,扒岭桥面貌一新,珠光宝气,显出精神。扒岭桥就这样把凌乱不堪的南北桥堰联系起来,它是系在烂裤腰上的一条玉带,即便常常蒙着尘灰污垢,也有光鲜峥嵘的时候。
来桥堰采买煤铁的外人,往往会到扒岭桥上走一遭,这些外人看看桥,再举目四顾破烂不堪的南北桥堰,就会又欣羡又遗憾地说:“不般配,一点也不般配。”好像扒岭桥投错了胎,埋没在桥堰了。他们隐忍不舍地抚摩着栏杆上光溜溜的兽头。
2
民国二十六年,夏。
九莲出嫁当夜,新女婿徐卯泰来丈人家谢婚,徐天元又跟来了。
上午徐卯泰娶亲,徐天元的身份是押轿小子,晚上谢婚,天元就成了提灯笼的小仆人了。
陪着新女婿上门的徐家人来了十二个,正好一桌半,这个数目预先打过招呼。大客人是徐卯泰的二哥有泰。来人手里都不空,提着烧酒生肉礼盒等,不拿礼的,手里就打个红灯笼,添个红火喜兴。
徐卯泰的婚事是兄长们操办的,徐家堡那边,有大哥丑泰在张罗摊场。
徐天元手上提个红灯笼,笑嘻嘻地四下张望。徐天元和徐卯泰同岁不同辈,徐天元喊徐卯泰叔叔,小叔。
徐卯泰的丈人吕乘之是一个赁屋设馆的先生,院落不大,屋里屋外摆设六七张桌子,有的贺客要后坐,就干脆等在街门外头,这些贺客的孩子都是吕先生的学生。屋里院中端盘的烧茶的在灯影下吆喝穿梭,很是热闹。
徐二娘单怕黑夜酒席筵上有人闹腾,把新衣裳拽扯脏了,出门前让徐卯泰替下长衫,换了一身新缝的绸缎常服。人靠衣装,又值人逢喜事,徐卯泰头戴着红顶闪光黑缎小帽,脚蹬千层白底扎帮青布鞋,长身玉立,一张薄脸格外精神。
“五官周正,一表人才,吕先生选了个好女婿啊。”
道喜的人们嘴巴里噙着冰糖,说出来的话也甜滋滋的。
吕先生给客人敬酒时,灯下认出徐天元,说:“你就是那个胡作乱的天元哇?”徐天元赶紧离了板凳,起身叫先生,双手奉杯,躬身接酒。十年前,他和小叔徐卯泰在吕先生的私塾里发过蒙,现在他长得比吕先生高出一头不止。多少年过去了,吕先生重提往事,徐天元不免有些尴尬。吕先生把着锡壶不放,笑道:“没想到今天咱们攀上亲了,你比卯泰低一辈,论辈分,你该叫我姥爷了。”边上的贺客起哄,让徐天元改口叫姥爷,徐有泰也站起来,笑着让徐天元好好陪姥爷喝几盅,赔情道歉,徐天元脸红脖粗,张了张嘴,却怎么也叫不出来,像是让酒呛着了,徐卯泰坐在当炕,和大伙一起瞧热闹,吕先生平素不苟言笑,今天办喜事,难免多出几分殷勤的待客之道。
吕先生家里用的是口径小如铜钱的二钱泥盅,吕先生的酒刚斟平,灯头火焰连抖三下,天元手里的盅竟喀一声碎成两半,客人瞅见灯下徐天元一脸慌张,吕先生的脸当下就暗了一截。
旁边有人说:“没事没事,喜冲了喜冲了,这个旺气,快,换上一个盅来。”说话人是杨先生,他也是私塾先生,在章家井设馆,今天是专门来给吕先生帮忙的。
换上盅,徐天元连接三下,吃进嘴里。方才灯头连抖,他怕失手,手指稍稍用力,意外捏碎了小泥盅,弄得自己挺尴尬,快饮三下,就是想遮掩过去。
盅小酒浅,全浇在舌头背上,慢慢才烧到喉咙和肚肠,徐天元张嘴吸气,觉得一溜火线正穿喉而下。
徐天元从小顽劣,下课如厕,经常冲着吕先生的夜壶嘴撒尿,吕先生打他手板,徐天元不敢尿了,过了两天,他竟用两截荆条夹了砖缝里歇凉的蝎子,塞进夜壶嘴里,多亏吕先生是个读书人,凡事细心,晚上有开水烫夜壶的习惯,方才没着了道儿。吕先生吃了惊吓,翌日早课,逼问学生,不说出谁干的,就得人人跪地顶砚瓦,吕先生一吓唬,徐卯泰马上说了实话,吕先生抓过徐天元的手,狠狠抽了五记手板,手板是用花椒木做的,打在手心里又麻又烫,徐天元咝咝吸气,龇牙咧嘴,吕先生不解气,加罚徐天元跪在院心,头顶石砚,吕先生往砚池里舀了一勺水,勺壳点着徐天元的鼻子说:“你不是习武吗?我今日倒要看看你能跪多久,洒一滴,加罚时辰。”然后布置其他人写仿。中间,徐卯泰急尿出来,看见徐天元直挺挺跪着,便跑过来蹲下,笑嘻嘻地问天元膝盖疼还是脑袋疼,徐天元直着脖子埋怨:“别人都不说,就你说!”徐卯泰说:“他们怕你,我不怕。”徐天元梗着脖子说:“你害我。”徐卯泰嬉笑着站起来说:“我要不说,你就害了我了。”
这都是小时候的儿戏,徐天元没想到吕先生会在这个场合重提旧事,吕先生见他失措,拍拍他的肩膀说:“坐下夹菜,压压酒气。”转身去招呼桌上的客人。
不知何故,从不贪杯的吕先生捏着小酒盅不放下,和客人碰着喝了不少酒,越到后来越能喝,平时的斯文相让烧酒燎没了,脑门儿、鬓角、眼白、耳朵、包括脖颈,全红了。
吕太太劝他少喝点,吕先生眼立起,直着舌根说:“你管你?今日我,高兴……”
“高兴高兴,”客人都附和,“嫁闺女,大喜事,放开喝两盅,不妨事的。”
杨先生也红了脸,安慰吕太太:“没事的,嫂子。孔圣人说‘唯酒无量,不及乱’就行,吕先生话不乱,没事的,不怕。”
吕太太撇嘴道:“都喝得脸红脖粗说话结巴了,还不乱?当是喝没主儿的呢?”
吕先生见众人帮腔,就说:“咱喝,今日高兴高兴,管它明日,高,不高兴……”
客人们都笑道:“明日高兴,天天高兴。”
吕太太想了也是,平时光景拮据,吕先生才不沾染酒瘾。今天嫁女,人逢喜事,当爹的能不开心?吕太太没有再拦挡吕先生,忙着到厢房里招呼女客去了。
新女婿和客人还没走,吕先生已经酩酊大醉,满嘴胡话,说话的口气也像换了一个人,吹自己熟读相书,深通命理,恨世道黑暗,叹生不逢时……这些话,他从来不说。
“酒坏君子水坏路,”吕太太隔着缭乱的客人,着急地说,“这下乱了。”
“没乱,‘乱不及防’就不算乱,没事的,我说没事就没事,”杨先生惺惺相惜,叫人把吕先生扶到炕上躺了,安顿停当才辞别出门。
留下贺客继续吃酒热闹,不时听到吕先生在房里提着力气念白:“三杯,通大道……”
客人们悄悄说:“今日吕先生真开心了,可惜量浅,这才喝了几下?”
有人说:“没听见吗?‘三杯’。”
“三盅就喝成这摊场?”
吕太太送完客人,自有邻家媳妇们留下,打帮洗涮盘盏,等把一应家伙整摞停当,已经鸡叫头遍。
徐天元搀着徐卯泰离开了勺坪的吕家,一行人都沾了酒,嘻嘻哈哈地顺着石板路往徐家堡返,走到椿树坡底下,老远就瞅见坡头上的椿树黑糊糊的。
树冠悬在半空,好像一块乌云,月辉稀释了夜色,却化不开藏在树冠里的浓重的黑暗。
徐有泰打着红灯笼走前,徐卯泰突然推开天元,紧走几步,抓住挑灯笼的棍子,一口吹熄灯笼。徐有泰没有防备,被拉得踉跄,随后就闻到徐卯泰嘴里喷出一股子酒气。徐有泰笑道:“你做甚?多了?”
“不是多了,是……省蜡。好我那二哥,我今日……喝油汤喝得我昏起来,也是应该!”
看不出徐卯泰是佯装醉态,还是真醉。今天是他的喜期,他喝水喝得昏起来也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