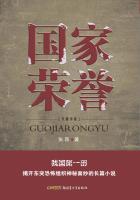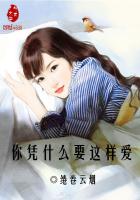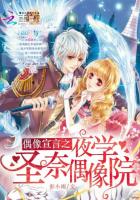封建官场为追求理想的人提供了实践场所。
深远地讲,官场是政治理想的具体表现,新型的官场,需要怀着崭新理想的政治家。
而陈旧的封建官场,一方面渴求变化的清风,另一方面却又排斥和绞杀着新型势力。
封建官场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统一体,是衰亡也是新生。
我国自古就在各地设立孔庙,每逢孔子诞辰纪念日时,庙的四周都热闹非凡。逢此时节,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庙,来访游客更是络绎不绝。
孔子在当时被誉为“至圣先贤”,今天仍获得“万世师表”的评价。孔子所说的处世为官之道,经众多弟子的阐述而成为儒家学说,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延续了二千多年,孔子被人视为偶像,顶礼膜拜。今天让我们把他看做一个平常人来重新审视他一番。
不以多能为可耻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山东曲阜。其父为孔纥,母亲为颜氏之女;因传说孔纥并未经正式仪式娶颜氏之女而生下孔子,所以对孔子“圣贤”的尊称,很多人无法认同,也因为如此,有关孔子的不少真相就被官方隐藏起来。
孔子自幼丧父,懂事后迫切寻求父亲之墓,母亲却迟迟不语,因为她不愿儿子知道真相,后来,母亲也过早地离开人世。
孔子年幼时生活卑微,毫无依靠,替别人管仓库,放牧牛羊。他的生活充满痛苦和屈辱。
吴国太宰对孔子学生子贡说:
“你的老师是何方神圣?为何如此多才多艺?”
孔子听后,说道:“因为少时鄙贱,所以学会许多琐碎的技能,因此这话未免有夸赞之意,但也意味着我与君子无缘。”
孔子以丰富博杂的学问立身,这和他幼时的生活体验很有关系。在古时,教育落后,对于贫穷者来说,求学很困难。但孔子不畏困难,不断努力,修撰著述,制定礼乐,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些努力的情形都可从《论语》中得知。
“三十而立”,孔子为了生活,为了寻求学问,更为了让世人知晓他的思想,而孤独地奋战。
孔子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
鲁是周统治下的大国,周朝开国君主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于此。武王死后,周公辅政,制礼作乐,为封建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但在孔子的青年时代,封建体制早已名存实亡,一国之君空有虚名,政治实权都操纵于贵族之手。尤其是季氏,掌握了鲁国的军队和税收,行为专横恶劣。
依据礼制,献乐舞给祖庙,必须按照身份,以决定规模的大小和内容。例如献舞的人数,天子是六十四人,诸侯为三十六人,大夫为十六人,士为四人。但季氏不过是大夫的身份,却拥有六十四人的献舞,无视天子的存在。
孔子说:“季氏不过是个大夫,却奉天子之舞,太傲慢无礼,太过分了。”
对于其他非礼的行为,孔子也非常愤慨:“不懂仁义之人,就算依礼奉乐又有何用?”
当时国君为鲁昭公,但季氏族长季平子却处处霸权,和其他贵族不断发生纠纷。昭公便想趁此机会打倒季氏,夺回政权,于是和反对季氏的力量联合,包围季氏的住宅,迫使季平子自杀,而孟氏和叔氏却拥护季氏,势力十分庞大。
鲁昭公终于失败,投奔齐国,至死都不能回国,流亡在外达七年,王位一直处于虚设状态。
孔子对贵族们的作风早已感到厌恶,于是也随昭公逃亡到齐国。
齐是功臣姜子牙的后裔,由管仲辅政。孔子来到齐国,接触到许多古典音乐,大为感动,于是对音乐开始注意,但他来齐国最大的目的是做官。
首先,他通过大夫高昭子出仕,希望借此接近齐景公。高昭子恶名昭彰,后来引发齐国内乱而被杀。孔子对此毫不在意,他认为当官不过是实现理想的手段,在孔子内心深处,理想主义和清晰的现实主义并存着,由这一点可以证明,他是个重实践又富有理想的人。
齐景公召见孔子,问:“政治的关键是什么?”
孔子答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其各行其是。”
这样的答案,道出了礼制的根本,同时也讽刺了齐国当时的内乱情况。
齐景公本意重用孔子,因招致其他大夫的强烈反对,被迫收回成命。
于是孔子重返鲁国,一边从事教育工作,一面继续寻求从政的机会。
不流血的革命
季氏有强大的权势,但内部也有矛盾。
季氏管家阳虎在季平子死后掌握了大权,把季氏一门斩尽杀绝,使季氏流离失所。区区一个阳虎,不过是个大夫,但借助季氏大权,摇身一变,成为掌握鲁国政权的大人物。
孔子此时已经将近五十岁,学者的名声显扬天下,门下弟子不断增加。阳虎为巩固自已的统治,竭力想得到孔子的支持。
阳虎绞尽脑汁,欲与孔子会谈,孔子都避而不见,于是阳虎派人给孔子送礼,而孔子欲趁阳虎不在时,至阳宅谢礼,不巧,在途中遇见了阳虎,阳虎立刻上前说:“请务必至寒舍一坐。”
等二人来阳虎家坐定后,阳虎开始说:
“夫子才干过人,却不愿一展才华,对国家的变乱熟视无睹,这岂是仁者应有的态度?”
“不可如此说。”
“那么有意执政却不断放弃机会,这岂是智者应有的态度?”
“不!”
“夫子应该知道光阴似箭,时不待人。”
“不错!我会尽早出仕的。”
阳虎看似厉害的角色,连孔子都不得不顺从他,但孔子却毫无协助他之意,因为阳虎背叛了主人,实在是一位不忠不义之臣,对于持忠君思想的孔子来说,阳虎之类根本不能接近。
孔子主张的政治理想可以用“德治仁道”来概括,以统治者的人格为本,注重教化而不重视强权,建设道德人伦的理想社会。
孔子的理想受民众信赖,依仗道义执政,把理想社会中的人称为“君子”,因此,他的教育目标是使人成为君子,这等于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
谈论理想的沙龙
有一天,孔子和子路、曾、冉有、公西华四人闲聊。孔子说道:“今天不必顾虑因为我比你们年长,心中有话就尽管直说。你们平常总是慨叹别人不了解你,但是有朝一日有人赏识,你们怎么做呢?”
子路第一个回答:
“我要到一个充满内忧外患而痛苦不堪的国家,虽然外面有邻国侵略,内有饥荒,我也要将勇气和正义教给百姓,三年之内,必能渡过此难关而建立理想国家。”
孔子微微一笑,改问冉有:
“冉有,你做何打算呢?”
“我只想固守一个地区即可,说不定我还无此能力,以礼乐教育百姓,保证三年之内,使人民丰衣足食。”
“公西华!你怎么做?”
“我也无多大的信心,但愿试着去做,我希望能担当宗庙祭典及诸侯聚会时身穿礼服搞接待的小官,做起来得心应手没有差错。”
“曾!就剩下你了!”
曾放下手中的弦琴,站起来说道:
“我的愿望和你们不太相同。”
“别顾忌太多,这只是把个人的心思说出来罢了!”
“我很想在春回大地之时,和青年人五、六个,再加上五、六个孩童,每个人穿着新衣服,到郊外踏青。走在汩汩的溪流边,到凉亭吹吹微风,引吭高歌之后,高高兴兴地回家。”
孔子颇有感触地说:“曾说到我心里去了。”
不久,三人离座而去,曾留下问道:
“老师!您对他们的理想有何看法?”
“大家只是说说自己的愿望而已。”
“但老师为何笑子路的回答呢?”
“负责一国政治的人,必须谦虚谨慎,但子路的说法有些自大,所以我不觉失笑”。
“那么冉有的愿望,岂不正是一国之政吗?”
“不错!只不过他的能力不限于区区一个小国!”
“公西华呢?”
“宗庙的祭典或诸侯的聚会都是国家的例行公事,公西华说得谦虚,但能担任那种职务者,即大有可为。”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三点:第一,孔子教育的中心目标,是培养实现自己理想的新型官吏;第二,虽然他们内心充满了理想,但是却得不到实现理想的机会;第三,孔子也有一种时不与我的感慨,所以很想抛弃政治,过悠哉舒心的日子。
哗众取宠,非君子所为
机会终于来临。
受阳虎之害最深的季氏特别重视孔子及其学生,因此季氏在孔门中物色了年龄最长、最勇武的子路和聪明的冉有为家臣。
这期间,季氏曾经和孔子交谈过:
“我想子路和冉有是不可多得的良臣,应该多提拔他们,你看如何?”
“您言重了,良臣应是忠于道义,甚至将道义看得比君主还要重要的人,若不能遵循道义,即使去职也在所不惜,他们二人不过是平凡的官吏罢了!”
“你的意思是不必服从我的命令!”
“若你要下令,要臣杀父弑君,必不能遵从其命”。
出仕于谁,谁就是自己的君主,但未必要言听计从,这是孔子一再强调为人臣者应有的认知,孔子曾赠子路一言:
“该说的话就要坚持到底,即使为此和君主发生冲突,也不能逃避。”
另一方面,孔子也不曾忘记做臣子应尽的职责。子路担任地方官时,率领人民治水,见人民生活穷困,便自己慷慨解囊购置大批粮食以救济灾民。孔子辗转听到后,即刻派一名弟子设法将子路所供应的粮食全部退还给他。子路激动地向老师抗议,孔子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