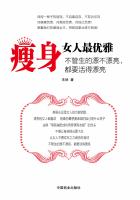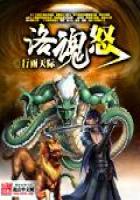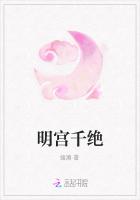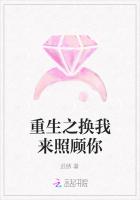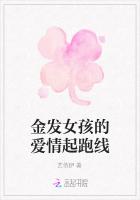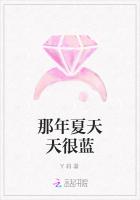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母亲唤我起来,就着这清油般的一点光润,出旅馆的宅院,去看看白洋淀的晚夕。夜好得很。我扶着母亲,绕过一棵粗壮的海棠树,站在郭里口的桥栏旁。乡野的狗吠声隐隐浮动在苇塘深处,间或有秋虫羞怯地和着。白白的月光底下,一淀秋水茫茫沉沉地伸展到天边去了,看不清了。近处的波怀里,放养着簇簇群群、触手可取的星颗子,长在水中的菱角似的,饱满而老实,这会儿都楚楚地醒着,抖着眉眼,放着那洁净的光。
我先前是计算向房东买下一只河灯来,依着白洋淀一带的乡俗放了陪母亲乐的。在呼兰河,便有着放河灯的习俗。萧红写过,很美的,我却只在小说里见过。城关长大的孩子总少着真正的美的教化。就一直想放河灯。河灯的本源大约是祈福祭奠之属,并不是回民喜欢的风俗;可我觉着它实在美好,便有了念想,便不排斥。只是房东劝我们,时候有些晚了,下淀也是不安全的,况河灯总须很多人来放才有味儿。我便有些索然。
国庆长假,看罢阅兵式,就扯着老太太逃出了北京。母亲很想去看华诞夜下的天安门,看广场上陈列的花车,仿佛这便很可以叫她满足了。我却专制起来,不愿我的母亲和那么多瓤瓤塌塌的看客挤在潮水里,看车上的假花。我说,咱们出去走走,去白洋淀,孙犁的白洋淀。母亲大抵不愿刚工作的我因她的来到而添了负重,就总说在北京过节很好了。我看出她的心思,就说白洋淀并不远,有连片连片的野荷花,你不是最爱看荷花么,我们去那里看,比北海都壮观得多——我那时全然忘却了荷花开放的时令。旅游网上说,黄金周的白洋淀荷香飘十里,我诚然有隐忧,但宁愿相信那不是伪说。再一层筹算,便是归途可走一趟沧州故里。闯关东出去的人,汉民是山东来得多,回民则多来自河北。我们石家的祖籍便在那运河边的泊镇;母亲的尹家,也在不远的青县。我就总盘算着,带上从没回过关里娘家的母亲走走去。
出发那天清晨,母亲起得很早。我睁眼醒来时,她已备好了一切行装。她嘴上不同意,却将这桩出行盼了许多日,大概只因我绘声绘色描画的那一淀荷花。母亲不认得孙犁,她在“忠”字舞曲中读完的初中课本里,也没有那篇不合调性的《荷花淀》。但母亲爱荷花是真切的,她的心肠和荷花并蒂在一起。
凉风渐渐有些沉了。
既放不了河灯,我们便回农家歇下。这静谧、深沉的郭里口,是隐在芦苇荡中一个三面环水的村庄,是白洋淀最近的入口,却不红火。主码头是在新安县的。我出门有个习气,不喜到游客趋附之所,只走异常的路,这便带着母亲,从雄县进来,追到这里来了。据说抗日那会儿,统领着回民支队、雁翎队的吕正操司令,也是从郭里口进淀的,这分明使我对这个不名的村庄,多了几分亲昵。但我确实没想到这地界凋敝成这副样子。黄金般珍贵的长假,人们不愿来诗意却不好玩的白洋淀;到郭里口来的,自然就更少。
我是被窗栏外的鸡鸣唤醒的。
水乡的清早湿润润的,有一股枣花般的甜气。桥上不知何时聚起一个早集,乡人摆出自家的杂货、果蔬,还有野鸭蛋,不动声色地待人打问。我们穿行在集里,欲去村庄的腹心寻看。母亲背一个小挎包,我把外套围在腰间,袒着惹眼的粉衫,一打眼便知是外乡客。但我们没有像在别的旅游区那样,被任何一个卖家拦截,这里连叫卖声也是稀少的。郭里口村的人们和白洋淀的秋水一般沉静。他们素色的面颜和节制的言语,让我觉得遇见了自己人。
房东唤来船夫,就上了一条快艇,独我和母亲一户。本想是租下一条木船,划桨过去的,船夫说去年还可以,如今官家管得严了,只准艇子进淀。马达循序渐进地隆隆响起,惊飞了树梢头的几只水鸟。它们用富有经验的表情和动作,盘桓在头顶,送我们离开这一湾浅浅的港。此时,我便在那白洋淀的水上,便在孙犁笔下浮着荷香诗情的白洋淀的水上了!
水面只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船夫稳稳地坐在船尾,他无需发力,这艇子就像拧满了发条,一蹦一颠地骑在浪头上,生气十足地向前欢奔。泖的风潮凉但不阴冷,猛烈地迎面驰来,擦着耳郭骋去,发出哗哗的笑喊声;也带着清香味,吹进我久居城关干涩酸疼的眼窝,穿透我总在澎湃着的尚未衰微的胸膛。大水无边无际,笼在茫茫雾霭之中。渐渐地望见了芦苇丛,先是淡淡的几排,越往深处去越浓,待船转一个弯子过去,就是别样的一重景致——密密层层的芦苇荡,全然跳现在一派苍茫之间,活如雁翎队的水丈夫,身子扎在水里,头却顶起了一个天。船窜进了苇丛,葱黄的苇叶摩擦着船舷和手臂。我仿佛听到风中芦苇的歌,那灵魂深处疼痛而快慰的歌。我听到鸬鹚清高的长鸣,含着对人的几分哂笑。我吟味着淀水赋予的撞击和抚慰,全然消隐在这湿漉清凉的苇香深处了。
却忘了一桩:母亲想看的荷花。
便问船夫:几时可以看到荷花。马达的吼声太烈,吞咽了这一声稚气的发问。我向他挥着臂膊,撕扯地喊:“荷花在哪里?我们想看——荷——花!”船夫这回是懂了,嘴角却显出一抹不可捉摸的笑意,怜悯地说:“这时节哪还有什么荷花,该败的都败了,只剩一些残菏,前面就有大荷塘,就能望到了。”
这回答并未使我多么突兀,却仍感到悲伤。我无辜地抗议道:“网上说黄金周荷香飘十里,冲着这个才来的。”
船夫有些歉疚,安慰道:“苑里还有一些睡莲可以看。”
他所讲的苑,料定是白洋淀文化苑,我是有听闻的,苑里有人造的嘎子村,有人造的康熙水围行宫、沛恩寺,有人造的雁翎队纪念馆,还有人造的金牛、荷花淀碑——却成了白洋淀最大的景点,游来必去的。无奈,只为了那些养在盆中的睡莲——那亡去的荷花的姊妹,我决意流一次俗,带母亲去。
“还有哪些好景致?网上说,这时候芦花飞絮……”
“你们来得不巧。”船夫叹息说,“前天夜下突降了一场霜冻,许多苇竿子都被打折了,花穗子也都蔫下去了,飞不起来了,你看——”他指向擦肩而过的芦苇丛。
我未曾见过芦花。经他一指,才知那些苇尖上低垂的穗穗儿就是芦花。它们果然刚刚经受了一场劫难,耷拉着黄央央的头颅,有的脖子已折断,漂浮在水面上,被风吹得一颤一颤。哪里还有几分花的样子呢!我不再发声了,更不去看母亲的眼。一片汪洋浩瀚的大水,顷刻间流成渺渺的悲怆。本想是带母亲来看荷塘,看那一望无边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铜墙铁壁一样。本想是看歌里唱过许多回的芦花白芦花美花絮满天飞,千丝万缕意绵绵路上彩云追……
却是个残花时节。
这时母亲开了口:“这若是花开的季节,该有多美!”她沉吟了一会儿,接续道,“花和人一样,过了季,就得歇着。咱们明年花期再来,看它们开得最好的样子。”
我回过头去,见她仍瞭望着无垠的水面,满足地吸着淀风。她出了神,神采里却没有黯然下去的迹象。一时间,恍然有成片雪白的芦花随风飞起来,漫天遍野都是,落在她的鬓角和额前,在水乡的晨光里,白亮亮地扑朔着。在我的记忆里,那白得刺目的分明是未折的芦花,却不是母亲的白发。
回到雄县时,人都有些乏沓。在小城仅有的清真饭馆要了些小菜,就盘算着回老家。那日正逢中秋,天津的表哥来短信邀我们过去团圆。想来母亲也是倦了,这节令做旅人确也不好,便不多思忖,见直达天津的巴士就登上去,并不觉得索然。无根的人,愁肠是无法言述清楚的。这些年来,我坦荡地把沧州挂在口边,一副熟络的样子,却不知,唯五年前去过那么一回,鸭梨、金丝枣儿都未入过口。亲脉倒攀得上的,走动实属不多,连祖父都如此,那感觉终究像是异域。游子有心念着乡情,可回去访哪些人,做什么事,竟没有一个主意。真到要去时,忽然寻个由头绕离而去,倒像是解脱了。
现世的事,本就是玄妙莫测的。
才到表哥家宿了一日,吃住都丰美,却硬是坐不住了。赏花的季节不复,故乡这枝花却逼真又羞怯地开着。我对母亲说:“你在天津安心歇着,我去老家访上一两日便回来接你。”我先前是想带她同走的,这会儿却觉得如此辗转对她未免残忍,况又无什么赏玩的去处,便真心劝她不要腾挪。母亲的倔劲儿却来了,执意随我同去。她的神采依然不显得疲怠,倒像得了一封喜令。故乡这把情做的刀,在我心头已挥砍得钝了,但在母亲那,却似才出刃,新鲜地灼着光泽。她分明比我还想回去的,仿佛那里有未败的鲜花,又仿佛多年前遗失在那里的名贵物事到了追讨的时候了。
对于沧州,我没有留下深的印记。五年前只顾着跟族兄约谈,没有细察风土。只觉是中土回回的重镇,教门①繁茂之地,便与西宁、固原浑然联想在一起。“这回可要掉进老回回堆儿了,遍地都是清真馆,想找汉民都难。”火车上,我已绘声绘色地向母亲描述起来。我讲话总不免夸张几分,往往要打八折来听。这次的折扣却要多了。出站一路西去,穿街走巷,直待潜入灯火通明的繁华街区,才寻到一处涮串的铺面,涮些鸡串牛排蘑菇充饥。我自然错愕了好一阵儿,仿佛一只闻花的鼻子染了风寒,什么也闻不到,却淌出一挂清鼻涕来。念起祖父幼年记忆中处处有白帽子①的老沧州,只觉得斑驳而茫远,匿在梦境深处罢了。我自知夜路难走,没有找对地方,若问好路,径直扎到回民区去,便不会是这番景象。不承想,母亲却惦念在心。翌日一早,她竟劝我不要急着回泊头,仍希望走走沧州城:“一定有回回堆儿,我们去找找。”我心里微微一惊。
我们所居的边城,族人是少的,除少数清朝发配的流人和西北商客,几乎全是闯关东过来的穷苦人。他们像芦花一样被风吹散,迫降在寒峭的北国;有一些赶上霜冻,干脆飞不起来,连着苇竿子一起,折在那水上。他们离回回堆儿的看守远了,但对同胞的念想总是浓酽的,如同在冰天雪地想念一个围炉取暖的旅伴。那种紧密、细致的感受,是无法言述清楚的!母亲对故土一无所知,她只是预感这根系所依的土地,该有别样的一重景致,该有苍劲的古寺、清真巷陌,有未曾见过的小吃。她想找找这一切,且当了一桩肃穆要紧的事,为此还有些焦灼。前些年同母亲出游时,她还不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大概只顾玩景了。
我暗自感慨,给族兄发信问路,不多久便潜入回民的巷陌腹心。密密层层的青砖院落,宛同一排排浩瀚的芦苇荡,户户门额上的经字杜哇②,多年来不曾凋残。临近晌午,小巷已有炊烟荡了起来,隐隐地漫着牛羊肉的香味,使我想念起祖母来。我说北大寺就要到了,我们快些赶吧。母亲嗯了一声,就加紧了步子。她的额上漫出了细密的润泽,面颊开成一朵红润的花。那娇小的影子在日头底下一晃一晃,显得很灵便,全然不像一个知天命已四载的女人。她分明不是自己在走,却像是风在助着走,这让我觉得她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回乡的路并不是那么好走的。
乘着巴士在蜿蜒中费了些时间,才到了泊头。大运河仍是一条枯涸的河床。乡人说冬月里河还会蓄上水,供给到天津去。我却不想见到那充填出来的丰润了。有水的泊镇,终归称不得水乡:那水中并没有容下荷苇的根。
时候还早,我们没有去亲戚家串门,见路旁有石家饺子馆,亲切异常,就进入坐。攀谈几句,居然远远近近都有些牵连。终归是无根的人,日日夜夜盼的故土归还了,仍像是无处安放的浮萍。现成的亲戚,竟不敢去登门探访,决意积淀一些勇气,晚间再去。这愁结是多么难述!母亲似乎比我更怕生,我们潜进一家客栈,很负重地睡去了。待到满盈的月亮升起来,更不好去搅扰人家,就这样搁下了。
再一宿过去,母亲已有了归意。
她是多么和蔼、温厚的一个人,总能同生人交往得喜喜气气,偏偏跨进故土的门里,倒觉得分明是异域了。我是很懂的,那感觉就像我童年时望着过开斋节①的清真寺②,来回进出的白帽子层层叠叠,却总觉得与自己无干;那扩音器传出的忧伤古调,像是隔绝我走进殿堂的布令。我也开始希望母亲不必再同我留驻了,大概还是天津好。我送她先回去,自己来走访吧。
母亲提出了唯一的希望。她只想走前看一眼泊镇清真寺。
那是六百多年前石家先人修建的一座古寺。
寺院里空荡荡,并无一人。我带母亲进来,背靠着花殿阁,看一块碑上刻着石家人斑驳的名字。母亲走过的清真寺不多,多半又被拦在外边,大殿是绝少进的。我特意把母亲领进了大殿,现在它仿佛不属于泊镇,却只属于两个无根的归客。后室殿的殿顶有一个六角亭,顶子用方木叠落成一方藻井。这式样在别地是没有的。母亲仰头望得出神,目光落在井外的天地里。
我沉吟着,该送母亲走了。出寺来,却没有见她。回身看去,她正向门栏外的木箱里塞着乜帖。我的心绪涩涩地荡漾起来。
后来的许多时日里,母亲常说起这次出行。她终于承认没留在北京看花车是多么聪明。她还说最吟味的一幕,是在游罢白洋淀回到郭里口的农宅以后。我也觉得那一幕最美,便只好留在末了来写了。那时我们下了快艇,总觉得兴致还没有尽。母亲望着码头边尘封的小木船,很羡慕地望着,仿佛那上面装着她的岁月。我便同房东租下了这只木船,请来一位老船工,重新下了淀。官家管的水域我们是不去的。这木桨儿,向着一方隐秘的水道摇去了。
哗哗——哗哗——
我听到水的歌吟了,清澈、安宁。这是真实的白洋淀的歌吟。
我不禁悸动起来,坐不住了。颤颤站起身,去接老船工的桨:“我划得来吗?”
老人笑而不答,目光像渺远的淀水。他默默扶我上了把位。小船又荡开了,钻过一座石桥,一片新鲜的芦苇荡在水道两侧壮观地铺满。那时已是后晌,阳光却如黄昏般恬静、柔和,衬着这些苇丛,有一股油画般的生动和浓郁。
母亲对老船工叹息说:“来得不巧,听说刚下了霜冻,连芦花都没有看到。”
船工却笑着摇起头来:“你们去的是大淀,无遮无拦的,风霜一来一定要受波折的。这边是避风的一处汊湾,花还在呢——”他示意我把船划得离苇丛近些。
近些,再近些。船舷擦过了舒长的苇叶。
我看到了,我们都看到了——芦花!
我摇桨的手停住了。我们错愕地看着这些艰难的生命,它们也显然经了霜冻,并没有盎然蓬勃的气势,却因为隐在水道深处,护住了几分元气,于是就比大淀的那些要饱满得多,精神得多。母亲赞叹说:“这些花开得多不容易,可是没有游客能来这儿看到,它们是开给自己看的!”风从西面吹过来,从苇尖上吹过来,带着一股眼泪般的咸味。惝恍间,几片雪白的芦花随风飞起来,洋洋洒洒,落在母亲的鬓角和额前。
我看得仔细,那白亮亮的扑朔着的分明不是芦花,却是母亲的白发。
原载《散文百家》2010年第5期
入选《2010年我最喜爱的中国散文10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