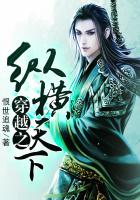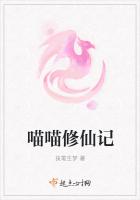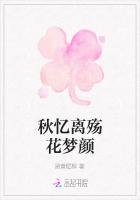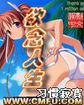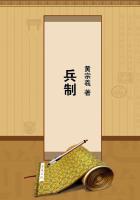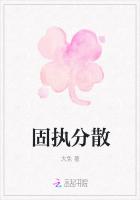1.乘风而上
在山东农学院进修结束之前,我不知道中国有个宁夏。在宣布分配方案之后,我才查看了新出版的《中国地图》。在祖国的大西北,有个叫做“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方。首府为银川市,这是我将去报到的城市。
我离家时,大哥让我带上大嫂二十几年前嫁到我家时的一件嫁妆——一个油漆剥落、旧得发黑、板子很薄的木箱。我有了这个木箱,感到莫大的满足。因为从出门念书以来,我的所有家当都是包裹在一个布包袱里,而这木箱可把衣物、零用品以至文具等都归整到里面了。尽管在那个年代里很少会看到提着皮箱上火车的人们,但我带着这又黑又旧的木箱,肩上还挂着一个布口袋式的包裹辗转济南、北京等大城市时,许多行人都对我投以不屑的目光,好像在说,这小伙子大概是去逃荒的吧。
我上了火车,一路孤寂,只能静静地品味离乡的愁思。渐行渐远,沿路的景物也常为这愁思增添一些凄凉。火车由济南向北经过德州一带时,连绵的秋雨竟使铁路两旁的积水如一片汪洋。在苍茫的暮色中,火车缓缓行驶在这“汪洋”里,令我提心吊胆,生怕有“翻船”的危险。德州地区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天不作美,这“汪洋”里的庄稼难道会有什么收成?经年饿肚子的农民恐怕连地里的野菜也找不到了。
火车离开北京向西,不久便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京张铁路是我国著名的铁路专家詹天佑主持勘测和设计的,火车为了爬一段最为险峻的山路,需有两个火车头同时拉动,在这山坡上的一个小站,矗立着詹天佑的铜像。火车停在这里二十分钟,是让旅客们瞻仰这位誉满中外的科学家昂首向前、指点群山的雄姿。我凝视着詹天佑的铜像,浮想联翩,这位科学家年轻时留学海外,历尽艰辛,学成后毅然归来报效祖国,设计并修筑连外国铁路专家都曾望而却步的京张铁路。他历久弥坚,排除万难,才会有这样的科学成就。詹天佑的博大胸怀和巨大成就激励着我,向前吧,我还年轻,初出茅庐应如初生之犊!
火车再蜿蜒西行,步步踏入荒凉,尤其自呼和浩特市以西,铁路两旁几乎看不到绿色。偶然见到几棵树木,树上的叶子几乎落尽。这里树木从主干到枝杈,一律倾斜向东南,像俯冲向前的战士。我纳闷不解,凝视窗外许久。呵,阵阵卷着黄土飞奔向前的西北风令我恍然大悟。这西北风!这西北风塑造了树木顽强不屈、勇敢向前的造型,也早早勾勒出黄土高原的秋色景观。时值八月上旬,刚刚立秋,山东老家正值“秋后一伏”时节,这里已是秋风萧瑟了。是啊,“春风不度玉门关”,秋风也显然是早起于塞外的。
再向西行,连这样的小树也见不到了。列车在平展的戈壁滩上行进着,两旁的荒野,连同视线尽头那依稀可见的山影,组成一幅迷茫、凄凉、悲哀的图画。凝视铁路近旁,不是铺展的沙砾,就是起伏的沙丘,沙砾上或沙丘之间可见一些稀稀落落的蓬草。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沙蓬。这沙蓬紧紧地贴在地面,高的不过半人高,带着沙砾的劲风把它们吹打成半球形。这一丛丛沙蓬犹如中流砥柱,顽强地与黄土高原上的劲风抗争着。
此时我的心境,随着黄土高原的景观由瞻仰詹天佑铜像时的兴奋荒凉了下来,我感到丝丝惆怅,些许哀伤,禁不住忆起王昭君出塞时的《怨诗》:
……秋木萋萋,其叶萎黄。……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
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
火车驶向西北,进入了地处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黄河后套地区,这里又是一种景观,平坦的地面上看不到沙砾和沙丘,而是白茫茫的一片,好像是均匀撒满了面粉的白洲。在“白洲”之中,可偶见耕耘过的农田,农田的边上,田埂上,也都是白白的“面粉”,还有稀稀落落的向日葵,有半人之高,面向东南弓背摇曳着。田地里的庄稼,低矮而萎黄,看不清是些什么。让人不解的是,两旁既看不到村庄,也看不到人影,这使得旷野更显荒凉;人们耕种过的田地也寂静地躺在那里,毫无生机。
火车离开这片白茫茫的土地,又进入了沙漠荒原,在这时,平坦的沙砾和起伏的沙丘,以及不屈的沙蓬已使我失去新鲜的感觉。火车继续前行,当我从昏昏欲睡中睁开眼睛,为之惊喜的是沙漠中出现了一条“小河”。我情不自禁地喃喃自语道:“这浩瀚的沙漠里竟然有一条小河”!这轻语触动了邻座的旅客,他为我更正说:“这不是小河。是黄河,中国第二大河!”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乘坐的火车要两次跨过黄河,这是因为这段黄河是呈S形在荒原中流动的。当火车从桥上缓缓驶过时,我看到这黄河不具流经山东济南河段的广阔汹涌的雄姿,只不过是几十米宽的波澜不惊的平静水流;当我再睹她的姿容时,她仍然是那样静谧,无声无息地在沙漠中穿行。我这才意识到,这里属黄河中游干旱少雨地区,如果有点雨水,这沙漠还不像海绵一样把它吸得干干净净,哪还轮得上流到河里去扩充水面?就是上游流下来的河水,恐怕也有相当一部分浸润到沙漠之中了。
我带着对黄河的留恋和沉思,进入了可见村落和树木的平坦地区。车上不少旅客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准备下车。火车上的播音员广播道:火车即将进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车站。我的目的地快要到了,不由得有些振奋,前面应是黄河平原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黄河百害,唯富一套”,这“一套”包括我前面经过的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后套,和我将要经过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所属的前套。前套的景观远胜于后套。她地势平坦,水渠交错,宛如蛛网;村舍星罗棋布,渠旁沟侧还有一排排茂盛的树木;更可喜的,还有望不到边际的稻田,田里的稻穗已显黄绿,稻穗下的叶子仍然葱绿,展现着盎然生机。村落近处还有不少的菜地,地里挂着殷红的西红柿、紫圆的茄子和青绿的长豆角。与小块菜地相毗邻的,往往有大片的白菜地和甘蓝地,地里的蔬菜清新而茂密。村舍里的房子令我感到奇特,是一排排的平房,这平房是规整的长方体,只在面南的一面留有门窗,除门窗以外的四周墙壁以及它的平顶都是黄土实体。我乘风而上黄土高原二十几小时,这才真正看到了她的黄土──将是我赖以落地生根的黄土。
这在我第一印象中十分奇特的黄土垒成的平房,还真与我结下了缘分。我在宁夏落地的前五六年,因为下乡带学生实习,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下放劳动等等,都是住在这黄土平房里。这土房是寒冷、干旱、多风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下的产物。它用不着高倾斜度的房顶以泻流雨水,脱粒之后的粮食如小麦、玉米、大豆等等都可以摊在房顶上晾晒至干。厚厚的土墙和房顶,使这房子冬暖夏凉,门窗虽仅仅开在南面,但西北黄土高原炽烈的阳光足以使房内十分明亮。
火车驶向银川途中的另一景观是大片的沼泽地以及与之相邻的茫茫白碱滩。这白碱滩的地貌与已看到的地处内蒙后套的景观是相似的。我问即将下车的乘客(我认为他们是宁夏人):这“银川”名字是否与这银白色的碱滩有关?有一位看来有学问的长者操着浓重的地方口音给我讲述了银川市名字的来历:
银川市位于银川平原中心。我们的先人远在秦朝已开凿渠道引黄河水灌溉农田,现流经银川平原的一条大引水渠就叫秦渠,但那毕竟是银川平原开发利用的初始年代。当时银川市周边有大面积未被开垦的白碱滩和沼泽地,尤在春季,由于土壤水分的蒸发散失,把随水上升的盐碱残留在地表面,愈发显得白茫茫的无边无际,银川市只不过是这白茫茫中的一点绿迹。这就是人们把这座边陲小城叫做银川市的原因。
我听了这位长者的讲述,顿觉长了见识。这塞外都有这般悠久的历史,祖国文明史的久远和辉煌实在是令人骄傲的。
关于银川市名字来历的另一种说法,是到20世纪90年代我才听说。这种说法披着神话的色彩,相当迷人:有一只银色的凤凰,由我国秦岭一带展翅北翔,飞到银川平原时,俯视这茫茫荒原中的一片绿洲,水渠纵横,阡陌交错,绿树成荫,瓜果飘香,好一派美丽无比的江南景象。她大为惊奇,无比欣喜,就停落在这平原中心的银川市,并定居了下来,所以这银川市又被叫做凤凰城。20世纪90年代,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地处边塞的银川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科技不兴,经济落后,人们为了振兴宁夏,发展经济,想尽法子宣传宁夏、打造宁夏,借以扩大宁夏与内地的交流。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文人墨客们编撰了上述神话借以提升宁夏,还是我孤陋寡闻不知早有这般神话?反正神话都是由人们编撰的,不管早编迟撰,编撰得好就可以流传,甚至可以成为经典。
我是1961年8月12日到达银川市的。我按照带的介绍信到农业厅人事处报到,并被安排在农业厅招待所等待分配。我赶着报到时间提前报到,是这批人最早来报到的之一。我一等等了35天,由农业部分配来的各省的支边进修班的人们才算陆续到齐。我们这批包括了农学、遗传育种、林学、水利、畜牧等各专业的进修毕业生共45人。但当时的宁夏农学院规模小,用不了这么多人,又赶上了1961年的“调整”,将与宁夏医学院、宁夏师范学院合并成立宁夏唯一的高等学府——宁夏大学。农业厅宣布分配时,只25人留到了学校,其余20人则被分配到农业厅、农垦局、农科院等单位。我被分配到农学院,但这时的农学院已摘掉了牌子,在校的学生已搬到尚未正式成立的宁夏大学去上课了。
2.落地生根
我落地生根的地方是地处贺兰山东麓腾格里大沙漠边缘的荒漠沙滩。即将成立的宁夏大学选址在这里。一颗种子如果落在肥沃的土壤上,必将很快发芽并茁壮成长;而如果飘落在贫瘠的沙原上,则需经百般周折,千辛万难才可有幸得以发芽和生长。
宁夏大学由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所创建的三所学院(宁夏师范学院、宁夏医学院、宁夏农学院)合并而成。初建时,利用了原宁夏师范学院的校舍,宁夏农学院舍弃了位于银川市老城西门之内的校址,首先迁入师范学院。位于银川市南门外的宁夏医学院虽也并入宁大,但不搬迁,只在“调整”的要求下缩小规模,以“宁夏大学医学系”保留在原址。据说这是因为医学院的院长不仅是宁夏唯一的二级教授,还是老革命,有在延安的革命经历。他坚持并校不搬家的理由是,宁夏医学院的实习医院不能搬到当时人烟稀少、城里人去看病很不方便的荒漠边缘。这位院长的真知灼见和敢于抗争,为宁夏医学院的过去和现在(已升格为宁夏医科大学)立下了不朽的功劳。
我到当时的宁夏农学院报到之后,被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整理实验室和搬家。那时的农学院是刚从银川农机学校分离出来而成立的,还占有农机学校的一座楼,家底很薄,没有几件贵重的仪器设备。我们把它们整理装箱之后,连同实验台、桌椅之类都搬走,没出半个月就把实验楼搬得空空如也。因为学生们正在上课,参加搬家的都是青年教师。那时仍属“三年自然灾害”的“低标准”时期,虽然肚子是空瘪的,但因为年龄的优势,以及刚落地、要生根的缘故,我们干起活来还是尽使力气的。
当时的银川市,人口不过10万,地盘却大而分散。她的三大部分自东向西一字儿排开。老城位于东,古老而繁华;中间是新城,只有新建的一条大街;新城之西是新市区,人烟稀少而荒凉。新建的宁夏大学位于新市区的西侧,距老城25华里,有一条公路经新城通向老城,这条公路是石子铺就的,路面像搓板,被称之为“搓板路”。这条路上的公共汽车每两小时一班,又很不准点,等两三个小时是常有的。坐上了汽车,路面上扬起的尘土通过振得哗啦啦响的破门窗的大缝子进来,很呛人。下车后,得好好拍打落得满身的尘土。不过我们搬家时,没有福分能坐上这样的汽车。我们把物品装上敞篷卡车,还需站在车厢边内照顾车上的东西。一路上,那才是真正的“风尘仆仆”。特别是遇有急刹车的情况,车尾扬起的尘土猛扑上来,我们个个蓬头垢面,满身黄土,只有牙齿还是白的。可当时我们并没把这当一回事,还开玩笑说:“在人类的各种营养成分之中,我们最不缺乏的是矿物质。”是的,只要上下牙齿稍稍相对,就会发出咯噌咯噌的响声。搬完实验室的东西之后,洗去了浑身的尘土,我们在荒滩校园里住了下来,并有了闲空去欣赏我们即将在这里工作的新学校。
初建的宁夏大学,只有四座楼零散地坐落在沙滩上,较大的一座是办公兼教学楼,四层,中间的一小部分为五层;用红砖砌成的一座三层楼,叫大红楼,里面全是教室;与大红楼遥相对应的是三层的小红楼,作为男、女生的宿舍;还有一座青砖砌成的拐角楼,主体南北走向,楼的北端向东拐弯,单身的男女教师和部分刚结婚的小两口住在这里。(这拐角楼保留至今,已成为宁夏大学的“古建筑”,从宁夏大学调走的教师们作“怀旧之旅”时,必定瞻仰)。这四座楼房之间仍残留着起伏沙丘的踪影,学生们从大红楼去小红楼宿舍时,中间要翻过一道沙岗。除这四座楼,还有好几排用青砖砌的窑洞,学校的一些领导和拖家带口的教师们住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