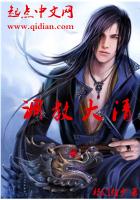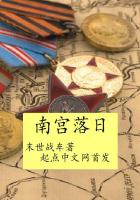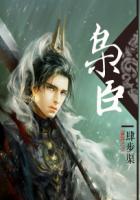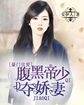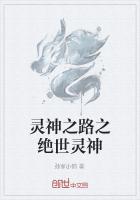1.童真无邪——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时光
我的启蒙教育,是从上私塾开始的。
早在我开始念书之前的1935年,南京政府已明令各地取缔私塾,但我国各地仍有私塾存在。我上的私塾,与清朝传统的只读《四书》《五经》,赋诗填词,学习八股文的那种私塾迥然不同,已经是以识字、学算术为主的新学堂,但仍由私人开设并收费,还保留传统的对学生的教学方法,所以村里人仍称它为私塾。
我父亲在村里人缘好,不光被称为“尊长”,还被推为我们村私塾学堂的“学董”。他与私塾先生是好朋友。我家兄弟四人,还有二姐,都上过私塾,但这不是因为父亲与私塾先生的关系好,是因为我父亲对于识字、记账的渴求。
父亲给各家做的木匠活,有的给现钱,有好多是赊账。赊账的大件(如车桩、车轮)好记,而换一副车耳,一根车轴,钱少,户数多,太难记了。他不识字,不会记账,全凭脑子记。他的记性很好,从没有记错过,但这太费脑筋了。所以他让我家每个男孩子都去私塾念书,要求不高,能识字、记账就行了。我的三位哥哥都念过四五年书,记账当然不成问题了。到我二姐,一则是我父亲思想变开通了些,再是因为“学董”的地位,就让她也去念了,成了私塾中唯一的女生。她去念书时我才5岁,也跟着她凑热闹去了。
记得去私塾的第一天,父亲正坐在讲台旁的一张桌子边与先生喝酒,他还把我叫上去,给我喂了两块肉,然后先生给了我两张纸片,一片上写了我的大名,就是现在我的名字。这大名,是区别于小名(又叫乳名)的一生中要用的正式名字。那天我非常高兴,因为从这天开始,我就有大名了,这大名是由先生给的,非同一般。另一张纸上写着“人、手、足、刀、尺”五个字。这五个字连同自己的名字,便是我最初认识的八个字。
上私塾新鲜了几天之后,我开始领教私塾的严规。那时的私塾,一、二、三年级同在一个教室里,老师教一年级时,其他年级的学生默写生字或背书等;教二年级时,别的年级也一样。我年龄小,不太会写字,默写困难,不会默写的字,都是二姐在石板上替我默写出来,再交到老师那里。默写能混过去,背书就难了。不会背,要挨板子。打板子时,老师抓住学生一只手的四个指尖部分,用板子狠狠打在手掌上。背书错得多的就打得多,打得狠,手掌会被打得肿起来;错得少,就少打几下,打得也轻。我也挨了几次打,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小,又是“学董”的儿子,我把衣袖衬在手掌上,老师没吭声,打得也不重。这个私塾分低年级和高年级两部分,高班的那位先生可严了,如果哪个学生不会背书,特别是趁老师不在时调皮捣蛋了,打起来特别厉害,只听得“啪啪啪”的响。有时还把学生按在凳子上,老师用一只腿压住他的脖子,板子打在屁股上,屁股肿起来,不敢坐凳子。
我在私塾里只念了一年,私塾就被废止了。又过了一年多,我们邻村开了一所小学,我去上一年级,这就是受日本鬼子侵略时的那一年。从日本鬼子投降到1946年土地改革后,这所小学搬到我们村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家大院,我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念到小学毕业。
在本村念小学的那几年,我尽情地享受着童年的快乐和幸福,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时光。胶东是老解放区,当时我们天天唱着一首歌曲: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人民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呀呼嗨呼嗨,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在解放区喜气洋洋的环境里,学校老师不打学生,以及温馨的家庭生活,让我们这些儿童自由自在,就像生活在天堂里。想来,那时的天空特别地蓝,蓝天下的白云舒展而悠闲,树木和庄稼都吐着嫩绿,人们的笑脸就像山花一样的灿烂。春天的鸟语婉转动听,夏天的倾盆大雨也下得痛快淋漓,我们相好的几个小朋友爱在大雨里光着脚跑来跑去。秋收时,新鲜的玉米、芋头、红薯等,让我们天天感到新鲜;上学时,有时也带上点,下课时你争我抢地分着吃。下午放学了,又轮流到各家菜园去,或摘黄瓜,或拔萝卜,再不就掐两根韭菜,也从不洗,用手撸一下泥,张口就吃。
我班的同学差不多都比我大,开始我学习并不出众,但到了高年级,我虽不是全班拔尖,却轻松自在,什么功课都难不倒。教算术的老师特别喜欢我。他爱出一些难题,让学生们到黑板上演算,叫做“爬黑板”,一般选学习中等以上的学生去爬。这既是对学生的一种测试,也是一种鼓励。老师总在别的同学在黑板上演算不出来或是题特别难的时候,把我叫上去。也不知哪来的那股灵气,我爬黑板从未出过丑。有时上黑板之前还不是很有底,上去之后,却神思泉涌,很快地演算出来了。老师对我的喜欢好像过头了,因为有些我本不一定做得好的事,他也让我出头露面。例如,那时每天上完早操时,各年级要集合在一起唱歌,他也让我上台先起个头,再打拍子指挥。有一次,全校年级间讲演比赛,他也非要我上台讲。他把稿子写好,让我背熟。可是在讲演之前,刚好我嘴巴上起了口疮,又蔓延到下巴上,我家不知用锅灰调了点什么药,抹在嘴边和下巴上,活像是大胡子。我对老师说,看我这样子,换别人上台讲吧,他还是不同意,我只好上台。我在台上只顾紧张地背台词,并按他教我的手势,一会儿摆一下左手,一会儿摆一下右手,不敢往下看,心想同学们一定觉得好笑。
那时的小学,也上晚自习,叫做“念灯书”。灯是自己带,一般是两三个好朋友同带一盏灯。那时的煤油叫“洋油”,很贵,所以我们都用豆油或花生油灯。那时的火柴叫“洋火”,我们每天晚上拿着油灯和“洋火”上学,在荧荧灯光下念书写作业。老师并不坐在教室里,只常来检查,老师说“放学了”才能回家。
我念小学时享受着老解放区安乐幸福的生活,但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在进行殊死较量。那时正在鲁西南、苏北和河南一带打仗,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淮海战役”。我们村很多20多岁的青年都当了解放军。记得那时常在后街正中的广场上扎戏台演节目,最有意思的一个节目是活报剧,演的是“小丑蒋介石”,道具是一株挂满桃子的桃树,蒋介石在桃子熟了的时候从峨眉山上下山摘“胜利果实”,解放军把他赶走了。戏演完了,台下党的工作人员动员那些二十岁左右的贫农子弟说:“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土改中分了房子又分了地,生活这么好,能把这胜利果实让蒋介石国民党抢去吗?”这时,戏台上已经有人戴着大红花带了头,他们在台上喊着口号:“打倒蒋介石!”“保卫胜利果实!”“有种的跟我来!”于是呼啦啦的一大片,小青年们都上了台。然后,这一队人骑着大马或骡子,戴着大红花,浩浩荡荡,从后街到前街,再转到大后街游行一圈,他们就光荣参军了。
因为我家的成分是中农,没人动员我大哥、二哥去参军。但他们都自愿上前线抬过担架。我家离济南市800华里,从济南转向南边到淮海战役的战场,1000多里,都是扛着担架、带着行李和干粮步行,要走半个多月,很辛苦。到了战场,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抢背伤员,抬下战场。他们在鲁西南、河南一带呆了一个多月,加上两头走路,两个月后才回到家。我大哥还没回来时,我二哥已出发了。那时抬担架的人是分批轮换的。
因为我在小学里学习好,老师喜欢,常指挥全校同学唱歌,算小有名气,在村里也被选举为儿童团团长。不过,这已是在共产党解放区蓝天白云之下的儿童团,没有做过像电影里演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那样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用“消息树”报信等活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拥军优属。每天下午放学之后,先不回家,我把同学们分成小组,再把校外的儿童(他们也可以加入儿童团)叫上,常是四五人一伙,分头到各军、烈属家中,给他们打扫院落、抬水、清理畜圈等。每家军、烈属街门框的右上边都有军属或烈属的牌子。我们村的军、烈属多,我们每次行动只集中在一条街(村里共有三条大街)。那时我们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在村里是文化人了,所以还常给军属家写信,寄给在前方的儿子。我当儿童团团长是在1948~1950年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时,到我上初中后,就换他人了。
到了1950年,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去,不打仗了。我也安安稳稳地小学毕业了。毕业考试那天,六年级的学生是坐在大操场上考试的。先排好队形,再每人张开双臂拉开距离,前后左右都是两个臂膀的距离。我们盘腿在地上坐好后,老师把抄有题目的黑板抬了出来,放在前面。我们坐在泥土地上,答卷纸下衬着硬纸夹子,用铅笔答卷。语文题是作文,算术题也没难倒我。我属于最早交卷的几人,交卷前,老远斜看我二姐,她皱着眉头在思考,估计会有几道难题做不出来,我偷偷把后面的几道难题的答案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揉成团,交卷时路过她身旁,把纸团扔给她。上私塾时,我二姐帮过我,到了小学高年级,我的学习比她强了,常常帮她算题。其实我二姐并非不聪明,但她在家中只比我大,从小也很娇惯。她很好玩,还常与村里的女孩子们参加演节目,用我三哥的话说:“太疯了,学习不专心。”
小学毕业后,我想上中学,但对考取中学并没有抱大的希望。因为村里比我大的孩子有的考了几年、好多次,都没有考上;其中有个比我大三岁的,已经考了七八次,都没考上。那时解放区的学校刚成立,有初等师范、初中等学校,分夏季和冬季两次招生,考试的时间由各校自主决定,所以夏季和冬季都可考不同的学校。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投考莱西一中,把四天的干粮和咸菜放在一个柳条篮子里,上面盖块白布。因为是夏天,行李只带了晚上盖的一条布单子,还有一个喝水的搪瓷杯子,与邻居家的一个男孩结伴,高高兴兴地上路了。与我们结伴的,本来还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他临走时,提了一下带干粮的篮子,觉得太重,路又远,吓得哭了起来,不敢去了。
当时的莱西一中位于县城东北的义店,离我们村有60华里。我俩是第一次出门远行,朝着大体的方向边问路边走,从大清早出发,到太阳离西山还有一竿子高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学校的身影。因为我们早就听说过,这所学校有一座二层小楼,是全县唯一的一座楼。那时的农村孩子,从未见过楼房。当我俩远远望见这座小楼时,把篮子放在地上,高兴地跳了起来,并在附近找了个高一些的地方瞭望赞叹了半天,然后抱着“赶紧走,看小楼去”的愿望又飞快上路了。
一到学校,只见考生云集,熙熙攘攘。这可把我俩吓坏了,就招100个学生,这么多人来考,我们能考上吗?我俩木木地在那里站了半天,我推了下同伴说:“考不上拉倒,先去看小楼吧。”
歇了一夜,第二天,不管有没有希望,我俩参加了考试。考语文和算术,上、下午各一门,一天就考完了。考后第二天,每一个考生都要经过面试。面试男生的是男老师,要求把裤子脱下半截,后来我才明白那大概是为了看看是否有疝气。然后老师要问一两个问题,我被问的是最简单的问题:你家里有什么人,几亩地等。我入学后才知道,一个同学曾被问了一个怪问题:“你上小楼了吗?”“上了。”“楼梯共有几磴?”这个同学当时只顾高兴地爬楼梯,没有数有几磴,没答上来。不过这并没影响他被录取,因为面试可能只是为了看学生是否口吃、反应是否迟钝等。
面试完了,还要等两天后看榜。因为考完试老师就批卷,接着就出榜公布。我俩去看榜时,是从榜的最后一名向前看,看到半截还没有我俩的名字,我说:“走吧,没考上。”忽然,我的同伴惊喊起来:“呵!那不是你的名字!在前面!”我一看,果然,我是第七名。我高兴极了,打算立刻回家,告诉家里人。但刚离开不多远,又不放心:录取的是不是我?有没有重名的?又回到榜前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恰好这时有几位老师就在榜前说话,有一位老师说:“包括王世敬在内的这七名考生,每人的平均分都在85分以上。”另一位老师说:“考生太多了,平均二十几人录取一个,太难了!”我一听老师的话,更加高兴了,我不光考上了,还考了个第七名,85分以上!
回家的路上,不时的一溜小跑,虽然干粮和咸菜都吃光了,肚子有些饿,可一高兴,一点也不觉得累,太阳离西山老高就回到家了。知道我考上了,全家比过节还高兴,我们村里的那些同学,同年级的、高年级的都来了。他们都替我高兴,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消息传到前街的西南角,我本家未出五服的五叔住在那里,他识字,算是村里的“学问人”,也有点孤傲自赏,平时不多来我家。那天他挺高兴地来了,坐了一会,把我叫到一个无人的房间里,他在一张纸上早就写好了7个字,拿出来让我念给他听。我一看,写了7个一样的“朝”字,我当即没打一点磕,脱口念道:
朝(zhao)、朝(chao)、朝(zhao)、朝(chao)、朝(zhao)、朝(zhao)、朝(chao)。
我念完了之后,五叔只说了一个字:“行!”就兴冲冲地离开了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