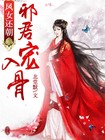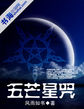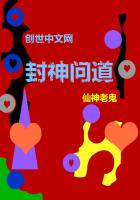我一直对诗歌有着一丝眷恋,因为年轻时写诗,今天又因为诗歌而品味到了年轻——英隽的诗集《雨自贺兰》又让我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了。
当然,诗歌不是青年人唯一的选择,但若青年时不写诗,对一个人来说,些许有些遗憾。
塞上宁夏曾是边塞诗的发源地之一,从唐太宗灵州勒石题诗,到大明宰相张居正的“一声羌笛吹关柳,万卒雕戈拥贺兰”,朔方的诗歌里张扬着西北人的气质和血性。可惜《诗经》十五国风中没有“朔风”,也不会有“胡风”。其实,赢秦和李唐都有些“胡气”。来自于胡地的诗仙李太白,其“十五游神仙,游仙未曾歇”的仙风里,确有着一股子“胡风”。
楚人宋玉这样讴歌大风:“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这是洞庭湖的湖风吧。
无论是“胡风”还是“湖风”,都那么有声有色、有形有种。
无风的日子里,《雨自贺兰》让我们感觉到了西北风的心律:
狂野的马蹄是风的心跳/刹不住脚的青草/把山,撞了个趔趄/天,眯缝着眼(《风之索》)
英隽的诗隽永着文化的张力,题材和风格不拘一格。《蹚过季河》清新、灵动,《喜鹊柴·喜鹊馍》于平淡之中余香绵绵,《无雪的冬天》《无土栽培的土豆》则发散着都市人的忧郁和朦胧。
组诗《塬上》——水与生命的组合,采撷“百井工程”“扬黄灌溉工程”的几簇浪花。其中,《水的情节》流淌着水的灵性和幸福。叙事长诗《苍啷塬》以真实的荒诞解读一个“草根”的价值困惑,带了点西北人所特有的冷幽默,你甚至可以用固原话来朗读它。
十四首《贺兰山岩画随想》,则展示出了一幅幅游牧民族的生活画面:
羊羔细嫩的叫声/霜晶般地明亮/女人如何让溪水平静/来映照自己的眼眉(《太阳是咸的》)
一根细长的羊毛线/挽结下了最后一个情结/黎明就缀在了/黑夜的后面(《等待》)
他是第一个用诗把贺兰山岩画写活了的诗人。
2011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