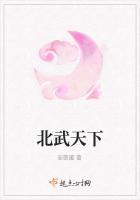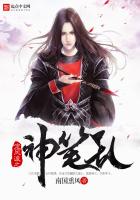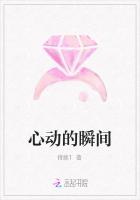第一节生产习俗
仡佬族所居住地区大都是高原山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条件决定了仡佬族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仡佬族历史悠久,同样也拥有古老的农耕习俗以及悠久的农业生产经历,是贵州乃至西南这片神奇土地上的土着民族。仡佬族人世世代代生活于崇山峻岭之间,山高坡陡,处处是未开垦的荒地。过去,由于耕作条件的恶劣和生产工具的落后,仡佬族人的生产方式也比较简单原始,他们通常在距村寨较远的地方实行刀耕火种,在离村寨较近的地方实行田园农耕,两种耕作方式并存。
一、刀耕火种
古老原始的刀耕火种,是仡佬族农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黔中杂诗》中叙述了仡佬族人“耕山到处皆用火”。仡佬族在荒山开垦土地时,先选取一块土地,砍去原有的植被,并用火烧掉,然后在土地上播撒种子,种植粮食,这种耕作方式也称为“砍火烟”。即使是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也有季节的讲究,有的是在春天进行,即砍即烧即种,这时候种上的是春夏季节播种的植物小谷、天仙米等。然而“砍火烟”主要是在农历六月进行,这个时候,气候干燥,草木长势好,易于用火烧,使土地更加疏松肥沃。到六月末七月初就可以种上一季荞子,还可间种萝卜或其他越冬的蔬菜。勤劳的仡佬族人在实践中总结经验,发现在初夏季节“砍火烟”的诸多好处。比如,这个时候正值农闲,不耽误正常的农耕,此时开垦的土地,到第二年春天正好可以种玉米、豆类等农作物,这样,秋季与冬季的农作物收成都很好。《宣德实录》中也有记载:“贵州所辖地方,悉是蛮夷,刀耕火种”,“刀耕火种,籽粒秕细,鲜有收获”。这种耕作现象一直沿袭至新中国成立后。
仡佬族生活的贵州山区,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处处是奇山怪石,很难见到大片的平坦土地,这一地理特征极大地制约了仡佬族的农业生产。俗话说:“高山苗,水仲家,仡佬住在石旮旯”,石旮旯中的仡佬族人严重缺少耕地,只能见缝插针,在石头缝隙里寻求生活的希望。凡是有一点能够生长农作物的土地,仡佬族人都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珍视土地犹如生命。
在仡佬族人生活的山区,岩穴、荒野和树林随处可见,也是各种野生动物频繁活动的地方,常常有野猪、虎、豹、熊、山羊、野兔、刺猬、豪猪、野鸡等兽禽出没。仡佬族人不仅要在艰苦的环境下开荒种地,还要时刻防范各种兽禽的侵扰,在长期与它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培养了优良的狩猎本领。仡佬族人狩猎出于两种目的,一是防止野猪、刺猬、猴等动物对庄稼的破坏;二是通过获取猎物,丰富自己和家人的菜肴。因此,狩猎也可以说是仡佬族人农业生产的一项补充,是仡佬族人生存必不可缺的世代相传的本领。他们常常在田地边搭上一个简易的“窝棚”,连夜看护,轮流值班,发现兽群便告知同寨人。在追捕猎物时,他们身手敏捷,步伐矫健,“依山走险,若履平地”,或群体围捕野兽,或用网、箭、铁夹、陷坑等多种方式捕获野兽。在大多数仡佬族村寨中,都有几个本领高强的猎手,称为“撵山匠”,有的一年能捕获野猪、刺猬、野兔数十只乃至上百只,成为以农耕为主的猎户。
生产条件的艰苦和生活的艰辛不言而喻,但仡佬人并没有灰心,为了生存,他们坚忍不拔,积极乐观,自强不息,在石山中寻觅有限的土地,寻觅生活的希望,用勤劳的双手生产劳动,创造美好的生活。
二、生产工具
由于仡佬族部分地区多为石山,土地稀少贫瘠,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的耕作器具显得古老和陈旧,为了适用于山坳石峡的“火石地”,非常坚固耐用,与平坦田坝地区其他民族的农具有一定的差别。
用于翻犁土地的农具主要是犁,仡佬语称“瓦”,通常是木制身架、铁制铧口,主件由犁底和犁箢以及铸造的铧铁组成,又分山铧和水铧。山铧的木架犁底无散板或散板较窄,铧铁呈等腰三角形,嘴尖微圆口,主要用来翻犁旱地泥土;水铧的犁底有散板,以利翻犁水田。由于山区地形复杂,根据不同的需要和其处地情况,山、水铧铁有的地方嘴尖呈结补状,弧度稍小,这主要根据土质或使用习惯而采用。
还有一种古老的犁称为“拖抬犁”,这种工具是伴随着仡佬族原始的刀耕火种而出现的。“砍火烟”的第一季,土地被烈火烧过以后土质很疏松,便于种植,但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土地变得板结了,需要借助牛犁耕作。但是在广大穷苦的仡佬族人家,不是家家都能买得起牛的,而且在一些陡峭的地形或犄角旮旯里的小块土地也不适合牛耕,于是仡佬族人发明了“拖抬犁”。实际上就是以人代牛,即前后两人,一人在后边掌犁一人在前边拖犁,前后两人拖抬翻转,所以得名“拖抬犁”。拖抬犁犁铧的形状与牛犁一样,略小一些,所不同的是牛枷担变成了抬犁杆。使用时,前边一人一只手紧握抬犁杆的前端,一只手反握住后边接近纤索的地方,使用肩膀的力量向前抵力,后边的一个人一手把犁铧,一手稳住犁杆,也用肩膀用力前抵,前后齐力,抬犁翻转。
除了犁之外,人们还用锄作为翻土的辅助工具,仡佬语称之为“波”,一般是仡佬族人自己的手工铁匠以熟铁烧炉锻打制作,其中用于翻土的称大锄,锄板长尺许,刃口宽三四寸不等;另外一种称薅锄,主要用来除草、壅土,铲除田土埂坎和地表的草皮,锄板前宽后窄,刃口一般在五寸至一尺左右,长五六寸,呈扇形或“凸字靶影”形;还有一种用于抓泥的农具,称耙梳,四铁齿并连套把,仡佬人主要用它来打“龙崩(埂坎垮塌)”、上田坎等。
翻犁好土地后,还需要有整地农具,仡佬族人主要使用钉耙,这种钉耙是由耙手、衬柱、耙辊子、耙鼓槌等木制件组成“Ⅱ”字形构架,在耙辊处安装八颗耙钉(有的为木制,有的为铁制),上面装有耙手,由农人双手掌握操作。两耙鼓槌系连枷担、纤索套在牛身上,主要是耙碎水田泥土,使之平整疏松。铧、耙是人工配耕牛劳役松土整田的主要工具,所以还附带有枷担、纤索、牛打脚配套使用。
到了农作物收获的季节,最常使用的收割工具是摘刀,主要用来收割粳稻。摘刀是在一种短梳形木板上面嵌上刃长5厘米,宽1.5厘米的小刀片,在小木板中段边缘穿一根带子,使之夹在中指与无名指之间以便一株一株地割稻禾。后来,随着粳稻普遍被黏谷代替,摘刀也就逐渐不再使用。还有一种普遍使用的收割工具是镰刀,普通镰刀长25厘米,刃宽5.5厘米,木柄长36厘米,装上木把,主要用来割稻、麦、包谷秆、青草和茅草。
在农作物经营管理和抗旱保苗方面主要使用的工具有龙骨车、水车、戽水篼、扯水筒等,与当地其他兄弟民族类似。农作物收获贮存盛装工具主要有挞斗、挡席、围席、软包箩、晒席、箩筐、撮箕、簸箕、风簸等,农产品加工工具主要有水碾、碓、磨,也大致与其他兄弟民族所用相同。
仡佬族人耕作的条件非常艰苦,他们所开垦的土地常常离家较远,因此他们需要有劳动时用来护身的用具,最常见的是棕制的蓑衣,有大蓑衣和蓑衣褡儿两种。大蓑衣是在田间地头干活时用来防雨的主要器具;蓑衣褡儿是一种矩形的负背,在背重物时用来垫背防磨,同时也有防雨的功能。还有一种圆形尖顶的斗笠,用丝篾穿编两层,中间夹一层皮纸,再喷上桐油制成,既可防雨也能防晒。此外还有一种用几层布纳成的环形罩肩,称为垫肩,主要用于挑背重物时减少背系或扁担对肩膀的摩擦。
由此看出,仡佬族祖祖辈辈使用的生产工具是极为简朴落后的,然而他们正是用这些古老原始的农具开辟了贵州乃至更广大地区一山又一山的土地,打下了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受地理环境等因素的极大制约,即使是在现代化农业生产迅猛发展的今天,仡佬族人仍然普遍使用着这些古老的农具。
近年来,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仡佬族人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科技知识的传播,广大仡佬族地区普遍进行了农田水利建设,兴修了若干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并推广了实用的农业新技术和农作物优良新品种,对烤烟、油菜、花生、茶叶等经济作物也有大规模的种植,并有效消除了病虫害和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生产的影响。仡佬族人民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农副产品,不断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一步步走向市场。
三、二十四节气和有趣的农谚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代各族劳动人民独创的文化遗产,是我国几千年农耕文化中的精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和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及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把一年平均分为二十四等份,给每等份取了专有名称,就是二十四节气。仡佬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积累了丰富的耕作季节性规律,对时令节气十分讲究,全年的生产都有计划地进行。
正月立春、雨水与数九。立春预示着进入春季,万物开始复苏;雨水则指春风遍吹,冰雪融化,空气湿润,雨水增多。这时候,仡佬族一些地区有这样的农谚:“春打五九头,十圈老牛九圈愁;春打五九中,十圈老牛九圈空。”主要指来年收成时有阴雨连绵的气候出现,这样稻草、玉米草就不能晒干很好地保存,所以牛在第二年冬天过冬时会因为没有充足的草料而瘦弱死亡。雨水节前后,人们便要整修农具,贮备柴火,翻犁田土,为春耕大忙季节做准备。
二月惊蛰、春分前后,农人们开始整土、运肥、种早包谷、修补沟渠。惊蛰指春雷阵阵,蛰伏在泥土里的各种冬眠动物开始苏醒过来,也预示着春耕即将开始;春分则是指春季90天的中分点,这一天南北半球昼夜相等,我国大部分地区越冬作物在这时进入春季生长阶段。仡佬族人在农历二月底之前,会准备好充足的肥料运到地里,农谚称:“正月二月不挑粪,三四月间拄拐棍。”意思是正月、二月如果不把肥料运到地里,到三月、四月农忙就会被动而耽误农时。人们认为惊蛰这一天要冷才好,如果天气暖和,则会有“倒春寒”出现;还说如果二月初二晴,山中的树皮换几层,也能预测有“倒春寒”天气的出现。
三月清明至谷雨节前后,气候逐渐变暖,是春耕繁忙的季节。这时候,仡佬族农人开始大面积播种包谷和各种豆类,育水稻秧和辣椒、土烟,有农谚称:“叮叮咚咚,谷雨下种。”育稻秧分两种:清明前后撒早秧,称“清明秧”;谷雨普遍撒秧称“谷雨秧”。仡佬族育秧的传统方法是:先用水泡稻谷种,三天后发芽,七天后撒在秧田里,隔四五天“晒水”,把秧田水放干使秧苗成长。用水拌清粪浇泼两次,作追肥。灭虫采取马桑叶灰追秧田,再用竹竿缠着马桑叶去刷扫秧虫。仡佬人有“清明要晴,谷雨要淋”的说法,诗文里描述“清明时节雨纷纷”,然而仡佬族人认为清明这一天要出太阳才好,否则在清明前播下的种子就会烂掉,即“清明不明烂早种”;而谷雨这一天则下雨为好,“雨生百谷”,如果天晴,在谷雨之前生长起来的秧苗就会因出现高温天气而死掉,即“谷雨不淋烂早秧”。
四月立夏小满节前后,农作物进入了旺盛生长的季节。在仡佬族地区同时也是收割油菜的时节,并要割压秧苗在水田里,整理好田坎,管理秧苗,薅包谷,打干田,保水蓄水。人们认为这两个节气都要下雨才好,如果天晴,则预示着有春旱气候出现,农谚有:“立夏不下,犁耙高挂;小满不满,干断田坎。”
五月芒种夏至节,芒种最适合播种有芒的谷类植物,如晚谷、黍等。农人们对播种秧苗的时间十分讲究,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农谚说:“芒种忙忙栽,夏至谷坏胎。”是指如果夏至前秧苗已拔节定型了,种下后再分蘖,影响产量,所以芒种前要“抢水打田”,不能急于栽种。又称:“芒种打田不坐水,夏至栽秧少一腿。”这里“坐水”是“保水”的意思,而所说的“腿”是指秧苗的分蘖数。在夏至过后栽下的秧子,由于在秧田中停留时间过长,密度又比较大,错过了分蘖期,移栽到大田以后,分蘖出来的幼苗大多数为无效分蘖苗,因生长期不足而无法在秋天结子,造成减产。所以农人们要在芒种前把稻田犁耙完毕,在夏至前把秧播完。
六月小暑大暑节前后,农人们要清除杂草,薅秧,看管水田,薅二道包谷。这时候是庄稼茁壮成长的重要时节,合适的降雨量也是农人们日夜企盼的,正所谓:“六月三场雨,瘦土出黄金。”
七月立秋处暑节前后,正值盛暑三伏天,要把牛关在圈中以避免它们破坏田里的庄稼,还要割青草垫厩积肥,勒黄豆叶以备冬季猪饲料,为秋耕、秋种做准备。
八月白露秋分节前后,要收获玉米、水稻和其他秋季作物。
九月寒露霜降节,该收获薯类和其他晚秋作物,并种植小麦、大麦、豌豆、胡豆,翻犁田土,农谚称:“九月犁田一碗油,十月犁田半碗油。”说明九月应及时翻犁稻田,使稻田在第二年更加肥沃并减少病虫害。九九重阳节,人们也希望来一场雨,有利于豆类的生长,农谚称:“重阳不打伞,胡豆光秆秆。”
十月继续种小季作物,收藏秋季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并翻犁完板田板土。
十一月,气候转冷,农人们要为小季作物追加肥料,这一时期还可以出售他们一年来辛勤耕作所获的农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