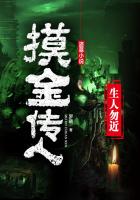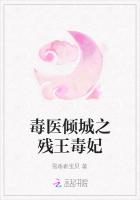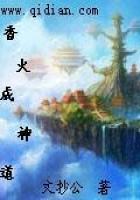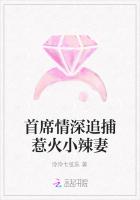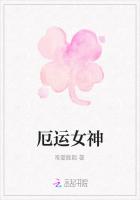姨妈盘腿坐在热炕上的小桌前,喝着温润清香的盖碗茶,和忙里偷闲的母亲拉家常。母亲端上烙好的油葱馍,炒两三盘拿手菜,还有爽口的米饭,一大碗炒鸡肉,这算是对姨妈的盛情款待。
父亲边吃边往炉子里添煤,时不时地插上几句。吃完饭出门给他那五十多只肉鸽撒些米谷,明天集市上他要卖掉那十对乳鸽。随后,他又给羊们添上些草料,它们安静了许多。
几只小羊羔兴奋地追逐撒欢。比母亲大两岁的父亲在雪地里咳嗽喘气,白帽下蜡黄的脸显出浮肿的病态,看羊吃草时有些呆滞的父亲,不知不觉中被雪装扮成白色。
清真寺里梆子响了,父亲上寺去了。老姊妹俩洗手后头遮白色盖头上炕礼拜,虔诚地面西叩首,心中怀着无限的崇敬,那一刻不容打扰。
雪停了,天色骤然放亮,太阳出来了,阳光穿过玻璃窗投射在老姐妹身上,暖洋洋的。
终于可以和白发的老姨妈坐在炕上面对面说些久别的心里话了。先说父亲的肾病、冠心病,我的残疾,再说我离婚后妻子丢下可爱的小儿走了,还有城里打工做生意的二弟三弟,出嫁的小妹,我家的收入来源……直说到夜深人静两眼犯困。
微笑芳香的死
人人都有花样年华,无可奈何花落去,一江春水向东流。
古语常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
还仿佛是昨日烟雨疾过,未等回味,今日又七十古来稀。明日虽“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将老去,不免喟叹人生短促,匆匆中口齿脱落,鬓生华发。诗人臧克家一首《三代》小诗写道: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人生就是一个洗澡、流汗、埋葬的过程。人只不过比花草树木多活若干个季节罢了,这是自然法则,任何生命都有兴旺、衰败的过程。出生与死亡的抛物线,就像上帝手中的魔棍划出的优美轨迹,多绕几下则长寿,少绕几下则短命。有辉煌的顶点,有暗淡的低谷。横坐标是喜怒哀乐,纵坐标是悲欢离合。纵横交错,点连成线,塑造人生。
人老了,总沉湎于旧事。旧事里盛装着年轻时的音容笑貌,旧事里记录着逝去亲友的举手投足。许多失眠之夜,旧事如幻灯投影般浮现眼前,萦绕耳畔,不免泪湿枕巾。人老了,特别是孤残老人,总孤单地寻伴恋子,就多拨几个电话,听听回音。做一桌饭菜,等儿女子孙们回家相聚。有时心里空落得六神无主,就只好陪着电视一会儿大笑,一会儿流泪。戴上老花镜,痴看尘封的黑白照片,蓦然回首,往事如浮云流水涌上心头。每逢佳节,就在门口眺望,像等着燕儿回巢。在外生活多年,身在异乡为异客,期盼落叶归根,死后埋入故土。
人老了,也许会怕死,会渐渐迷信起来。年轻时,总认为青春永远是葆鲜的,认为言死过早,一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傲慢模样。想想年轻时做过的好坏事,许多遗憾积存在心里,愧怍的事就会指责良心。信仰神主的人,就会向神主祈祷恕罪,做善事积德,施舍钱物积善,以求死后进入天堂不入地狱。
双腿瘫痪的北京作家史铁生坐在轮椅上终日都在生死圈里思考,他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和史铁生有着同样的人生磨难与不幸,而我却没有悟出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厄运惠顾善良,灾难覆盖美好,一切遗憾均在瞬间跌成碎片,我的人生从峰顶速滑谷底。欲哭无泪的残体,无端地进入与世隔绝的境地。我从此成了朋友间唏嘘哀叹失败的例证。我在失望的那段暗光里觅不出一道微小的可供呼吸的空隙。如今,我敬佩自己活下去的那份勇气,以及平静面对家庭变故和慈父病故的心态。
依托了那份伟大的母爱,我终于可以微笑着生活了。久积的伤痛可以渐趋麻木,不再无端地追忆自我的不幸与惨相,原来还可有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人生境界。我选择了“以文字疗伤”。母亲成了我的双腿,她的脚印与我的车辙覆合成我追逐理想的心路——成为我存活于世览胜的风景。我开始迟钝地感恩,虽报恩无力,却把四面八方春潮涌动的关爱沉淀心底。心壁潮湿时,就以一字一泪的笔墨向世人答谢。我深知我的无奈与无能。古人云:大丈夫难为妻贤子孝。我愧称大丈夫,不及古人今人半分,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苟活者,只能在消亡的时光中,做着别人不屑一顾的文学梦。
卧床十余载,身如枯木,关节筋骨变形。病痛习以为常,而身心愉悦,生命不息,就得珍爱生命,切莫辜负了盛世。活着是多么美好!
罗素在《论老之将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像河水一样——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在狭窄的两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渐渐的,河道变宽了,河岸扩展了,河水流得更平衡了。最后,河水流入了海洋,不再有明显的间断和停顿,而后便毫无痛苦地摆脱了自身的存在。
这种自然流淌、毫无痛楚的回归式的死亡,带着至高境界的美感,是一条奔流于理想天国幻化的河流。
我渴望死于尚能劳作之际,嘴角留着微笑,躺在花草上,芳香谢世。手里一支笔,还有一叠未曾写完的我之残缺人生的奋斗历程。
母亲的花儿
搬家时,母亲总是对那些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旧物拿起又放下,难以取舍。我知道,家里的每一件家什都存有我们的念想和情感。
母亲爱花,当然最舍不得花。搬走的十几盆花都不是名花,诸如绣球、吊篮、仙人掌之类好养的花。一楼光线虽不及高层明亮,却出行方便。我在电脑前摆放了一小盆抗辐射的仙人球,卧室靠暖气的窗台上选了一盆绣球、一盆文竹、一盆满天星。
绣球表达了我残存的爱情之心,依稀的梦中,还能再缘个向我抛掷绣球的伊人吗?文竹纤叶碧绿,碧盖之气直抒胸怀,是我追逐的翩然君子之性情。那满天星花开不败,几株枝杆上少叶而多小钟般灼艳的红花,每枝分三朵,每朵十几丛,每丛宛如满天星斗缀空,哪个是我的星座?细观颇有趣味。除了母亲每次松土、施肥、浇水时碰溢了绣球的娇羞之气外(有人说绣球的气味不佳,我说是女人的香汗味可妥?)其余两盆均无味。读书写作倦了,抬头看看这些花草,看它们温馨地沐浴在暖暖的阳光中,倦怠之气顿消,烦躁情绪忽静,思索之间,也是心花怒放了。
那次母亲有事出门几天,我却忘记吩咐小儿给花浇水。
母亲回家后,发现绣球叶黄花蔫,文竹也减退了几分碧色,而那满天星的盆中竟长出了豆角枝叶,嫩丝儿攀升于满天星花枝上,跃跃欲试。母亲惊喜地说,我随手种了棵豆角子,没想到花都开了,怎么就长活了呢?惊奇之余,母亲赶忙找来一根长长的白线,一头系在满天星枝上,一头系到屋顶窗帘的横拉杆上,再将豆角丝头剥离花枝,牵攀到临空的白线上,让它抽丝自由无阻地向上生长。
每天看着窜长了一截叶子和丝头的豆角,再看看那三盆养眼的花儿,我心里顿生感慨:这些年,母亲把我当花侍弄,昼夜精心养护,她就是想让儿子身残志坚,早点开花结果。感谢伟大的母爱!我在一首获全国征文奖的诗歌《旋转的母亲》中这样写道:早晨起来,母亲/在床与轮椅之间/——抱起我/划出几十道金色的弧线/每道弧线倏地就是一岁/我的衣服鞋子和牙刷/在您匆忙的手指上/完成开关的细节/——坐进阳光/我白昼的石磨/托着您长满鸡眼的脚旋转/碗里的奶香瞬间在您/额头的纹路里牵出一头奶牛/我变形的筋骨和身体/像您翻烙的烧饼/为了我不再被心火灼伤/花费了您没有完整睡眠的夜晚/母亲啊!/拿什么还您的感情债/我是您精护的花草/剪枝施肥又浇水/一切为了我开花结果我希望每天都能健康快乐。又在网上起了个“时刻上”的网名,也意为每天都像那棵豆角丝蔓一样,时刻向上,开花结果。
母亲的长发
母亲从来没剪过头发。她和许多乡村回族妇女一样遵循“青丝不见日月”的习俗。
母亲十八岁嫁给父亲后,两根粗黑齐腰的长辫子就藏在白帽里,一藏裹就是四十二年。
唯独在镜框的旧照片里,有一张母亲和两个邻居姐妹留着短发、胸前手持毛主席语录的三人组合照片。听母亲说,这是“文革”前期,为了响应社教运动,“破四旧,立四新”拍的。
小时候,我常记得母亲从生产队下工回来,不管多苦多累,先要烧锅热水,装满汤瓶吊罐,洗个澡。母亲用碱水洗头,再抹上用杏仁特制的杏仁油,洗过的头发又黑又亮,透着清香。母亲的长发真好看,用“流动的黑色瀑布”来形容,并不夸张。不一会儿,“瀑布”被梳成两根粗壮的麻花辫,对镜盘在头顶,用红头绳扎紧,再戴上白净的帽子。更换上干净的衣服,没了灰头土脸的模样,面目清秀地去做饭,洗衣,干杂活。土炕,土地,土院,总被母亲打扫得干净、整洁。邻居们串门,都夸母亲“细详”(爱干净之意)。母亲是最怕我们几个孩子身上头上生虱子,虽说那时肥皂供应紧缺,没有洗衣粉,更没有洗发膏,人们戏言:县长身上还生虱子呢!谁身上没虱子造反游行呢?可母亲总让自己和孩子在人前有个干净面目,作人更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
后来,我上学、工作、成家立业,在外奔波忙碌,很少近距离留意母亲洗浴过的长发。残疾后受恩于母亲的昼夜护理,与母亲朝夕相处,才发现母亲青丝渐白,从鬓角向头顶蔓延,而且大把大把地脱发。弟妹们心疼母亲,买来高级洗发水、护理霜、黑色染发剂,设法让母亲年轻,可儿女子孙们的烦心事太多,总让她的心清闲不下来。父亲病逝后,母亲显然衰老了许多。
每次看见母亲梳退下来灰白的长发放进一大塑料袋积攒着,从门外收购废品的那里换回瓷盆、碗碟、盖碗茶盅等一大堆物件,总有“春蚕到死丝方尽”的感叹;每次看见母亲从梳子缝里抠捋出脱发又装进塑料袋,再将渐渐枯瘦的两根灰白辫子盘在头顶,对镜微弓着腰身,用黑头绳扎好,戴上白帽,露出两鬓的白发时,我总提醒母亲说,妈,给你买回的染发剂你怎么不染?母亲说,哎哟,我忘了。
是的,六十多岁的母亲总是忘事。做儿女的,总希望母亲的白发皱纹慢点长出,从心里——让母亲离年轻近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