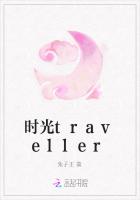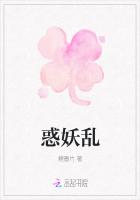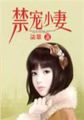那山那水那铁桥
青铜峡拦河大坝很巧妙地扼住黄河蛟龙之喉,犹如困兽野马的黄河水波涛汹涌,直奔不远处的黑舰一样嵌接在古渡口的黄河大铁桥。
黄河大铁桥始建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竣工。长二百九十三米、宽四米的高架固拉大铁桥,巨人般伸展着钢筋铁骨,承载着两岸的车水马龙,行人物资。
大铁桥为单行道,行驶的车辆每次只能单排行驶。每遇高峰时,两岸排起长龙蛇阵。道班两头电话相接,红绿旗子在守班人手中挥来舞去,风飘旗语,隔岸相悟。红绿灯有时就像昼夜累极的哨兵,两眼睡意蒙眬,让强夺时间的车辆乱了方寸秩序,在桥中对头顶牛。相峙的结果,总有一方软下来,退回去,使原本拥挤的道路,更加拥堵不堪。行人的吵闹声、责骂声,自行车的铃铛声,摩托车、汽车的鸣笛声,在黄河两岸形成声声入耳的乐章。上班族总是不停地抬手看表,现出各种焦急等待的表情,他们热锅上的蚂蚁般团团乱转。而大铁桥依然稳如泰山,不急不躁,一副姜太公钓鱼的悠闲神情。
我每次骑自行车上班,经过铁桥,迎面相遇车辆经过时,急忙下车站在旁边木板行人便道上躲避,等车通过。那一刻,高驾凌空的大铁桥,被黄河的浊浪拍打震动,心就随桥不由产生微微颤动和恐惧,仿佛人车霎时会掉进奔流汹涌的河水中,被吞没卷走。
青铜峡镇——这个工业小镇的繁荣热闹,就是凭借这大铁桥的雄伟壮观的存在,而店铺林立,人气大增,熙熙攘攘。
小时候,我常随父亲越过大铁桥到河西各建筑工地玩耍,大铁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留下神秘古老的色彩。先是两岸防风固沙的沙枣林中沙枣花随河风在桥中央清香扑鼻吸引着我,金黄沙枣粒的甜涩满足了孩童们的馋嘴。后是读高中时,常被黄河两岸花红柳绿、青山鸟鸣所牵引。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邀五喝六,结伴同行,到河西路去看环山而来拉煤运货吐冒黑烟的火车(铁路现已废弃);沿山道沟畔抓野兔、捉蜥蜴、捕蛇、摘酸枣;遇大坝水库泄洪排沙,顺铁桥而下,拿捞兜、脸盆、鱼叉等工具追奔着,赤脚裸背穿着短裤捕捞被浊沙洪水呛昏漂浮上来的黄河大鲤鱼大鲇鱼。
每逢水涨潮落,桥下游形成浅滩河岛。孤岛草长莺飞,柳绿草旺,水浅处赤脚踏浪,卵石细滑,仰躺青草花丛,实为世外桃源。是同学朋友聚会、野餐观光、畅谈人生理想,恋人相依相吻、互诉衷肠的好去处。
晚霞点染西岸苍山,河光潋滟,碎金着彩。夜幕降临,黄河两岸更是万家灯火,大铁桥顿时流光溢彩。若满月清辉,大铁桥空驾银盘,桥影布河,水波灯影,别有风韵。即兴赋诗:
河似银杯水胜酒,举杯邀月醉嫦娥。人间遍地真情留,错把铁桥驾天河。
黄河大铁桥风流散尽,风采依旧。某日倏然间,负重不堪,败塌码头,桥尾陷落。这时的大铁桥已滞后于经济发展步伐,如同患了肠梗阻的病人。在下游新的黄河公路大桥没有建成通车之前,大船载车,小船载人,发动机“突突突”地来往于黄河之上,让两岸行人车辆过足了船瘾。虽没有古渡口小舟摇橹和羊皮筏子那般清静悠闲,但两岸行人匆匆来往,如同大铁桥上空漂流的云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的大铁桥建成通车,让昔日拥堵了三十多年的大铁桥退台谢幕,隐士般清闲了下来,只有行人摩托车每日穿梭而行。少了车辆鸣笛的大铁桥,也少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支宁建设者的脚步和身影。一些人忠骨埋于青山之下,黄河岸边,子承父业,根留古峡。一些人从这大铁桥上走向全国各地,成为异乡人。但是更多的人仍走在这大铁桥上,建设着美好家园。又有多少人梦里思故乡,天涯海角都难忘——那山,那水,那铁桥。
秀芝老师
眼前的班主任李秀芝老师是位十八九岁的天津女知青,黑而弯曲的眉毛下,那双眼睛清澈如潭,明亮如星。白皙的脸蛋,微笑时露出两个甜甜的酒窝,那好听的普通话令我们这些灰头土脸的乡村野孩子充满了好奇。
秀芝老师教我们语文,另代音乐和舞蹈。她的嗓音很甜,那架老旧的手风琴居然在她纤巧的十指下飘出那么动听的曲子,荡漾在我们一颗颗童心里。我们张大嘴巴,一首首歌曲穿过那破旧的土坯教室的“人”字型房顶,穿过透着斑驳阳光的破瓦洞和低矮昏暗的窗户,响彻整个校园。
秀芝老师的舞跳得极好,特别是她那根油光发亮的大辫子在后背甩来甩去,带着一阵香气,就像《红灯记》中的李铁梅,旋转起来的红衬衫像一团跃动的火焰,燃烧着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因为惧怕上台表演,我不愿参加秀芝老师的舞蹈队,便常常逃课,和那帮坏小子混在一起。秀芝老师好言相劝,三番五次硬拉我到舞蹈队,反而让我产生了逆反心理,让我从心里“恨”起她来。
那天,我拿了弹弓,上了颗小石子,趁秀芝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空当,“啪”的一声,像射一只跳跃的麻雀。秀芝老师“哎呀”一声跌坐在地上,她甩着红肿的手背,痛苦地慢慢将头转过来,流着泪说:“是谁干的?站起来!……”
我当时惊呆了,也怕极了,低着头站了起来。
“怎么是你?!连你这乖孩子也在学坏……”我看见她将头抵在弓起的双膝上,抽泣了很久。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广播里传出敬爱的毛主席逝世的哀乐,全校师生顿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看见秀芝老师趴在课桌上哭了很久,像个伤心的孩子,而我们这帮二年级的顽皮孩子低着头左顾右盼,努力想挤出几滴眼泪。
一九七八年春天,知青返城。秀芝老师和六名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地的知青带着遗憾、知识和歌声,伤心地走了。两辆马车卷起的灰土遮不住孩子们围着土墙送行的泪眼。
紫花苜蓿
我倾心于眼前这香泽浸润开满紫花的苜蓿地。是盛夏晨露湿润的目光,是蜂飞蝶舞于画的景致,赶在我前面,闹着花事,嗡嗡地唱,翩翩地飞。
这片奶牛的饲料基地,令我想起多年前去内蒙古巴音草原的一幕。
也是盛夏。游云般飘动的羊群,沿草场移动,连绵的青山下,有一汪偌大的湖堰,远观像嵌着的蓝宝石,亮晶晶,蓝盈盈,融蓝天白云入境——这像是“宝石湖”。
装饰宝石湖边缘的,是满目翠绿的紫花苜蓿地,宛如少女长长的睫毛,微风过处,忽闪忽闪的。噢,满怀心事的少女在想她的情郎了。
女人们都在收割苜蓿,男人们在放牧或出门务工。黄狗趴伏在柔软芳香的苜蓿地里,懒洋洋地晒太阳,牛儿在远处山坡下抖擞发亮的红色皮毛,悠闲地摇头摆尾,忽而又卧下,“哞哞”地叫几声,反刍着灿烂的阳光。
微风送来女人们收割时被苜蓿花香熏染的淡淡气息,那是一个十八岁少年对青春健美少女体香的敏感。我的镰刀在浓郁的花香中停下来,盘腿坐在紫花苜蓿上,擦一把汗,咕咚咕咚喝几口铝制军用水壶里的奶茶,看那些嬉闹的女孩子追逐蝴蝶时甩动的长辫,和单薄的衣衫下凸现的丰满身姿。
有谁吆喝一声“洗澡去喽”,女人们立刻放下活计,欢笑着蹦跳着跑向前面的宝石湖,脱成光亮的鱼儿,在清澈透亮中掀起一片水潮。而男人的目光则远远地围起了一圈栅栏。
多少次梦见自己躺在紫花苜蓿上仰望夜空,身边坐着我热恋的草原姑娘,夏夜因为她的笑声失去燥热,如水的月光照着她的肌肤。晶莹的露珠滚动着馨香,苜蓿花柔软轻盈地开放。啊,那温馨的日子毕竟已经远去了!
岁月如歌,繁花似锦转头空。紫花苜蓿,成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被割去又长出的青春一去不返。
岁月如麻
麻呈纤维状,可织布制绳,增加经济收入。春耕种麦后的三月下旬开始播种麻子。五月的麻苗长到了一拃高,开始集体拔草疏苗,施肥灌水。经过晨露滋养,阳光孕育的麻苗青绿欲滴。放眼一望无边的麻田,末尾还夹杂着胡麻地、西瓜田。
转眼到了夏季,西瓜在几个有经验的庄稼把式老头手里压条、掐花、施肥,精心侍弄下,成熟的瓜体滚圆如翡翠点地。
麻苗长势喜人,八月里长成两米多高,绿麻叶茂花白,风摇舞摆。我们这些六七岁还没入学的玩伴,越过蓝花香海、蜂蝶翩闹的胡麻地,匍匐爬行。偷摘了西瓜后,被眼尖的看瓜老汉发现了,一阵逃窜狂奔,就势拨开绿林麻秆一头钻进去,恰似一滴水融入大海,任凭你长了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也寻觅不出丁点踪影。密匝匝的高秆麻叶,遮蔽了似火的骄阳,虚惊的热汗顿时消退。我们这些屁孩子们压倒一片麻秆,围坐一圈,将那红瓤西瓜摔成几牙,手抓嘴啃,个个吃得瓜水满脸,凉爽甜润。肚圆嘭嘭响,尿憋哗哗流。不知谁出了新点子,再玩捉迷藏的游戏。又分头觅声寻音探向那喳喳叫的翠鸟的窝巢,摸蛋捉雏雀,享尽童趣。
麻秆成熟时,队长组织有经验的好手去割。用手斜拨麻秆轻轻揽入怀中,将锋镰紧贴地皮轻割,以防止断了麻茎。杀青的麻秆,逐排淹入深挖的水塘,盖草掩土,发酵半月,麻塘呈幽碧水色,像融进了一片天日。观察青麻翠涩退净为熟,一个多月后,出麻时,臭味掩鼻,清水洗浊,风干后堆积成山,只等秋收冬闲,剥出麻线。
生产队院落土坯房大会议室里,除男壮劳力外,年轻妇女小孩老头老婆婆集聚一堂。冷天围着火炉,暖天门外晒着太阳,你一捆我一堆,坐在角角落落里剥麻说笑嬉闹。有唱秦腔眉户戏的,有谈论家常是非琐事的,小孩的哭闹声,大人的责骂声,叽喳如雀,嗡声似蝇。有时也为闲话小事争吵骂仗,泼嘴粗话连珠,内容全是偷鸡摸狗偷汉骚情捕风捉影烂舌的事。麻脸的王二妈就绘声绘色地咬耳根,背地里说死了男人的二牛媳妇和村东头光棍汉马三娃在麻田里野合时,被听见了声响,被看见了赤裸的一幕。那时的谣言,能捅烂脊梁骨,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年轻漂亮的二牛媳妇蒙羞含恨,洗身更衣,将三岁的小儿交给吊着黑脸不拿正眼瞅她一下的公婆,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
在雪白麻秆上玩耍饿哭的毛孩子,被娘塞进乳头堵了馋嘴,吃饱了入梦。听母亲说,缺奶的我,总被母亲抱到人家孩子吃剩的奶水前,讨一口奶吃。收工时麻线称斤记分,胆大的手缝里偷绕几团乱麻。麻秆柴归自己,成捆地背回家,或用驴车拉回,麻秆是农家烧火取暖做饭的上等柴火。
那时实行商品凭票供应,布票、粮票、棉票等票证也十分有限,所需紧俏商品只能在供销社门前排长队购买,针头线脑的碎小物件也奇缺稀罕。每家分到几斤麻线,用来搓绳。冬天下雪休工,妇女们就忙着纳鞋缝衣,补袜绣鞋垫,邻里串门比着花样,而最数母亲手巧。男人们扎好驴马骡子的拥脖,套绳笼头,鞍件红樱花铃,修理好牛车马车,都是为来年运送土粪,耕田跑运输做准备。
批斗会上,麻绳捆扎的四类分子弓腰曲背,鼻孔流血。社员们手拿毛主席语录齐喊口号,高唱革命歌曲。阶级意识,在无聊的大会小会中无端地增添了几分仇恨积怨。女人们一放下语录,就拿起针线绳子偷空纳鞋。麻团绳索,绾成一个巨大的惊叹号!一些人脑袋伸进绳圈中结束了难以忍受的生活。
禁锢的思想,羁绊着每一寸发家的步履。社会主义的镰刀,锋利地监视着追割着资本主义的兔子尾巴。越穷越光荣,却走不出愚昧贫穷的怪圈。贫与寒似乎是一对孪生姐妹。
儿时顽劣,手拿火柴,点燃麻秆柴火。熊熊大火冲天,烧了一垛柴草——那是寒冬腊月我们全家御寒解冻、取暖烧锅的救命草啊!没了柴草煨烧的土炕冷若冰霜。母亲和乡邻们正在田间劳作,发现我家着火后,惊呼着扔了工具,一群人慌忙跑过去,提水救火。无奈水井太远,风吹火旺,烈焰燃尽,柴草成灰。母亲痛打我一顿,我哭,母亲哭。众邻们劝慰母亲说,还好,没有伤了娃娃是万幸!我那时六岁,不明事理。炕头的木桌火盆里的火焰有气无力,暗淡无光。冰窖似的土坯房里,哈气罩雾,木格窗纸上,饥饿的麻雀啄食着糨糊,在天光的映射下恰似皮影戏上的纸皮雀,大人只要伸出沾有唾沫的食指浸湿纸张轻按雀爪,就会捉住一只。回族人不吃麻雀肉,却很在乎一张纸,纸张金贵,纸破了,风钻屋,寒气就会结霜冻头,冰凉手脚。那时家家户户烧煤紧缺,要星夜五更套了毛驴牛车,怀揣干粮身背茶水,赶百十里山路到太阳山地区石沟驿煤矿三四天才能返回。父亲下班回来,借钱买了人家几十垛麦柴,两手推车麦壳草屑,才让炕头有了温暖。
身为木工的父亲从厂里下班回家后,抽空要用母亲涉水越坎沿各沟岸选砍晒干的笔直的柳条编筐扎簸箕。母亲拉到集市上卖出,换回油盐粗粮等添补窘迫的家境。母亲也学会了亲手编织各种家什。
麻的种植在风雨飘摇中随着改革春雷的一声鸣响而悄然退耕。塑料编织袋替代了粗笨的麻袋,精神的绳索不再捆绑人们致富发家的手脚。丰饶的物质生活反而使人们感觉到精神追求的虚空不足。面对昔日苦难如麻的记忆,那个饥馑的年代已成缩影,幸福的下一代是否能得出一点忆苦思甜的感悟,那就是——
流水诉岁月,把酒话桑麻。
和谐致富路,金色好年华。
童年的天堂
我的家乡青铜峡多渠多沟多桥。渠是汉渠,历史久远。后来开发了许多农田灌溉渠,夏季水量最大,冬春渠干结冰。因而渠口多桥,每两公里就有一座水泥桥。至于沟,我家门前的四季沟,是灌区各大小沟渠之水交汇直通黄河的一条清水沟。
这些大大小小的水道像农田的血管经络,是宁夏川区最具活力、生机和希望的水循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