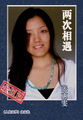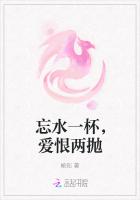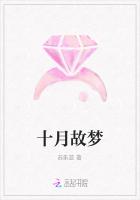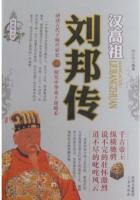年羹尧决定去见一见隆科多。这日晚上,年羹尧吃罢晚饭,一个人悄悄来到隆科多府上。二人相见之后,相互寒暄了几句,谈话就进人了正题。隆科多道:“年大将军,此次面圣有何感想?”年羹尧忙道:“隆大人,皇上对西陲之事到底满意不满意?”隆科多似稍稍一惊,望着年羹尧道:“大将军,你对皇上尚有疑虑?”年羹尧忙道:“不敢,皇上待我如此天高地厚,我怎敢有丝毫不满呢?我只想知道皇上对青海有何打算?回去后好早做准备。”隆科多哈哈大笑:“大将军,大清的半壁河山就靠你在那撑着,你还想班师回朝,或者调入京中吗?那你看有谁能接替你呢?”
年羹尧听到此言,心中涌出一股难以言表的滋味,这里面有苦、有甜、也有酸涩。看来自己的下半生只能与黄沙、朔风、雪山、草地为伍了。但这是皇上的信任,也说明自己对大清帝国来说是多么重要。隆科多见他沉默,心想他可能有些失望,忙安慰道:“大将军,这一切都是皇上的意思。不过一旦条件成熟,我会向皇上言明,调你做做京官,也享享几年清福。”年羹尧听隆科多如此一说,心中宽慰许多,忙道:“多谢隆大人了。京中有隆大人,我年羹尧在江湖中为官又有何惧呢?”
隆科多听年羹尧如此一说,倒也很高兴,满脸兴奋,说道:“大将军,我们今后要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今后只要我隆科多尚在位上,就不会让你吃亏。不过时世多变,百事难测啊!”年羹尧忙点头称是,心中自有一份威激。隆科多见年羹尧似有话说,但又不好开口忙笑道:“大将军,你今天来我这,不是单单来看我,给我送这么一只翡翠烟斗吧?还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可避讳的吗?”
年羹尧听他这么一说,便道:“怪不得外人都称隆公为‘小诸葛’,什么事都瞒不了你。我这次进京。老是感觉圣上待我不如以前那么亲近了,连单独召见我一次都不肯?”
隆科多一听,又是一笑道:“大将军,皇上曾亲口对我说过,‘年羹尧是个人才,朕半壁江山都要交给他’。就凭这话皇上会拿你见外吗?他不单独召见你,一则他现在已是皇上,做皇上就要对每位大臣都要公平,不能偏私,做事多考虑全局。不像原来只是一个王爷。做事可多带些私人感情。二则皇上最痛恨结党营私,讲究政治清明。他如对你过于亲昵,岂不留下话柄于百官吗?大将军是聪明人,难道看不出这些吗?”年羹尧这才彻底释然。心情一高兴,谈话也就很轻松。谈着谈着又谈到了京中的事。
“隆大人,皇上对诸王爷是何态度?”隆科多当然明白年羹尧问话的目的,便道:“皇上以仁慈为怀,对诸王爷是仁至义尽,无论怎么说,还是亲兄弟嘛。不过……”隆科多顿了顿,压低声音道:“皇上对以前的事并没有完。很多事现在还很难预料,我们都要多加小心,谨慎从事。”年羹尧郑重地点了点头。
回到驿馆,年羹尧心头的乌云散去,心情很是舒畅。这时,一个仆人来房门外道:“年大人,外面有人求见。”年羹尧一怔,道:“让他进来。”来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人,一身普通装束,外人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大将军也不认识他,那人看大将军满脸疑惑,忙道:“大将军,我是十四爷府的,今日受十四爷所托,特来看望大将军。”年羹尧一听,差点跳了起来,呆呆地在那发愣。来人忙道:“大将军,你不必惊慌,十四爷让我给你捎个信,现在皇上已对你不满。你要小心。”说罢掏出一封信递过来,年羹尧并没去接。那人微微一笑,把信放在桌上。
年羹尧道:“请你转告十四王爷,以前的事就不必再提了,翻起旧账,对谁都没好处,至于其他的事,现在不必多说,各人心中自然明白该怎么做。”
来人大概没想到他会如此冷漠,便只好起身告辞。这一夜,年羹尧一夜没睡。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十四王的话和隆科多的话,他不知道谁真谁假。斗争的结果,他还是相信了隆科多。看来京城是呆不下去了。第二日,年羹尧上朝面圣,请求回西宁。皇上道:“年爱卿,西域之地寒苦,尔多年在任上为国尽忠,今日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机会难得,不妨在京中多呆些时日,清闲清闲。”年羹尧一听,心里热乎乎的。看来皇上还是挺关心自己的。于是道:“多谢皇上关心。西宁叛乱初定,川、陕之地事务繁忙,臣怕在京中耽搁太久,误了国家政事,有负皇恩。所以臣还是请求早日返回任上。”皇上龙颜大悦,道:“年爱卿为国尽忠,赤胆忠心。值得褒扬。既然爱卿执意返回任上。朕也就不强求你了。现在有朕从新科进士和宫中挑选了几名新人,让他们在你身边效力,多向你学些文韬武略。你要多加调教,为朕多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
年羹尧忙跪地谢恩:“多谢皇上对臣的抬举,臣一定不负皇恩。”三天后,年大将军带着这几位新人和自己的随从匆匆逃出京城。兵部、吏部许多官吏到十里长亭送行。年羹尧一一与他们辞别,怀着复杂的心情返回西宁。事实上这几个新人就是雍正皇上放在他身边的耳目。
雍正三年。
青海平定。卓子山、棋子山叛乱番贼大部被年羹尧部擒获,整个青海、甘肃烽火渐熄,狼烟散去。叛乱各部死伤大部,元气大伤,苟活残余都拖着累累伤躯遁入荒漠、草原深处,堰旗息鼓,匿藏于草丛沙石之间。一时边境平静下来,胡人不敢南下牧马、东向而视。
这一日,西宁城一片欢腾,冲淡了多日沉闷的气氛。大将军迎来了京都使节,年羹尧跪接圣旨,旨日:“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又擒获卓子山、棋子山番贼,威震胡番,国稳边固,劳苦功高,特加封年羹尧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其子年富封为一等男爵,以彰其勋。”
2 因材施教——年羹尧成才之路
一个没人可以管教的孩子是怎样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军的?这是一段关于年羹尧成才的传奇秘史。
年羹尧是个文武全才,提起他,就不能不提到他的一个启蒙老师,叫王涵春。年羹尧上任西北大将军不久,踏遍千山万水,终于把这位老师请到西北大营,一来以报师恩,二来教自己的儿子读书。关于这位王老师,还有一段故事。
多年以前,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空有万贯家财,在三十岁上,生了一个大儿子,名希尧;看看自己到了四十岁还不曾生第二个儿子,心中十分懊恼。后来他夫人在三十八岁上又得一胎,生下一个年羹尧来,把个年遐龄快活得直把年羹尧宠上天去。看看到了八岁年纪还不曾上学,年遐龄便去请一位饱学先生来给他上学。谁知年羹尧自小生性粗蛮,也不愿读书,见了先生,开口便骂;那先生生气,便辞馆回去。一连换了五六个师傅,他总是不肯读书。他年纪慢慢地长大,又天生的一副铜筋铁骨,他后来不但见了先生要骂,且还要打呢,他气走许多先生。从此以后,吓得没有人敢上门来做他的先生。那年羹尧见没先生,乐得放胆游玩。这几年被他在府中翻江倒海地玩耍,险些不曾把家中的房屋拉坍。年羹尧看看长到十二岁了,还是一个大字也不识。年遐龄心中十烦闷。有一天,他带着儿子在门外闲玩,忽然一个走方郎中,摇着串铃儿踱来。走到年家门口,向年羹尧脸上仔细一看,说道:“好一位大将军!”
这位走方郎中原是有本领的,当时他看定十二岁的小孩子将来有大将军之命。年遐龄还不十分相信,那走方郎中又仔细一看,连连说道:“险啊!将来光大门庭的是他,遭灭门大祸也是他。须要多读些诗书,才可免得这祸事。”提起他儿子读书的事体,年遐龄便触动了心事,叹了一口气说道:“这孩子便坏在不肯读书!”那郎中说道:“老先生倘然信托晚生,包在晚生身上,教导他成个文武全才。”年遐龄听他说话有几分来历,便邀他进府去暂住一宵。那郎中把自己的来历和教导年羹尧的法子细说一番,说得年遐龄十分佩服,到了第二天,便要请他做先生。这郎中说道:“且慢,老先生且拿出二万银子来交给晚生,晚生自有办法。”年遐龄听了,毫不迟疑,便立刻拿出一叠钱庄折子交给先生,任凭先生用去。
那先生拿了银钱,依旧不管教年羹尧;只是在年府后面买了一方空地,雇了许多工匠,立刻盖造起一座花园来。楼台曲折,花木重重,中间又造一座精美的书室。直到残冬,才把一座花园造成,四周高高地打一重围墙,独留着西南方一个缺口。先生便拣定明年正月十六日,为年羹尧上学的好日子。到了那日,年遐龄便备办下酒席,请了许多亲友来陪先生吃酒。吃完了酒,年遐龄亲自送年羹尧上学去,他向先生作了三个揖,说了种种拜托的话,转身便走。先生把年遐龄送出了那围墙的缺口,吩咐工匠即刻把那缺口堵塞起来,只留一个小小窗洞,为递送食物之用。那年羹尧住在围墙里面,只因花园造得曲折富丽,一天到晚玩着,却也不觉得气闷,那先生坐在书房里终日手不释卷,也不问年羹尧的功课,年羹尧也乐得自由自在,在花园中游来玩去;他自从到了花园里,从不曾踏进书房一步,也从不曾和先生交谈一句。他高兴起来,便脱下衣裤,跳下池中去游一回水;有时爬到树上去捉雀儿;春天放风筝,夏天钓鱼,秋天捉蟋蟀,冬天扑雪,一年四季,尽有他消遣的事体。
有时玩厌了,便搬些泥土,拔些花草,也是好的。他在花园里足玩了一年,好好的一座花园,被他弄得墙坍壁倒,花谢水干,甚至于那墙角石根,都被他弄得断碎剥落。只有那先生住的一间书房,却不曾进去过。先生眼看着年羹尧翻江倒海,他也不哼一声儿。后来年羹尧实在玩得腻烦了,便进到书房去,恶狠狠地对先生喝道:“快替我开一个门儿,我要出去了。”
先生冷冷地说道:“这园中没有门的,你倘要出去,须从墙上跳出去。”
年羹尧见不给他开门,便擎着小拳头向先生面门上打去;只见那先生双眼一瞪,伸手把臂膀接住,年羹尧不觉“啊唷”连声。先生喝他跪下,他怕痛不得不跪了。先生放了手,他一溜烟逃出房门去,一连几十天不敢进书房去。
看看又到了秋天,景象萧索,年羹尧也实在玩不出新鲜花样来了,便悄悄地走进书房去,只见先生低着头在那里看书。
他站在书桌边默默地看了半天,忽然说道:“这样大一座园子也被我玩厌了;他这小小一本书,朝看到夜,夜看到朝,有什么好玩?”那先生听了,呵呵笑道:“小孩子懂得什么?这书里面有比园子大几千百倍的景致,终生终世也玩不完,可惜你不懂得!”年羹尧听了,把脖子一歪,说道:“我才不信哩,你给我说说,让我听听,怎样个好玩法?”那先生听了,摇着头说道:“你先生也不拜,便说给你听,没有这样容易。”那年羹尧听了,把双眉一竖,桌子一拍,说道:“拜什么鸟先生!我不稀罕!”说道,他一甩手出去了。这先生也任他去,不去睬他。又过了十多天,年羹尧实在忍耐不住了,便走进书房来,纳头便拜,说道:“先生教我罢!”先生这才扶他起来,唤他坐下。
第一部便讲《水浒全传》给他听,把个年羹尧听得手舞足蹈;接着又讲《三国志》、《岳飞传》、古往今来英雄的事迹、侠客的传记。接着又讲兵书、史书、经书以及各种学问的专书;空下来教他下棋、射箭、投壶。后来,十八般武艺也件件精通,又教他行兵布阵的法子。足足八年工夫,教成一个文武全才,此时,先生便叫年羹尧自己打开围墙出去,拜见父亲。那年遐龄八年工夫不见他儿子,如今见他出落得一表人才,学成文武技能。如何不喜,忙去拜谢先生。那先生拱一拱手,告辞去了。任你年遐龄父子再三挽留,也留他不住。他临走的时候,只吩咐年羹尧记住“急流勇退”四个字。年羹尧如今富贵已极,却时时感念他的先生,又请王先生在西北大营呆了三年。
雍正三年春天,年羹尧叫幼子送师归家。这位王先生匆匆回家。到了家门,蓬荜变成巨厦,陋室竟作华堂。他的妻子出来相迎,领着一群丫头使女,竟是珠围翠绕,玉软香温,弄得这位王先生茫无头绪,如在梦中。后经妻子说明,方知道这场繁华,全是年大将军背地里替他办好,自然是感激不尽。那位年少公子,奉了父命,送师至家,王先生知他家法森严,不敢叫他中道折回。到了家中,年公子呈上父书,经先生拆阅,乃是以子相托,叫幼子居住师门,不必回家。先生越发奇怪,转想:“年大将军既防不测,何不预先辞职,归隐山林,逍遥自在,以乐余年,有何不美呢?”王涵春本想写封书去劝他,但又怕他刚愎脾气,未必肯听,便将来书交年公子自阅。公子阅毕,自然遵了父命,留住不归,从此这个儿子流落在民间,算是为年家留了后人。
3 惹火烧身——年羹尧败运的开始
对于正在寻找年羹尧短处的雍正来说,碰上了年羹尧自己送上门来,真是高兴还来不及,这为他对年羹尧下手找到了借口。
年羹尧隐隐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已经降临。他上的那一道奏折,皇上迟迟没有下旨,这与以前不同。以前自己每道奏折上去,不出两个月,皇上必会恩准,可这次已经过了三个月了,仍无消息,罩在心头的这块乌云,愈积愈厚。
羹尧的预感不久变成了现实,最终发生了扭转年羹尧人生命运的一件并不起眼的案子—金南瑛弹劾案。
雍正从即位的第三年开始处心积虑要干掉两个尾大不掉的对头。一个是平定西藏、青海,历任四川、陕西总督、抚远大将军、加封太保太傅的汉人一等公年羹尧。此人功高震主,据说他行路时要用黄土填道,百官见之一律跪拜和皇帝平起平坐。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这时,雍正整治年羹尧的机会来了。雍正手中拿着年羹尧的奏折,慢慢环视群臣,厉声道:“自朕临御以来,一直有人暗中作梗,不与朕同心。宫中诸王子心存二志,年羹尧、隆科多等人又假借朕的信任,挟权自重,胆大妄为……”一番话未曾说完,那股肃杀之气却已横扫大清。
金南瑛被参,原来不过是一件普通的事,开始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但就这件小事,却扳倒了两棵大树。两位叱咤风云几十年,又是炙手可热的新朝宠贵栽下了马,一死一囚,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对此耿耿于怀。
金南瑛,康熙末年进士,外面传言很有才学。后结识了大学士宋轼。二人相谈颇投,宋学士赏其才华,向康熙奏闻,保举金南瑛,康熙命金南瑛入会考府,负责会考的出题、阅卷工作。这金南瑛恪尽职守,为政清廉。每次出题,均能体察圣意,启迪学人,获众人称誉。后与恰亲王一起主持会试,怡亲王亲见他呕心沥血,评卷公平、公正,甚为欣赏。
新皇继位,正是用人之际,怡亲王竭力向新皇奏荐,言金南瑛为人正直,办事公道,一心为国家着想,是难得的人才。新皇意悦,授甘肃金昌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