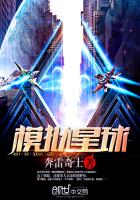2001年9月21日
当你抚平你的忧伤的时候(时间会缓解任何忧伤),你就会是我永远的朋友,你要跟我一起笑。而且,有时候,当你为了与我一同欢笑而打开窗户时,你的朋友一定会因为你看着天空微笑而感到惊讶,到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们,“没错,星星常让我笑!”然后,他们就会认为你疯了。这是我跟你开的小玩笑……
——《小王子》第二十六章
一
当觉得一切都没劲透了的时候,我决定去旅行。那时我已不年轻,但也不太老。阅历刚好够自己不至于被低级的欺骗给伤害到。
我几乎两手空空就上路了。文明进步的结果,就是让物质统治了一切。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可以算作一个“人”。但是,我星球上的其他人都跟我一样,脑部植入了芯片,身上也是随时可以接上莫名其妙的管子,可以跟任何需要的东西连接起来。所以,我虽然轻装上阵,却也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
在旅行社的简报上我找到一个不起眼的名字——死穴·塞伯坦。下面的注解标明,那里是曾经跟我们星球有过交集的一些巨型机械人的故星。价格很便宜,因为是危险星域,而且没有保险。我一向烦透了保险,所以我决定去那里。
到塞伯坦不用坐航天飞机,而是用古代遗留下来的天桥,很老旧的装置,但是交了通行金后,剩下的只是等待就可以了。大概多年以来这天桥使用的频率很少,操作员看到我时,我分明从他眼里读到了“哪里来的怪人”的字眼。
我还是一脚踏进了天桥泛着白光的“托盘”里,听天由命了。
二
我怀疑自己曾被肢解又重新组装,等到意识稍微清醒时,斑驳的塞伯坦已经在我脚下。
塞伯坦曾是高度科技化的星球,在翻看简介时我记得好像是叫什么宇宙大帝的家伙造出了这颗金属核桃,又有个长着五张脸的怪物造出了一大堆机械人,以奴役他们取乐。一部分是军品,算私人卫队,一部分是民品,干体力活儿。后来两拨可怜的机械人有了觉醒,联合起来反抗,就把老主人给赶跑了。再后来,能量和智力占优势的那拨机械人先学会了统治,于是战争重新开始,战火一直烧到我们星球。曾经一直被奴役的一方,联合了我的祖先们对付那拨军品。多少年以后,一场空前绝后的宇宙大战,可怜的机械人们都灰飞烟灭了。
他们的故星现在是墓地。唯一活动的生物只有我。
我也真是无聊到家了,来看古代的机械人的墓地,又不是多感兴趣。可返航的天桥要在翌日才能获载能量接通过来,剩下的十多个小时里,我只有滞留在塞伯坦上。
太空靴溅起了厚积的宇宙尘埃。我很快适应了塞伯坦的重力,可以正常地行走了。没有地图,只好依靠左臂上的定位仪。盲目走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发现两个巨大的穹隆。一个装饰着红色的标志,一个是紫色的。由于经年星暴侵蚀的锈迹,两种颜色早不分明,但我的肉眼还是能辨识出来。我们星球上我所在的区域盛行红色,我个人倒是对具有神秘感的紫色更感兴趣。于是,我向那装饰着暗淡的紫色标志的圆穹走去。
现在我是这颗星球上唯一的活物,所以不用担心被什么东西偷袭。可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寂静和幽暗恐惧的劣根性,恰如其分地发挥着作用。我强抑心跳,钻进圆穹张开的大口。
三
到现在也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描述我乍见墓群的心情。震惊、赞叹、窒息、压抑、恐惧、兴奋、战栗……我早就做好了会有以上那些感觉的心理准备,但不仅仅是这样,还有更多难以名状的冲动。我彻底知道了语言的贫乏。
巨大的,也许是和原形等大的塑像站立成两排,庄严肃穆。我想到了卡纳克和卢克所神庙。突然有点哑然失笑:本来可以永生的机械人,却屹立在所谓墓地里,妄图恢复昔日的荣光。一个起先模糊而后变得恐怖的念头包围了我:究竟是谁给他们建立了墓地?是机械人的后代或是说后世的机械人吗?那么那些机械人又到那里去了?
我来到最显赫位置的塑像前,有点置身某帝国蜡像馆的错觉。这是一个右臂的炮管无比粗大的机械人,他的头不可一世地向前方倾斜,早已没有任何光彩的机眼中似乎仍透露着威武和狰狞。基座上的名字是威震天Megatron,我想就是那位曾经连被他奴役的人都很钦重他的军用品的头目吧。这么说,我来到的这一圆穹,就是古时那军品进化的攻击方的墓地了。
“昔日的繁华都变做今朝的泥土。”我的母星上有很多哲言,可以验证各种各样的情状。
仰视太累了。我把目光收回到基座上。那还有一行小字,写着“有霸天虎,才有汽车人;有邪恶,才有正义。”我想有光就有影,有白就有黑吧。原来我们星球上东方文明有个很古老的图形,是迎头吞尾阴阳相化的,据说可以解释世间万物。
战争,只有一方是打不起来的。
四
一个塑像一个塑像的走过,看着那些有的清晰有的模糊的名字,猜测主人“生前”的轶事。其中,有个机械人声波SoundWave看来很和睦,身边静置着几个小型的机械动物和机械人。他的基座刻着“忠诚”。喜爱动物的人都会忠诚吧?尤其他还养了一条狗,还是美洲狮?我开始觉得制造他们的怪物还算是个有人情味儿的家伙。
忠诚于邪恶不就是助纣为虐吗?可是他的同伴都会认为他“忠诚”。任何形容词都应该有个界定的范围。可是,谁又能说他不忠诚呢?我冲着这个牵狗架鸟的机械人笑笑,觉得自己很傻。
大概供氧和恒温装置电力不足,害得我有点手脚冰凉,呼吸困难,好在还有不到十个小时,就可以熬到天桥开通了。
迷迷糊糊地摸到后面几个塑像,我才发现这是几个……怎么说呢,跟刚才的感觉不同的机械人,可以算成是女性吧。因为我看到其中一个叫SilveryShark的形状跟前面一排里的双胞胎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纤巧一些。我顺着她倾垂的机翼向下看着,看到基座上的铭文:逃避。旁边的一个有点像蜂鸟状的Timeless也有个相应的词语“思考”。
为什么会有女性的机械人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或是说为什么会给机械人以不同的性别呢?难道在我们星球早已盛行试管婴儿时,他们这些机械人还会是有性繁殖吗?当然,我只是以我们星球的思维方式在假设,而事实上,谁又能知道当时真正的历史?
五
见证了黑暗便渴望光明,我还是决定去旁边红色标志的墓地看看。如果说紫色标志像狐狸的话,红色标志倒有点儿像老虎。狐狸和老虎都是我的所爱。其实我在痴人说梦,我们星球上根本看不到什么动物了,我对动物所有的认知都是从信息资源库中提取的。
我看到传说中的擎天柱OptimusPrime。他好像是个浑身充满了正气的人,双手紧握,想给予,又想承担的样子。基座上附带一句念起来很响亮的“Till all are one!万众一心!”我不知道一个人或是一个机械人总扮演着救世主是一种什么心态。不过,他们并没有人类多愁善感的心灵,他们有的是头脑。一旦程序设计好了:他、他或他是以解救天下为己任,他们就会坚定不移地执行。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而已。但我差点忘却了——不论是霸天虎也好,汽车人也好,他们都是有智慧的。他们并不是人类发明的机械人,他们会创造,所以,也会选择自己的路。
宇宙大战的辉煌时代,我没有赶上。那时我的曾祖母还是个小姑娘。可惜她死得很早。据说是因为不听警报擅自离开掩体而被流弹击中。我现在以一个客观人的身份游览着变形金刚的故星或者说墓地,我既不为曾经的朋友汽车人叹惋,也不为曾经的敌人霸天虎厌愤,我想我能冷眼看待这一切。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存在的价值,机械人也不例外。
还听过另一种说法,初代的汽车人首领擎天柱OptimusPrime把他们叫做“能源宝”的东西传了下去,他的继承人还在率领着旧部和新丁与霸天虎作战。
山顶的神每天造一个人,当人下山时,就被山下的魔鬼吃掉了。神不停地造人,魔鬼不停地吃人。终于有一天魔鬼跑到山顶质问神:为什么明明知道人一造出来就被吃掉还继续造人的工作,神停下手上塑的泥胎迷惘地说:我总得找点事做。半晌,魔鬼说:我也是呀。
六
汽车人与霸天虎打了几辈子的仗,到头来,他们先人的墓地都并列在一起,像兄弟一样相亲相爱。而且,我还想知道,“死”,对于机械人来说,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销毁他的芯片——这是通常人类的想法。
电池里的电不多了吧。我艰难地走出汽车人墓地,感到冷得有点恶心。我不会死在这里吧?和这两堆伟大的机械人躺到一起,多少年后,成为另一个或几个像我一样无聊的人的观摩对象?
可是,我的视线被什么东西给吸引了。在两个圆穹的不远处,似乎还有一个塑像,横置着,离群索居。我拼尽最后一点力气走过去——
他跟霸天虎里的双胞胎是一样的,可能他们是三胞胎,能够变形成流线型飞机。当时我们星球上最先进的F-15战斗机也不过如此。虽然,他们三个的外形相同,但我觉得被遗弃在外经受宇宙射线洗礼而浑身坑坑洼洼的这一个更有一种……魅力。他的脸上有表情,像在嘲弄别人,又像在自嘲。
我真的是在死亡边缘了,竟然觉得机械人有魅力。这一定是幻觉。
他的基座翘在半空,我很费劲才找到他的名字——StarScream。
StarScream,StarScream,StarScream……我喃喃地念着,觉得这名字有点耳熟。我突然想起来,曾祖母的日记里出现过StarScream的字样。她曾书写她的梦想,就是“坐在红蜘蛛StarScream的肩膀上看风景”。这个名字还不止一次出现过,我一直以为StarScream是哪个小伙子的绰号,没想到,是这个倒在尘埃里的机械人。而且,是侵略的一方。
特洛亚的公主波吕克赛娜也曾爱上过敌将阿喀琉斯,结局是为他殉葬了。我突然又想到曾祖母是擅自跑出掩体而死的。
这个叫红蜘蛛StarScream的,为什么被他的同伴和敌人都抛弃了?他究竟有过怎样的经历,连塑像都得不到安息?
七
氧气不多了,真不知能不能支撑到天桥开通。我的意识模糊不清,注意力也集中不起来,这种又冻又窒息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
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旅行地。
我好容易摸到红蜘蛛StarScream的塑像旁,紧贴着他倒下。死前我总得抓住什么或靠着什么。在这个位置还能看得到天桥。
在我的眼睛终于撑不住闭上之前,看到了基座上的一句话……
……
有人在拍我的脸,我正恨他扰人清梦,被迫清醒过来。天桥操作员的脸部特写一时让我无所适从。他在喋喋不休:
“您看,我是个多么有责任感的人,见您没等在入口,我就到处找,要知道我的氧气带的也不多……喂!您怎么哭了?不用这么感恩啊。”
我低着头不理会那人的聒噪。
不记得上次流泪是在什么时候。我唯一能记住的是昏迷前看到的句子:
“I am, what I am.”只想做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