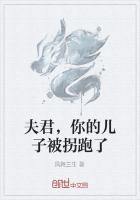小引
据说,钱钟书一生从不写新体诗歌评论,唯一的一次破例,是发表在《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六期上的一篇文章,叫《落日颂》。这是径直以一本诗集名称命名的评论文章,那本诗集的作者:曹葆华。
曹葆华(1906—1978),原名曹宝华,四川乐山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文学系,民国二十年(1931)入该校研究院。他的这本诗集《落日颂》,由新月书店于1932年出版。而钱钟书的评论于1933年3月1日发表,可谓及时。由于同为清华校友,又同在“新月”字号下,一个出版、一个评论,看官们一定以为是互相捧场,彼此彼此的文坛勾当罢,实则不然。
在钱钟书的《落日颂》中,有这样的评价:看毕全集之后,我们觉得单调。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被罚,Prometheus被絷的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咤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了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咒诅。
无论是用文雅的说法,还是用粗俗一些的说法,钱钟书说来说去,总而言之对曹氏诗作的评价并不高,这是显而易见的。时年二十三岁的钱钟书对时年二十七岁的曹葆华如此评价,想来同为青年时代的人都应当有一种激烈的心态与回应,奇怪的是,至今没有看到过曹氏的任何回应性文字或相关记述。
如果说是学养层面的文质彬彬,或是修养层面的含蓄使然,口诛笔伐可免,肚皮官司总难免吧。或许,此时的曹葆华尚无暇与比自己小四岁的钱钟书说长道短,年轻的新月派诗人正沉浸在爱情的蜜罐与“灵焰”的煎熬之中。
在《落日颂》出版之前,有一首曹葆华所作的“情诗”流行于清华校园。诗名“她这一点头”,作于1929年;后来选辑入诗集《寄诗魂》中,震东印书馆1930年出版。诗中充溢着浓厚的爱之喜悦,有酒神的欢悦浓烈味,也有东方的淡雅书卷气。诗曰:
她这一点头,
是一杯蔷薇酒;
倾进我的咽喉,
散一阵凉风的清幽;
我细玩滋味,意态悠悠,
像湖上青鱼在雨后浮游。
她这一点头,
是一只象牙舟;
载去了我的烦愁,
转运来茉莉的芳秀;
我伫立台阶,
刹那间瞧见美丽的宇宙。
校园中盛传着曹葆华的情诗,但无从知晓诗的“本事”与“背景”。从字面上看,应该就是一位诗人心怡的女子认可了他的爱恋,让诗人欣喜若狂,满眼里皆是诗意了。
《落日颂》扉页上印着的一行字迹,透露着年轻诗人的秘密——“给敬容,没有她这些诗是不会写成的”。就在诗集出版的这一年,诗人要将诗歌与爱情进行到底。1932年5月23日,曹葆华带着十五岁的初中女生陈敬容(1917—1989),从西部偏僻的家乡乐山肖公嘴码头乘船,沿岷江水路出走。他们准备一直向北,到达北平,热望着开始人生中一段新的历程。他们的最后一道关口,从地理因素上讲,是要穿越水急滩险的“三峡”;从伦理因素上讲,则是要冲破旧式传统家庭的种种阻挠,这当然主要是来自女方家庭的强大阻力。
一、未来最好的诗人
如果你是鱼,
只能看着天上的云。
我宁可是雨,
粉碎自己,
为了触到你的鳞。
那可是你的灵,
再不是天上的云。
——曹葆华《夜雨第二章》
这首诗是新近发现的曹葆华手稿内容之一,在诗的末尾加上一段类似副题的文字:赠给未来最好的诗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钱钟书《落日颂》一文末尾的那段评价,他说,“所以,作者最好的诗是作者还没有写出来的诗。对于一位新进的诗人,有比这个更好的,不,更切实的批评么?”这个“未来最好的诗人”就是那个在未来能写出最好的诗的人,这似乎算是曹葆华的自勉,更可以看作是一种自信罢。
但是在1932年5月底的曹葆华,在三峡与那个比自己小十二岁的女生一起准备渡船的曹葆华,更应该是未来最好的爱人,而非未来最好的诗人。经过紧张筹划,他们舟行三天,抵达万县。但一封由乐山女子中学与陈敬容父亲陈勖联合发出的代邮快电,终于拦住了他们的北漂之路。快电紧急通知了当地同乡官员,请求他们组织人手将曹陈二人拦截在万县。当地官员火速行动,立刻拦截,并先将他俩囚禁起来。陈敬容的父亲随即赶来。携未成年少女离家出走的罪责如何,问讯处理的具体意见如何,现在都无从查证。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或许是因为同乡的情面,或许是出于女方声誉的考虑,最终陈家人没有追究和张扬此事,曹葆华的爱情计划泡汤,但却可以平安返回北平。
一个星期后,曹葆华脱身回到清华,而陈敬容则被带回乐山,从此严加看管,被家人关了禁闭,并从此辍学。或许陈敬容此时就是那只只能看着天上云的“鱼”,而愿意从云化雨的曹葆华此时也只能重新飘回诗歌的天空中去了。
1933年10月,曹葆华开始在《北平晨报》上主编副刊《诗与批评》,前后历时两年半,集中刊登了卞之琳、何其芳、李健吾等诗人的创作,还大量登载了叶芝、瓦雷里、艾略特、瑞恰慈、威尔逊等西方最前卫的理论家的诗论,有研究者称曹葆华此举“为30年代中期中国诗坛黄金时代的到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有研究者盛赞道,曹葆华“创办的《诗与批评》,从整体上看,是与1932年施蛰存等人主办的《现代》杂志的倾向相近似,在推动新诗的象征派、现代派发展中,是起过一定作用的很有价值的专门性的诗歌副刊”。
曹葆华此刻搁置了前期曾热情高涨,而且普遍受到新月派同仁认可支持的诗歌创作,转而热衷于诗歌前沿理论的译述与推介。从诗人向理论家转变、从实际创作者向诗学译述者转化的历程,应该是两个外部诱因所致,而并非纯属自觉的思想转化。一是钱钟书评论中的苛刻与严厉,无论是刺激还是促使,都必然使他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基础及理论体系。二是与陈敬容那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计划泡汤之后,沮丧与疑惑的心态也间接促使他冷静思考自己的诗歌与未来。在这两个外部诱因作用下的曹葆华,实现这一次由诗歌创作向理论研究的转变,实属偶然中的必然。
据相关统计资料表明,从1933年7月24日翻译梅士斐的《译十四行诗二首》到1936年3月12日翻译安诺德的《安诺德诗序——第二版时之广告》,曹葆华在《北平晨报》上共翻译诗歌理论34篇,翻译专门的诗人传记3篇,翻译诗歌3首。除此之外,还有自己撰写的《现代诗论序》和《渥兹华斯——西洋批评名著小引之一》,诗歌创作19首。毫无疑问,曹葆华的这一次转向是相当坚决,成果也是颇为显著的。
有意思的是,由曹葆华主编的副刊《诗与批评》在1933年10月2日创刊号上,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他自己创作的一首小诗《她睡着了》,而另一篇则是署名为“陈敬容”的翻译文章,Gilbert Murray的《论诗》。一整版的内容均为这两个天隔一方的恋人所包办,这是诗人的象征主义手法使然,还是无奈的自我慰藉使然,皆令人叹息。而曹葆华代笔署名几乎毋庸置疑,因为时年只有十六岁,且被家人严加看管而辍学的陈敬容本人,翻译这么专业的诗学理论的可能性极低。
曹葆华在《诗与批评》副刊上发表的西方诗论中,于1937年以《现代诗论》的合辑形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这标志着曹葆华翻译生涯的阶段性成果。该书开创性的在中国新体诗坛中祭出一面大旗,即所谓的“纯诗”理论。
二、重读者与“纯诗”
城里没有雨。
一团庸庸的云,
拢缩着不愿离去。
砚台边上的残污。
催促
僧侣功课之法鼓,
咚咚底敲响归途。
——曹葆华《夜雨第一章》
这首诗仍然是新近发现的曹葆华手稿内容之一,在诗的末尾也加上了一段类似副题的文字:送给重读者。“重读者”的说法,仍然在钱钟书的《落日颂》中能够找到注解,文中曾多次提到“耐读”与“重读”之区别。
钱氏的原文为,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有一个分别:非文学作品只求READABLE——能读,文学作品须求RE-READABLE。RE-READABLE有两层意义。一种是耐读:“咿唔不厌巡檐读,屈曲还凭卧被思”,这是耐读的最好的定义,但是,作者的诗禁不得这种水磨工夫来读的。为欣赏作者的诗,我们要学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方法——囫囵吞下去。用这种方法来吃人参果,不足得人参果的真味,用这种方法来读作者的诗,却足以领略它的真气魄。他有PRIME-SAUTIERE的作风,我们得用PRIME-SAUTIERE的读法。行气行空的诗节忌句斟字酌的读:好比新春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好比远山的翠微,“即之愈稀”。在这里,RE-READABLE不作“耐读”解,是“重新读”的意思。
用“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比喻来解析曹葆华的诗,虽然乍听上去有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轻蔑,但也的确言之有据。新月派诗人大都看重与关注“韵味”,如钱氏的评论者则看重“气魄”,二者各有所重,无可厚非。即使是对曹氏诗作一贯予以支持和赞赏的新月派同仁中,也有持与钱氏“整体论”相近观念者,如罗念生致曹氏信札中就可见一斑。
早在曹氏《寄诗魂》一集出版时,高出曹葆华两届的学长罗念生就致信于他,称读《寄诗魂》“好像在迷梦中忽听了均天的神乐”,“一连读了三遍,觉全诗的意境很高,气魄很雄健。这是一座火山的爆裂,远看是一个整体,近看不免有些凌乱”。这无疑是钱氏论点的先声。而曹氏本人对学长总体赞赏、略有批评的观点应该还是满怀感激之情的,他在1932年11月仍由新月书店印行的《灵焰》(实际上是《寄诗魂》的精选本)一集中充分表达了这一感激之情,诗集扉页上赫然印着:给念生,没有他我是不会写诗的。
而作为学长的朱湘就在给曹葆华的信中称他的诗“用一种委婉缠绵的音节把意境表达了出来,这实在是一个诗人将要兴起了的吉兆”。徐志摩也致信曹葆华,称《寄诗魂》“情文恣肆,正类沫若,而修词严正过之,快慰无已”。闻一多在信中说:“大抵尊作规抚西诗处少,像沫若处多。十四行诗,沫若所无。故皆圆重凝浑,皆可爱。鄙见尊集中以此体为最佳,高明以为然否?”这些信件中的赞赏之词背后,其实都表明了一种对曹氏诗作定性的看法,那就是曹葆华对西方的格律诗商籁体即十四行诗的高度忠实。事实上,曹葆华正在试图以西方诗歌格律移植到中国新体诗歌中,这其中当然蕴藉着中国传统诗歌创作者的情怀。
这种想法在其相继出版的《寄诗魂》、《灵焰》、《落日颂》诗集中都得到全面呈现,格律体的借尸还魂与传统诗歌的古典元素,在日益需要新鲜养分和前沿理论支撑的新体诗歌界中并不新鲜,而且必然遭到激进的新派批评家和传统的古典批评家的联合围剿。青年时代的钱钟书只不过在此充当了一种时潮的代言者,对曹氏诗作大加诟病。
如果说钱氏提出“耐读”和“重读”来进行细致的旨趣勾勒,进而提出“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打诨式譬喻尚能让人勉强忍受的话,在后来逐首、逐句摘选并逐一解析中,一针见血的指摘与批评则没有给作者留丝毫的余地。在提到诗中屡屡征引中国古典意境元素时,钱氏指出:
你看,这许多琵琶声,婴儿啼声,寺钟声,杜鹃声来得多巧?每当诗人思想完毕的时候,江上立刻奏着琵琶,婴儿立刻放声大哭,和尚立刻撞起寺钟,杜鹃立使使劲哀啼,八音齐奏,做诗人思想终止的chorus。此外,作者所写的景物也什九相同;诗中所出现的生物都是一些不祥的东西,毒蛇猛兽是不用说了,乌鸦和鸱枭差不多是作者的家禽。
在钱氏的严厉批评中,我们看到曹葆华的诗作(如《夜雨第二章》)格调仍然没有改变,但似乎在内在机理和心理层次上发生了变化。他为坚守的象征主义格调以及发生着的微妙变化找到了理论依据,那就是:“诗中两种重要的成分——‘纯诗’与象征作用:这两种成分本是常存在于古今诗韵中的,不过在近代诗中占着特别重要的位置,而且当作理论来探讨,却是近几十年的事。”
他在《现代诗论》一书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出了上述这段话。他明确指出书中收录的雷达(Herbert Read)的《论纯诗》,墨雷(J.M.Murray)的《纯诗》,梵乐希(今译瓦莱里,Paul Valery)的《前言》,夏芝(B.W.Yeats)的《诗中的象征主义》四篇文章即是“象征主义”与“纯诗”概念的理论依据。但从文章排序中我们可以看到,“纯诗”的重要性与比重明显强于“象征主义”。或许,可以揣摩这种安排背后的用意,即“象征主义”的理论作为一种诗歌格调的常规表述,对1930年代的中国新体诗歌界而言已毋庸多言,而“纯诗”作为某种“灵魂共同体”似的东西,则需深入阐述与解析罢。
钱钟书在《落日颂》中对作者有一种委婉的肯定与期许,即神秘主义在诗作中的蕴含,他还勉励作者说,作者将来别开诗世界,未必不在此。此刻,在《现代诗论》中,作者以雷达的《论纯诗》对钱氏的“神秘主义”予以了回应与补充。雷达对“纯诗”这一概念的六大特征加以归纳和阐示,无一例外地沾染着“神秘主义”的力量。六大特征如下:
1.每首诗中主要的诗的特质,是由于一种神秘而又一致的实体,显现于诗中。
2.把一首诗当作诗读,若只攫得其意义,那是不足够的,并且常常是不必需的。有一种朦胧的魔力,是独力存在于意义之外。
3.诗是不能改变成合理的论文。诗是一种表现的方式,它是超越论文一切的普通形式。
4.诗是一种音乐,但不仅是音乐,它作用起来,恰如一种潮流的指导,能传达出灵魂亲密的性质。
5.诗是一种咒语,它把灵魂的状态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诗人在未用观念或情感表现自己以前,就在这种状态里。在诗中我们使混乱的经验复活,这种经验,对于明显的意识是不相接近的。散文的语言把我们日常的活动力刺激,惹起而达到顶点。诗歌的语言使它们安定,又趋向着把它们停止。
6.诗是一种神秘的幻术,与祈祷是联合的。
六大特征实际上给“纯诗”概念大致勾勒了框架,即纯诗是“由于一种神秘而又一致的实体,显现于诗中”。而诗之所以为“诗”,仅以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的“诗言志”主旨来探究的话,“那是不足够的,并且常常是不必需的”。这个观念倒不完全是与钱钟书相回应,而可以回应当时胡适的激烈论调——胡氏认为,李商隐无题诗争论了上千年,是谁也不明白的“鬼话”。
“纯诗”的第二、三个特征,实际上仍然是新月派诗人们的一贯主张,对以胡适为代表的激进的反古典观念针锋相对。至于“纯诗”实乃咒语与幻术的说法,则是对钱氏声称的一个“顽固”笃信的观念之回应——“我是顽固的,我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以为好的文学不仅要技巧到家,并且要气概阔大(LARGE-NESS)。”因为虽然神秘主义未必就不“阔大”,但既然“纯诗”已相当于咒语与幻术,“阔大”本身也只能归于幻觉或者说只是幻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技巧到家与气概阔大在“纯诗”这里都属于表层之表象,“纯诗”的形成与理解本身都只是一个神秘主义过程。
雷达最后总结说,诗的真正不可思议之处,是在许多互相矛盾的东西皆集合起来,把它组成。钱氏诗学观念中的“技巧”与“气概”在这里只是众多相互矛盾可以列举因素之一,而钱氏在《落日颂》中对曹氏诗作中“技巧”与“气概”之间存在种种矛盾,且提请注意并改善的批评,在雷达的总结陈词中不攻自破。
钱氏《落日颂》中提道,“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他大有此种气概;但是,诗人,小心着,别把读者都扫去了!你记得“狮子搏兔亦用全力”那句妙语罢?这便是有气力的不方便处。有了气力本来要举重若轻的,而结果却往往举轻若重起来。按照雷达的观点,钱氏所列举的这些曹氏诗作之矛盾,不但不是其“技巧”或者“技巧”与“气概”关系处理上的问题;恰恰相反,正是“纯诗”的本质所在,是“诗的真正不可思议之处”。无怪乎曹氏对雷达《论纯诗》一文所加的尾注中自信地断言:“纯诗”不是限于一个时代的东西,虽然这个名词和理论之创制与成立不过是近十几年事。能够了解这种理论,可以说对于一般的诗歌的理论参透过半了。
看来,曹葆华的诗作不需要“重读者”,倒是钱钟书的诗学论文需要“重读者”了。
三、失路之英雄与纯诗
无帆的船,
送来远去的山。
遗失的伞,
已堕入幽幽的潭。
有一行落款印在天边,
那是邮件地址,
斜阳山外山。
——曹葆华《巴山第一章》
这首诗是新近发现的曹葆华手稿内容之一,在诗的末尾也加上了一段类似副题的文字:献给失路之英雄。末句“斜阳山外山”的意境,古典意味浓厚,甚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李叔同作于20世纪初的那首歌《送别》。当然,说其古典意味浓厚,还是要纳入到曹氏热衷的“纯诗”境遇中去再次诠解与理解。毕竟从体裁上讲,这是一首典型的新体诗,而且仍然貌似新月派。
从无帆的船、远去的山、遗失的伞、幽幽的潭、天边的落款到斜阳山外山,这些在七行诗格律中环环相扣、节奏紧凑却最终无法企及之物,在古典意象中渐渐趋于舒缓与稳定。一个将走未走的旅人,一个渐行渐远的理想,都在时间与空间的种种矛盾对峙与冲突中,莫名其妙地达成一致。这种一致的不可思议,与“纯诗”理论不谋而合。雷达的论调,在这里得以完满呈现。
当然,说其古典意味浓厚,还要联系着诗作的副标题“献给失路之英雄”来作一次按图索骥。钱钟书对曹氏诗作最为着力的批评,无非是那一句评价: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英雄失路,才人怨命。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批评本身并无新意可言,可奇怪是,这似乎是成为评价青年诗人作品时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个屡试不爽的准则。“情绪化”成为诗人的一个标笺,好像没有一个诗人不是要喝几瓶酒、抽几盒烟、骂几句娘、掉几滴泪的。应该说,钱钟书分析得相当精准、批评得相当苛刻,无可挑剔、无从反驳。虽然撰写《落日颂》当年的钱钟书,只是二十出头的小青年,比诗人曹葆华还要小四岁,不过他写的是论文不是诗,论诗而不写诗的青年,自然又比写诗的青年多了一种主动权,因为他可以不“为赋新词强说愁”。
曹葆华《巴山第一章》中所要表达的种种不可企及之物,从字面内容上看,似乎正是在表达这种情绪化的无奈。诗人的情绪化与情绪化的诗人,本来无可厚非,但钱钟书的批评“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却着实让诗人却步,无可奈何。只有在墨雷的《纯诗》中,曹葆华似乎找到了回应钱氏批评的答案,并为那些“失路的英雄”们重拾信心与信念。
墨雷认为,若是他们都有那种力量,能把文字与全盘心灵经验配合起来,在读者心中激起同样的经验。只单独凭藉着这种力量,他们便是“纯粹的诗人”,而他们的文字便是“纯诗”。在这一观念之下,“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并不可怕,只要能激起同样的经验,曹葆华和所有青年诗人一样,都有可能成为“纯粹的诗人”。如果说“爱与哀愁”是青年诗人通病的话,也即是说是“同样的经验”使然,在这样的人生经验中,曹葆华是真诚而确有感触的。正在写诗或翻译“纯诗”理论的他,也正在经历这样的一场真实的“爱与哀愁”,并且确是有点“英雄失路”之感的。
原来,自1932年6月爱情之舟在三峡搁浅以来,这段看似无望的爱情,并没有彻底阻断青年诗人与少年女子的异地相思。在1933年10月2日《诗与批评》创刊号上,由诗人精心制作的只有他们两人署名文章的“恋人专版”不但宣示着爱情的执著,同时可能还酝酿着另一次爱情远航。1934年底,陈敬容再次离家出走,偷偷启动了这次远航。陈敬容晚年承认,第二次出走是“曹葆华寄的路费”,这份路费也极有可能就是“恋人专版”的稿费罢。无论如何,十九岁的陈敬容与时值而立之年的曹葆华从此不再是“斜阳山外山”,失路的英雄又重新找回了爱情的路径。
1935年2月,陈敬容到达北京。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纯诗”译述者与想成为“诗人”的青年女子从此开始了纯粹的新生活。但生活从来不是真空的,生活本身无法有“提纯”一说,两位诗人的新生活很快为抗战所中断。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曹葆华偕陈敬容撤归大后方,二人返回成都,次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但期间不知道确切的缘故,二人迅即于1939年春离婚。曹葆华奔赴延安而去,陈敬容则与回族青年诗人沙蕾结婚,1940年随沙蕾由重庆转赴兰州,这段仍是两位青年诗人结合而成的婚姻,维系了四年之后,也宣告破碎。1944年,只身一人的陈敬容仍然向当年逃离家庭羁绊一样,挣脱了这一次失败的婚姻,毅然返归重庆;只不过这一次再没有爱情的热望,只有清冷的哀愁。
《现代诗论》出版的这一年,不仅仅是曹葆华理论大丰收的一年,还是其人生经验迅速转变的一年,他的生活中除了诗歌、诗学与爱情之外,正是经历一次极为重大的转折,这种转折也更加接近墨雷《纯诗》中描述的“纯诗”境界:
诗歌不是像有一些人(用意是对的)所主张的一样,只是情绪(这可说是纯粹的感觉)的传达,或只是思想的传达。诗歌乃是一种整个经验的传达。不管我们(因为自己是道学的人们)是否赞成那传达出来的经验,但是这对于我们,总是一种召唤。
四、走向布尔什维克
极黑的光,
粼粼埋藏。
粼粼的泉,
养不活水仙。
盈盈的莲,
撑起、展示,
死囚背后的签。
——曹葆华《巴山第二章》
这首诗是新近发现的曹葆华手稿内容之一,在诗的末尾也加上了一段类似副题的文字:呈给怨命的才人。除了仍能让人联想到是对钱氏诗论的某种回应之外,诗中的意象与表述方式已经大为变化,新月派的优雅与技巧似乎已不复存在。
事实上,在1937年《现代诗论》出版之际,曹葆华的“诗生活”仍在继续。同年5月,他最后一部象征主义色彩浓厚的诗集《无题草》,由巴金编入其主编的《文学丛刊》,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3月由太岳新华书店印行了一种苏联作家M.佐琴科所著《新时代曙光》,中译者正是曹葆华。很难想象,曾是苏俄斯大林时代著名讽刺作家的原著者M.佐琴科,这位最终在专制时代被剥夺话语权(1946—1948年联共(布)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中,有将佐琴科开除出作协的决定)的奇特作家却曾经写过类似于《新时代曙光》这样的颂歌式著作。恰恰是这样的苏俄主旋律著述,作为俄国文学的指示牌,让曹葆华的诗歌创作、诗论研究在这一时期逐渐退居次席,他开始成为一名专事俄文译述的作者。1939年奔赴延安之后,苏俄文学那“粼粼埋藏”的光开始闪耀于他的视野之中。
1941年9月,曹葆华翻译的《斯大林与文艺》,由新华书店印行出版。作为“鲁艺丛书”的一种,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曹葆华彻底结束文学生涯,正式进入苏俄政治理论翻译的专业生涯。从1941年开始,准确地说始于1939年的延安,诗人曹葆华、诗学研究者曹葆华不复存在。
在此后三十余年的专业译述生涯中,“曹葆华”这个名字在版权页中的出现,皆是以“译者”身份一掠而过。虽然仍是与那些舶来文字与思想打交道,仍然是将这些看似新奇的理论推介出来,但作为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于译者而言,已不再具有任何特别的诗意与激辩的争议。在这些曹氏译述中,有60后、70后读者熟悉的马恩列斯著述多种,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高尔基的《苏联的文学》、普列汉诺夫的《没有地址的信》等等。
而1945年12月6日,在上海美军俱乐部作演讲的钱钟书开始在公众场合谈论“纯诗”,演讲的题目却是《论中国诗》。时年三十五岁的他在演讲中列举了格雷与歌德的诗篇,并声称这些诗篇的“口吻情景和陶渊明、李太白相似得令人惊讶”。随后,他得出结论说,爱伦坡的诗法所产生的纯粹诗(poesie pure),我们诗里几千年前早有了。所以,你们瞧,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特别“中国”的地方。
附录:
新近发现的六页曹葆华诗稿内容简介
六页诗稿以毛笔书写在中式宣纸信笺背面,四页如上文已述,另两页内容如下:
第一页:
君问归期未有期(归期。七行),巴山夜雨涨秋池(巴山夜雨)。何当共剪西窗烛,(剪烛西窗),却话巴山夜雨时(巴山二夜雨二)。
七首。致象征主义者?纯诗之实验或神秘主义者致哀。
第二页:
归期一章(注:似乎没有写完)
看一颗裴翠/碾碎了脚下的蝉蜕/笛声在关外吹/你用指尖拈出花间的灰??
曹葆华
曹葆华(1906-1978),四川乐山人。曾就读于清华大学文学系,1931年入该校研究院。著有《寄诗魂》、《落日颂》等诗集,译有梵乐希的《现代诗论》、瑞恰慈的《科学与诗》等。1939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专职翻译马恩列斯著作。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翻译组长、编译处副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译有《马恩列斯论文艺》、《苏联的文学》、《斯大林论文化》、《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