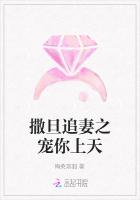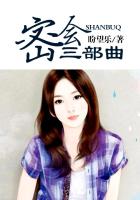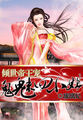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当代诗歌中的叙事与抒情
其实,这个标题也可以写成“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但含义却会大不一样。“说的”和“唱的”指的是说和唱的内容,而“说得”如何,“唱得”如何,指的是说和唱的方式和形态。叙事性问题在当代诗歌理论中已经说得太多,但是其中的关键却并未深入涉及。似乎诗歌中的叙事仅仅是对小说等叙事文体的靠拢。
我在这里想要探讨的有两个问题: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便是所谓的“叙事性”的问题。所以就有“说得比唱得还好听”这样一个题目。这个“唱”显然就是1989年以前,主要是从70年代末甚至60年代末过来的现代诗的一些传统和以个人主体的抒情为机制的。与之相对也就是许多批评家认为相对立的(即使不是那么明显的对立,至少也是不同的)一个方式,即在诗中融入了许多叙事的方式,而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主观自我表现的机制。我们都知道“诗”是和音乐非常有关的(在文学中它和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诗中的音乐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这次演讲的主标题本来是“从咏叹调到宣叙调”。希望大家能对音乐感兴趣,也许我是多虑了。因为我本身对西方的古典音乐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想到在歌剧中有一种“咏叹调”,它是靠非常旋律性的方式唱出来的。那么另外一种(其实也是“唱”并不是“说”,和“说”还是不同的)就是在比较旋律性的主要唱段之间,用不那么带有旋律性的方式唱出来,就是“宣叙调”是带有那么一种“说”的方式的。它其实还是一种“唱”,但是它和“咏叹调”的“唱”是不一样的。它不同于京剧里边的(京剧里边当然也有相对于“咏叹调”的唱腔),它不是“道白”,还是一种旋律(当然这种旋律还是不如“咏叹调”那么明显)。
下面呢,我想重点谈一谈很多批评家在当代诗歌流变中所发现的,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风格到90年代诗歌主流风格的变迁:从抒情到叙事的(模式的)变化。比较早对这一问题提出看法的应该是程光炜编的那本著名选集《岁月的遗照》的序,不过我就不念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那篇文章。他先提到了叙事,90年代诗歌的一个重要写作策略,也提到了叙事功能之中需要警惕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他里面谈的是比较全面的),而很多人恰恰忽略了其中要我们警觉的话语。“当人们热衷于谈论具体、准确,谈论叙事功能,谈论词语的创造力,实际是在谈论语言的工具理性。”这是一个很学术性的说法。“工具性”这个词应该是个比较贬义的意思,一种语言去机械地表达,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那么如果是这样去理解的话,它并不是对那种抒情性的一种纠偏,而是走到诗的反面去。我想我们这样引用一些文章,还不如来看一些诗更为直接。
芒克有一首诗,叫《阳光中的向日葵》。我先念一下:
你看到了吗
你看到阳光中的那棵向日葵了吗
你看它,它没有低下头
而是把头转向身后
就好像是为了一口咬断
那套在它脖子上的
那牵在太阳手中的绳索
这首诗我觉得是可以用一种“咏叹”的方式唱出来的。在他的那个年代里,大家知道芒克自己虽然没有歌唱的才能,但是他的两个朋友有——多多和根子,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诗人。现在已被埋没的诗人是根子。大家都知道多多了,而根子并不为人所知,主要原因是他后面没有再写。70年代初的时候,多多是受了根子的影响才开始创作的。根子后来考取了中央乐团,他是那种特别浑厚的男低音,唱得非常好。他去美国后没有继续从事声乐的活动,而是去电台当播音员。唐晓渡一听那个足球比赛就说:“嘿,那不是根子的声音吗?”多多也是对音乐非常感兴趣的,也是一位意大利歌曲的爱好者。还有一首,是90年代以来比较晚近的诗,大家来看看它们在诗歌的表达方式上有什么区别。随机地挑一首,刚才念的是《阳光中的向日葵》,那我就找一首臧棣的诗(我觉得他的诗比较有代表性)——《反驳》,没有什么具体、具象的东西。
第一段是以“说”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其实我想说的是,“叙事”这个词意思是去说一件事,但臧棣这首诗里难道有一个事情吗?我们在说到叙事这个问题时,其实有一点是比较可疑的,因为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他在说,但实际上这个“事”本身并不是很重要。我今天说的是“从咏叹调到宣叙调”。我要讲的是大家看到的“叙事”,并不是要把一个事情说出来,而是在这个诗歌中以一种语态来说。所谓的“宣叙”是一种说的方式,不是说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用“叙事”这个词来描述1989年以来当代诗歌的一个总的面貌,我觉得是有一些偏离的。我更想用的一个词是“陈述”。陈述是一种语态,这个词语我想没有错。用“陈述”来代替“叙事”我觉得更加准确。诗的叙事性绝不是指一首诗的叙事功能。其实这个问题臧棣也说过,而且很多谈到诗歌叙事性的文章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大家一直没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但是有一点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叙事并不是一切”。很多人的文章(包括程光炜的文章)确实具有某种先锋性、叙事性,但是呢,如果过分夸大语言功能的话,比如说古典的、抒情性、意象的深度,则是不可取的。最近,有一篇文章,敬文东的,也认为抒情才是古今中外诗歌的传统,具体作品则在这两者之间偏移。原因就在于他感觉在这个诗歌之中,所谓的叙事不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我就在不断地想,谈论1989年以后的中国诗歌的问题,比较关键的究竟是什么。因为这个差异肯定是有的,所以谈到了这两首诗的比较。另外有一首,应该不是我随机取的,还是和臧棣的一首诗比较,这两首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说,有一首多多的诗,1973年写的,叫《致太阳》,这首诗现在看来也还是非常好:
给我们家庭,给我们格言
你让所有的孩子骑上父亲肩膀
给我们光明,给我们羞愧
你让狗跟在诗人后面流浪
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劳动
你在黑夜中长睡,枕着我们的希望
给我们洗礼,让我们信仰
我们在你的祝福下,出生然后死亡
查看和平的梦境、笑脸
你是上帝的大臣
没收人间的贪婪、嫉妒
你是灵魂的君王
热爱名誉,你鼓励我们勇敢
抚摸每个人的头,你尊重平凡
你创造,从东方升起
你不自由,像一枚四海通用的钱!
题目叫作《致太阳》,那么“太阳”基本还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因为“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劳动/你在黑夜中长睡,枕着我们的希望”还是非常正面的、肯定的、光明的。它其中也有“给我们洗礼,让我们信仰/我们在你的祝福下,出生然后死亡”,这里面就有一些非常悲观的情绪出来了。我是说这首诗里面对太阳的礼赞并不是和当时的很多诗歌一样:有一种简单的太阳的象征。多多这首诗对那种宏大的象征其实是有所质疑的。其实,很多芒克的诗,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有很多“太阳”的意象,比如说“太阳升起一枚血淋淋的盾牌”。把“太阳”这个意象和“血淋淋的盾牌”联系起来,等于对这种象征有所颠覆。在多多的这首诗里面,它没有一个明显的颠覆,在整个抒情中我们可以看见它有一种很强烈的意愿在里面:“给我……”“给我……”相对应的,我就看到臧棣的一首诗,叫作《原始记录》。它也用了许多“给我……”,但是它是从不同的声音开始的:
椅子说,给我
一把能遮住他们的伞。
但除了猛烈的羞怯,
他们还能在哪里泄密呢?
雨说,给我一扇玻璃后面
蹲着一只黄猫的窗户。
智慧说,给我三个鸟蛋,
我要帮助他们熟悉
速度不同的飞翔。
木偶说,给我一支铅笔,
我想记下这些吩咐,
好让其中的傲慢免于晦涩。
晦涩说,给我一面已经打碎的镜子,
或是把反光的语法
直接传授给他们。
桌子说,给我另一种海拔,
我就告诉他们用四条腿
如何区分坡度和制度。
我就先念这么多,最后是:
轮到我时,我说,给我
我现在就想要的东西——
两斤尖椒,四斤洋葱,三斤牛里脊,
因为我眼前的这些盘子都空着,
我得做点什么来填满它们。
这当中有什么区别?它也说“给我……”,在这首诗里,它不是以一个抒情者的身份来说“给我……”,而是以他者的声音。“雨说……”、“椅子说……”……这是选用别人的话,一种引述,带有一种陈述的因素在里面,不是把“叙事”当作一个贯穿的东西,而只是一种陈述。我的意思是说,在很多诗里面,并不是把抒情的因素剔除掉了。我们要警惕简单的二元论,这个不对就把这个去掉,其实很多当中是包含,你挪用了一种方式,但是你走的是一种偏离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这里我们也会想到拉康说的“无意识是他者的语言”,如果说诗是无意识的,那么它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从他者的声音中创造的。
同样的,刚才说到的这个“象征”的问题,有一个非常具有理论性的问题可以在这里探讨,就是在美国的后结构主义中,德·曼写过几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时间性的修辞学》。它探讨的就是“象征”和“寓言”的问题,对这个“象征”提出了疑义。他认为“象征”是“虚幻的同一”,“寓言”是“花园”,非常有时间性的问题。一个例子就是卢梭在他的一本小说中提到的,大家都认为这是卢梭对应他内心的一种向往,但他举了很多例子,然后觉得这个“花园”是一个很人工化的东西,这个意象是通过和其他文学作品中不同花园的意象比较获得意义的。它无法和“花园”本身的意象获得一种意义的重合,和大家普遍的理解状态无法同一。“寓言”,他说“是一种符号”,是“一个无法获得与先前的符号相一致的符号”,相对于象征的、虚幻的、破碎的,它更具有动感,更有暧昧性、多义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原始记录》这首诗。我们的阅读习惯是喜欢揣摩这首诗在说什么:“为什么这些东西说这个?”这其实都有关系,比如说:“鞋说,给我全世界的牛皮,/或者,给他们都换上飞毛腿。”那显然,这个“鞋”和“牛皮”是有关的。牛皮“换上飞毛腿”,鞋的功能就在这个牛皮化的飞毛腿中获得自己的本质,好像是看懂了。但是其他的呢?“纪念说/给我一个角落,我想知道/语言到底能结多大的网。”这又是什么意思?那可能是说“蜘蛛网”。那“纪念”又是什么?可能是蜘蛛网式的被人遗忘的东西。你把这两个联系起来,我又看懂了。但是这又和鞋有什么关系?你还不是很懂。这么多声音,整个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非常愚蠢的。“所有问题都是有有机的意义的”,这个想法你要是质疑的话,你会觉得这首诗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是说各个不同的物所说的愿望,可能和诗人主体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一种所谓的“异质”(文化批评常用的词汇)。像福柯所说的“异托邦”,不同的东西在一起,大家能够互相容忍。看一下福柯《词与物》的序言,里面举了博尔赫斯的例子。不同的东西在一起,你并不指望它们给你确定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陈述”往往是陈述了一件无法陈述的事情,是对一种不可能的叙事。在异质或“异托邦”的事物中,你会发现一种冲突,一种不谐和,而这种东西正是一首诗歌所要揭示的。因为诗歌应该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东西,而感性的东西往往并不是逻辑、理性的东西所能规范化的。我解释一首诗,没有用一种道理去规范某种方式。否则,诗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之所以还用这么多理论,只是要用它们来说明一些问题。其实在念诗的时候,大家如果不是念文学的或搞文化批评的,你不用搞清楚它的意义所在(因为诗是感性的东西)。从我的角度看,运用理论不是说应该如何来阅读诗,如何来怎么样。要是那样,诗歌就完蛋了。你要从感性的方面说这首诗好,这样你的写作才是有意思的。你再看到一种理论,就会产生一种认同感。
所谓“叙事的不确定性”也不是我发明的。应该是唐晓渡的诗歌评论里面的。在他对翟永明、陈东东的评论里,其实也说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词,其实也比“叙事”好,是“叙述”。姜涛的一篇文章里(我现在用的都是你们北大老师的文章)用的是“叙述”。我觉得这个词更为准确,而且我认为我们俩对叙事性的看法比较相近。“与其说是某种既定的‘物’被语言所触及,毋宁说物是文本自我与周遭历史现实间的相互修正、反驳和渗透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并不吻合,而是充满冲突又不断渗透的过程。他还说:“90年代诗歌的本质不在其叙述中的叙事性、及物性或本土化等等写作策略,而恰恰存在于写作对这些策略的扰乱、怀疑和超越之中。”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扰乱”、“怀疑”和“超越”。不是盲目地运用“叙事”,而是应该颠覆这种“叙事”,我觉着只有这样的诗,才是比较成功的。
再比较一首啊。陈东东在80年代特别具有象征性、咏叹的一首诗(我没有当面和他说,我非常喜欢他现在的诗,这首诗相对就太简单),叫《点灯》:
把灯点到石头里去,让他们看看
海的姿态,让他们看看
古代的鱼
也应该让他们看看亮光,一盏高举在山上的灯
灯也该点到江水里去,让他们看看
活着的鱼,让他们看看
无声的海
也应该让他们看看落日
一只火鸟从树林里腾起
画面感很强,但是那些意象的意思是十分明确的。把灯点到石头里去,好像要用一种光明去照亮不可能光明的地方、窒息的地方,由此产生了海的广阔意象,落日啊,火鸟啊,都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这个象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我想要比较的是他最近几年写的诗——《月全食》:
旋转是无可奈何的逝去,带来历程
纪念,不让你重复的一次性懊悔
真理因回潮
变得浑浊了
向西的樱桃木长餐桌上,那老年读者
摊放又一本剪报年鉴它用来
备忘,仿佛《逸周书》
像卫星城水库坝上的简易闸
每一个黄昏,当邮差的自行车
经过闸口,花边消息就抬高水位
——“人怎么才能够
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
这首诗你很难捕捉它某一个意象,或是它某一类意象所要表达的确定的东西。我觉得陈东东要是在80年代写这首诗,就会有别的处理。月亮作为一个公众化的意象,让你读这首诗时有一种警惕:对公众化的象征符号带有解构策略的使用。它这个里面实际上所说的也不像他原先说的“把灯点到石头里去”那样,有一种祈使句式的主观性。现在的口吻是很陈述性的,是“无可奈何的逝去”,还不是叙事,多了一个“说”,“什么是怎么样了”。它是对一个时态的描述,是所谓的“历程”,尽管这个时态是什么我们还很难捕捉。整个一首诗还是一种先前的东西,要求我们也要对先前的事物有一种经验式的准备,一种文化的准备,那么这类诗的阅读会比较有成效。像“真理变得混浊”,大家要是能仔细想一想的话,就能够捕捉到其中微妙的内容。这种“混浊”、“老年读者”、“逸周书”、“樱桃木”,都带有某种历史感,带有同先前的东西发生关联的事件性。邮差的自行车也是一个外来的形象,插入性的,而不是本来就在的,它的功能是“抬高水位”,他使老人的形象(确切地说是老人的内心欲望)发生了变化。像花边消息这一类的外在诱惑,也是扰乱性的。总而言之,有许多不同的、具有杂质的事物在不断对另外的事物产生作用,扭曲,篡改,驱动,引发,等等,而不单是单一的象征意象在自身中起作用。
我再来介绍另外两首,一个是你们另外的一位老师——胡续冬的,这首诗你们应该都看过,叫作《云是怎样疯掉的》,先念第一段:
小鲫鱼翻炸片刻,佐以
泡椒、芹菜,形成一小片
快乐的云。我们体内的三伏天
在专心地煨汤,偶尔
开开小差,让一阵暴雨出丑,
让闪电错误地切除掉
我们折叠在盲肠里的翅膀。
但云总是,在雨后,用鲜美
使一切恢复正常:鱼肉
代替难咽的未知堵住了我们
琐碎的嘴。好了,云
穿过了我们的滋味。云在静中。
整个第一段贯穿的意象还是“云”。从这个意象你会捕捉到它和以前的象征主义的或抒情主义的有什么区别。因为它说的是很日常的东西,很像炒菜的过程。这种联系,若和我所说的你应该具有的一些“前理解”联系,会更有成效。比如,顾城有一首诗,大家可能都会背,“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它表达了一种人性中的缺憾吧。即你在和自然交流的时候感觉很贴近,跟我交流的时候可能就很遥远。一旦破译出来,你会觉得这首诗索然寡味。这个“云”的意象其实还是很复杂的,除了顾城的诗,在传统诗歌“云”这个语库里面,“云”并不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东西,不像月亮。本身含混的意象被胡续冬运用后就更加含混了,一开始就变成一种错误比喻的东西,自然的意象错用到世俗的日常经验上来,但是日常经验本身其实又的确是人性自然的一部分。诗里明显地用到了“出丑”和“错误”这样的词语,指向经验中那些难以捉摸的部分。那么这种含混性或不确定性,是当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就不再把这些意象当作象征的、本质的、中心的东西来对应于某种内心的体验,而是对已有的对应方式的一种反思。对“云”我们会有很多理解,但它是否会有明确的含义?这些都是可以探讨的。对于当代诗来说,它没有给你一个确定的、像顾城诗那样具体说出的含义,这才是可以挖掘的。
对于叙事学,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秦晓宇在论坛上贴的一个帖子。我想他对理论的运用还是比较熟练的,尤其是对诗歌的感觉非常好,否则他就不会喜欢我的诗了。但是对他的理论立场我想提出一些质疑。他的这个文章写得比较专业化。他说中国诗里有三种特质:一是主体的在场性,即诗人在写作中是在场的,而不是有距离的。二是自我的本真性。我是本来的“我”,达到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澄明”的境界。孙文波不惮于以粗话入诗,但“他的粗口有民间语言的纯正健康,姿态性的文人语言既达不到那样的质感力度,也会被衬得猥亵”(席亚兵语)。比如:“哦,张秋菊、李素芬,什么屁样子嘛;爱她们就是对母猪表示敬意。”(《醉酒》)他说粗话表现了自我的本真性,我觉得很可怀疑,似乎优雅成了伪装。还有:“使死亡可以成为嘲弄的对象,不怕你,滚你妈的蛋!”(《起来》)这个就真的是本真性吗?有些诗人在日常生活里表现出一种“伪粗俗”,故意说些脏话来显示放浪。孙文波肯定不是这种情况,但是用本真性概念来说明这个问题是比较值得怀疑的。第三个是说语言的日常性,即语言还原到了它本身。比如孙文波的一首我们都非常喜欢的诗——《上苑短歌集》:
人民就是——
做馒头生意的河北人;
村头小卖铺的胖大嫂;
裁缝店的高素珍,
开黑“面的”的王忠茂。
村委会的电工。
人民就是申伟光、王家新和我。
秦晓宇说这是对“人民”这个词的还原。“这里经过还原的人民不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及物的……”“还原后的人民成了一个活的词。”这个词本身能够还原吗?“人民”这个词这样理解就绝对地对了吗?也许所有这些具体的人都是一些隐喻。“人民”这个词能让这几个具体的人就这么了结吗?我觉得这还原有点乌托邦化,一厢情愿。因为不是所有的语言都能让诗人去改造的,诗人的任务也不是去改造某些不对的意义。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深入我们的思想中了。这首诗之所以能打动我,是因为我觉得它把“人民”这个词拆解掉了。我和秦晓宇的观点一致:这首诗写得好!但是角度完全不一样。我可能是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黑‘面的’”可能处在一个灰色地带,虽带有正面的人民范畴,但似乎不能算得进去。可见,“人民”这个概念不是同质化的,而是刚才臧棣那首诗中(我所用的)异质化的、无法被还原为固定的前理解的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它起的是质疑的作用。
我这里穿插别人的一些论述。别人问桑克:“据我所知,在90年代中期以前你是一个相当纯粹的抒情诗人,有自己偏爱的主题和题材,但在你近期的写作中却融入了叙事和讽刺的成分,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桑克说:“是绝望。”非常悲观主义的回答。这不是说叙事要呈现出非常本真、本来的面貌,而是说对象征的自足性丧失的绝望,对你想象的某种同一化的绝望。
这里还有两个和叙事有关的概念:在场和及物。在场一直被当作一个极端主观主义的观念,好像诗人在那里了,能够依赖他的洞察力,其实他是高高在上的。孙文波这首诗如果有在场的话,是在当中反思自我的形式、概念等,如大词,像“人民”这样的词。所以“在场”在这里不是主观主义的东西,它变成了对主观主义的质疑,作者把自己都放进去了。另外一个是“及物”,似乎又与现实主义、客观主义有关。去年年末开了一个杨炼的作品讨论会,很多批评家提出“杨炼的诗还停留在早期朦胧诗的阶段”,缺乏及物性。这涉及我们如何看待“当代”的问题,其实非常微妙。我不认为一定只有写当代身边的东西才是及物。杨炼的写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记忆和过去的经验,去年诺贝尔奖的得奖作品不也是写集中营的吗?但这都不是关键。当代现实,一进入诗,也都是隐喻。在很多诗里面你很难看到现实有直接的参与,臧棣自己对这个事情都有说法,我觉得他这个说法非常好:“因为说到底,我们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才知道存在着什么样的事物的。”我们不能离开修辞的东西来谈“物”,否则就不是诗的东西,而可能是一篇报告的东西。他说:“我愿意想象诗歌的本质是不及物的。假如我的诗歌在文本上看起来像是及物的话,那是因为我觉得及物会引发一种风格上的富于变化。认为诗歌必须要反映或回应现实的观念,其实是一种极为专断的美学主张。我的诗歌会触及现实,但那不会是他们的现实。”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诗人我们没有提到,他是我最后一个要提到的,是肖开愚。他的《学习之甜》分三段,第二段叫《警察的第二个问题》。这是比较现实的。因为那几年我见过他几面,他在上海确实受到了一些骚扰。这首诗写的和那时差不多是一致的,几乎可以看作现实主义的,但其实还有隐喻的问题。这里有一个虚拟,是以女性的口吻来写。还有“老师”的意象,可能和管制有关。这些意象性的东西,的确是被叙述出来的,但往往带有很强的隐喻色彩。有的你不可能说得很准确,因为带有多重性和多义性。
我在说了这么多之后,还是要避免一个简单化的因素,就是这样一种跨越、变迁绝对是80年代到90年代文学样式的变化。其实1989年以前就有那么一种对“象征”有质疑性的写作方式,但是那种陈述性的或叙事性的方式并没有形成。孟浪《靶心》里面就有一种不可能的东西,比如象征自由的飞鸟被“冻住了”,被当成了射击的靶心。90年代诗歌里面,许多意象就被融入陈述的过程之中。我们所说的寓言不是固定的,它是通过与别种语言发生关系而获得意义的。胡续冬还有一首诗叫《亚细亚的孤儿》,我就不念了。“亚细亚”指的就是“太平洋”大厦,或者是淹没在太平洋里的那块陆地。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前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罗大佑有一首歌叫《亚细亚的孤儿》等等。你会发现为什么德·曼说寓言中的寓意来自与前人表达不一样的地方。罗大佑的这首歌词也不是自创的,而是来自台湾吴浊流的一篇社会小说。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历史感中探讨民族的悲情。那么在胡续冬诗中你看到的是IT业的生活或是后现代的生活在当下的状态,在网络时代、全球化世界里我们的“亚细亚”处境,和前文本比如何具有差异性(或者德里达说的“延异”,也是从时间性而获得的),什么是“亚细亚的孤儿”这个原来的象征的多重意味,也就是寓言性,这才是更重要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它表达的是某个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变迁——从咏叹调到宣叙调?因为80年代早期抒情的写作占主导地位吧。后来为什么又是陈述性的、叙事性的占主导地位呢?其实每一个时代的诗歌还是和那个时代的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相关的。8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的主导文化声音其实还是很诗意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带有象征意味的有点神圣化的文化状态。每一种写作都会有它的对象。当时的写作状态和朦胧诗的表达形式是有关的。哪怕是北岛说的:“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我要做一个人。”这种语态本身是很英雄主义的。相反到了1989年以后,整个社会状态就变了,神圣性消失,而许多世俗化的东西出现,似乎这是追求中的实际问题。这也可以解释散文在90年代兴盛的原因。因为大家都不太……今天这个讲座来的人也不算太多。(笑)我想这个讲座要是放在70年代末、80年代的时候,会在大礼堂里讲,会有黑压压一片激情澎湃的听众。诗好像在走向没落,话语方式都好像改变了,不再是很高调的声音。诗里边有对话的对象,并不是站在外面,只是用消解的方式来对待主流文化,它是有对象的,也是有来源的。所以诗里面许多都是无意识的流露,这就是为什么说是他者的声音。
(2003年4月14日在北京大学三教107室的讲座,录音整理:卫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