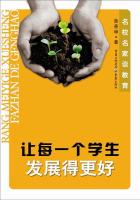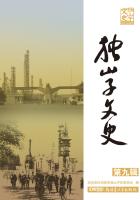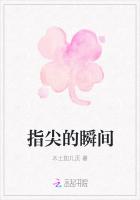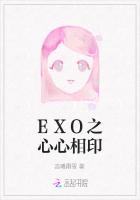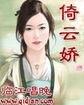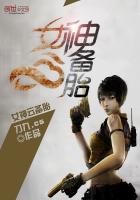“家族、宗族聚居”与“聚族而居”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此,杨际平等先生在《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一书中曾对这两个概念作了明确区分,指出:“所谓‘聚族而居’,从语义上讲应该是人们在宗族观念的支配或影响下,有意识地将分散居住的族人聚集起来,集中居住。它有个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而宗族聚居,则只是反映族人住处相对集中这一客观现象。它可以是人为的,也可以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聚族而居”作为一种行为,受家族、宗族观念的影响很大,而“宗族聚居”只是反映一种客观状态,是古代农业社会的自然形成,与宗族观念的强弱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因此说,“聚族而居”与“家族、宗族聚居”在行为状态上和与宗族观念的关系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家族、宗族聚居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自然形成的一种居住状态,其存在具有普遍性,而“聚族而居”则不然。就此我们考察了史籍中“聚族而居”一语的使用情况以作印证。
真正的“聚族而居”很罕见,史籍中也罕用此语。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传世文献言“聚族而异”,仅见员例,这就是《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庆封逃亡于吴事:庆封既杀崔杼,益骄,嗜酒好猎,与庆舍政,但又与庆舍等有矛盾。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缘源缘年,齐景公三年),庆封出猎,庆舍与栾、高、陈、鲍之徒攻庆封宫,庆封奔鲁,鲁不纳,又奔吴,“吴句余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史记》卷猿圆《齐太公世家》亦记其事,称:“吴与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说的都是吴“聚”庆封之徒“而居之”朱方。此后,正史记“聚族而居”亦仅见于《宋史·赵汝愚传》与《明史·鸡笼列传》。《宋史·赵汝愚传》载:“汝愚聚族而居,门内三千指,所得廪给悉分与之,菜羹疏食,恩意均洽,人无间言。”赵汝愚是宋太宗八世孙,汉恭献王元佐七世祖,为宗室疏属。据《宋史》卷圆源源《宗室传》记:宋宗室疏属,“宗正有籍,玉牒有名,宗学有教,郊祀、明堂,遇国庆典,皆有禄秩。所寓州县,月有廪饩。至于宗女适人,亦有恩数。然国祚既长,世代浸远,恒产丰约,去士庶之家无甚相远者。”那么,赵汝愚一支在靖康难后迁至江西余干,于此“聚族而居”应该是集中族人而居。
《明史·鸡笼列传》载该“地多竹,大至数拱,长十丈,以竹构屋,覆之以茅,广且长,聚族而居”。
笔记小说言“聚族而居”始见于《太平广记》引《原化传拾遗》载:“蚕女者,当高辛帝时,蜀地未立君长,无所统摄。其人聚族而居,递相侵噬。蚕女旧迹,今在广汉,不知其姓氏。”所记“蚕女”虽多有神秘色彩,但反映了氏族部落时期的一些情况。在氏族部落社会中,个人不能脱离群体单独生活。这里的“聚族而居”也属此义。
元明清以后的各种“义门记”、“族谱序”、“墓志铭”等才常见“聚族而居”之说,大体上都是过奖之词,而少见提供实证资料。受其影响,今人也或将家族、宗族的相对集中居住,说成是“聚族而居”。
秦汉时期被今人视为“聚族而居”的典型事例是万石君石奋。史载:石奋之父为赵人,秦灭赵,石氏徙河内温县。楚汉相争时,石奋年员缘岁,为刘邦小吏。刘邦曾问石奋其家何有,石奋对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贫。有姊,能鼓瑟”,刘邦即娶石奋之姊为美人,“徙其家长安中戚里”。从石奋与刘邦对话可知,时石奋之父已亡,石奋无兄弟,石奋未婚,家中唯有寡母与一姊。可见,石奋徙戚里时,其家只是残破的核心家庭,且石奋在戚里也并无近亲。汉景帝时,石奋官至诸侯相,有四子:建、甲、乙、庆,因石奋与其子皆为二千石,故被号为“万石君”。景帝晚年,石奋归老。汉武帝建元二年(前员猿怨年),石建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时万石君仍健在,徙居茂陵之陵里。“万石君家以孝谨闻乎郡国,虽齐鲁诸儒质行,皆自以为不及也。”有一次“内史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万石君闻之,不食。庆恐,肉袒谢请罪,不许。举宗及兄建肉袒,万石君让曰:‘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乃谢罢庆。庆及诸子入里门,趋至家”。《汉书》于此有“举宗”一词,论者即以为石氏为“聚族而居”,并进而推论《汉书》此处所说的“里门”可能即“石庆的家门”。究其实,石奋居戚里、陵里时,都只是数代(石奋及其子孙,时石奋愿园多岁,可能还有曾孙)同堂的大家庭。家庭同居乃为寻常事,本不足为怪。此时,石奋除其子孙外,仍并无其他近亲,自然也谈不上“聚族而居”。从石奋责石庆时所说的“里中长老皆走匿”看,该“里中长老”必非石庆的兄长或同姓长辈,而是异姓长辈。这也说明,石奋一家所居之“闾里”,也是异姓杂居。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作为“聚族而居”的典型实例是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李鱼川居之。究其实,李显甫七世祖李楷之孙李慎、李敦早已迁居柏仁。据史载:李楷生子缘人:辑、晃、癈、劲、叡。其中辑圆子:慎、敦;晃员子:义;劲源子:
盛、敏、隆、喜;叡圆子:勗、充。其后,“慎、敦居柏仁,子孙甚微。
义南徙故垒,世谓之南祖。勗兄弟居巷东,盛兄弟居巷西”。可见,李楷后裔至第三代时已分居四处,其中一支已迁至柏仁。下距李显甫尚有六代之遥。换言之,不迟于李显甫迁柏仁之前一百多年,柏仁已有诸李居住,为数可能还不少。并且在李显甫迁往柏仁时,与其同时代的李氏族人多未随之而迁。如南徙后的李义这一支,至其五世孙李义深、(弟)李秩廉时,仍为“赵郡高邑人”;居平棘巷西的李隆这一支,至其五世孙李密时,还是“平棘人”。可见,与李显甫世系较远的李氏均留居原地。居平棘巷东的李勗这支,其中李系和李曾两支肯定也未随迁。据载,李系五世孙李祖昇,“赵国平棘人”;李曾四世孙李士谦,“平棘人”。这就说明李祖昇的祖父李宪、李士谦的父亲李郁当时都未随李显甫迁居李鱼川。再有李均孙辈李元茂、宣茂、叔胤、仲胤兄弟,与李显甫是再从兄弟关系。李元茂父李璨,官至兖州刺史,封始丰侯。李璨卒,李元茂袭爵,官至司徒司马、彭城镇副将。从李元茂太和中有官爵的情况看,元茂不大可能随李显甫南迁。《魏书》卷源怨《李灵传》载: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书博士,后来又兼定州大中正,“坐受乡人财货,为御史所劾,除名为民”。宣茂曾孙德饶,《隋书》卷苑圆《李德饶传》载其为“赵郡柏人人”。推测李宣茂“除名为民”后,有可能随李显甫南迁柏人。另一种可能就是子孙于东魏北齐时自行迁往柏人。宣茂弟叔胤皇兴元年(源远苑年)生,太和初尚年幼,未仕之前当依长兄元茂,也不太可能随李显甫迁柏人。而可能随李显甫迁居李鱼川的家族成员除李宣茂外可能仅有堂兄弟李遵一家。史载,李遵父李综早卒,李遵子李浑为“赵郡柏人人”。说明李综死后,李遵一家与李显甫兄弟的血缘关系最近,其联系交往应该最为密切,所以在李显甫迁居时也有可能随之同行。因此说,随李显甫同迁的最多只是其弟李华、李凭和堂兄弟李遵等数家而已,不可能是“诸李数千家”同迁。而且,李显甫迁柏仁后,只是与早已定居柏仁的李慎、李敦后裔或其他李氏后裔同居李鱼川而已,这些都算不上是“聚族而居”。还有一点,西山只是柏仁西部的一座海拔一百多米的岗丘。李鱼川大体上也只是西山的一条山谷,其地面积有限,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柏仁西山李鱼川能否容纳“数千家”,也不无可疑。太和年间柏仁县的户口数不详,武定(缘源猿—缘缘园年)年间,殷州员缘县,猿缘愿园怨户,平均每县约缘园园园户。时南赵州远县,猿圆园源远户,每县平均也是缘园园园户。既然武定年间整个柏仁县只有缘园园园户上下,那么,此前缘园多年,李显甫又怎么可能率“诸李”数千家从平棘迁入柏仁的西山李鱼川呢?况且,李显甫迁入柏仁西山时,柏仁西山并非荒芜人烟之地,那里早已有胡汉各族杂处。若此,李显甫迁入柏仁西山之后,也只能与原住各族居民共居杂处,想要专门清出一大块地盘供李氏居住,谈何容易。
还有南朝刘宋时吴兴武康人沈庆之之例。史载:沈庆之“有园舍在娄湖,庆之一夜携子孙徙居之,以宅还官。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焉”。其中“携子孙徙居”,说明沈庆之为大家庭同居;“悉移亲戚中表于娄湖,列门同闬”,按字面理解,应是家族、姻亲“悉移”娄湖。实际上,沈庆之的家族、姻亲又不可能都移居娄湖。沈庆之兄敞之,兄子僧荣等,弟劭之,弟子文秀等,或已卒,或仕宦在外,都不可能随迁娄湖。《沈文秀传》载其为“吴兴武康人”,也确证沈劭之一家并未迁娄湖。史传所见的沈庆之兄弟仅此两人,都未随迁娄湖。沈庆之从弟沈法系,历任始兴太守等职,也不可能随庆之迁娄湖。沈庆之从父兄子沈攸之,《宋书》卷苑源《沈攸之传》记其“吴兴武康人”,说明沈攸之亦未随庆之迁往娄湖。沈氏为吴兴武康大姓,沈法系、沈攸之等也不可能弃其家业而迁娄湖。沈庆之徙居娄湖时,已经苑园多岁,子孙一定很多,姻亲也一定很多。“娄湖”一地,据《元和郡县志》卷圆缘《江南·润州》载:“(上元县)县东南五里,吴张昭所创,溉田数十顷,周回七里。昭封娄侯,故谓之娄湖。宋时为苑”。娄湖周回仅七里,南朝宋既已为苑,则庆之所得就只能是娄湖之一部分。以此区区之地,要安置庆之全部亲戚中表,也绝无可能。要言之,沈庆之充其量只是将其子孙与一部分“中外亲表”迁往娄湖,其近亲(兄、弟、侄)并未随迁,谈不上是整个家族的“聚族而居”。总之,被今人视为“聚族而居”者,多半都只是家族、宗族聚居,而不是有意识地“聚”族众而居。许多学者未加区别地将“聚族而居”与“家族、宗族聚居”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也不符合乡里社区里家族、宗族聚居与异姓杂居并存这一客观情况。这种以“聚族而居”代称“家族、宗族聚居”或认为“聚族而居”是家族、宗族制度的特征之一的看法,极易模糊人们的视线,不但忽略了“家族、宗族聚居”这种居住关系的客观性,而且也置“家族、宗族散居”与异姓杂居若罔见,同时也人为地强化了家族、宗族观念对居住关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