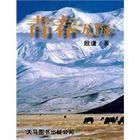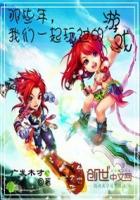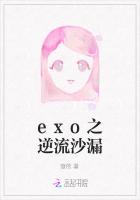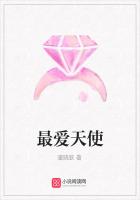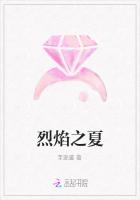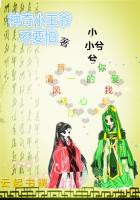电脑给人带来了太多的方便,为了随处享受这种方便,便有了手提电脑。手提电脑太贵,还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3寸盘和光盘便应运而生。只可惜3寸盘太小、光盘太浪费也太麻烦(非要有个刻录机伺候着),聪明人又推出了优盘。我们单位为广大教师做好事,每人发一个64兆的优盘,有个同事喜滋滋地把原先存在硬盘里的一个文件搬了进去。为了腾出硬盘的空间,还把那个文件删除了。等他笃笃定定把优盘打开,天哪,里面什么也没有!一百多万字的心血,顷刻之间化为乌有。用上海话说,真是“哭啊哭得出个(哭也哭得出的)”。
在敞开的互联网中,除了有用的信息和邮件,又有多少狂轰滥炸的广告和居心不良的病毒呢?今年年初,赵丽宏老师的电脑就中过病毒的暗招。一封来历不明的电子邮件生生把他的电脑硬盘破坏了,众多专家也“无力回天”。对这样的作恶者,真该骂一声“杀千刀的!”而且一定要用普通话来骂。
据说,将来的战争,很可能没有硝烟没有炮声、也不用扔氢弹原子弹,更无需劳驾科幻小说里的死光、中子弹什么的。只消通过网络发出一些指令、送出一批病毒,敌方的电脑指挥系统要么统统瘫痪,要么发出错误的指令,兵不血刃将不再是神话。不过,打仗之类的国家大事,似乎用不着我等操心。当务之急是呵护好正在为我们服务的电脑,尽管它们一下流水线就已经落伍了。总的来说,它们还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虽然有时候,它们也会劳累过度消极怠工,也会弱不禁风大翻白眼。作为它的主人,我们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假如它是一台公用电脑,你就为它的左右逢源百无禁忌百毒不侵经久耐用多多祈祷吧!
渐远的风景
一提起上海话,35岁以上的上海人大多会生出一种自豪感。想当初,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上海话也随之飞到了白山黑水、飞到了云之南、天之涯、海之角。那时候,上海话和上海知青的时髦发式时新玩意连在一起,和他们分给老乡的精致糖果连在一起。上海话,成了神秘上海的一扇窗口、一个标记。那时侯,谁的上海话里夹杂了一点点郊区口音或是外地口音,可恶的上海人马上就能听出人家老祖宗的籍贯。某次,一个大龄女青年的相亲又以告吹结束,介绍人问何故,答曰:“那男的有乡下口音”。
有一阵子,上海话的耀眼光环被南来的广东话抢走了。一时间,会讲广东话成了应聘成功的重要条件。至不济,来上两句香港腔的“国语”也是好的。记得有个到东莞做生意的女同学,就曾在电话里问我“垒(你)现在在忙什摸(么)?”我分明记得,她是湖北人。
当上海普通话在春节晚会上出尽洋相之后,传授上海话的夜校却悄悄地开张了。前些时,我甚至从报上读到这样一种说法——会讲上海话也算一项技能。不管是不是开玩笑,上海话总算是苦尽甘来、“收复失地”了。然而,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欣喜,就惊愕地发现,从上海儿童和上海青年人嘴里吐出来的“上海话”,已经面目全非了。
他们把“我”念成“吾”,把“调一调”讲成“换一换”,把“微(v)波炉”说成“微(wei)波炉”,把“太阳(tayang,沪语读音)”读成“炭(tai沪语读音)阳”、把“一个钟头”说成“一个小时”……我的读初中预备班的女儿,还经常用“上海话”对我说“妈妈,刚才吾……”呜呼!
方言专家下过一个定义:严格地讲,上海方言是1981年以前长期稳定的市区地域内居住的人们所使用的一种吴方言。也许,正因为在成长期青春期遭遇了经济和文化的长期禁锢、经历了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35岁以上的上海人才能把上海话说得如此纯正。而年轻一代从托儿所幼儿园开始,就受到“要讲普通话”的谆谆教诲。那些惟恐自家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们,也不大敢在家里跟孩子说上海话。我的一个邻居,甚至整天用英语和两岁半的儿子对话。我女儿的洋泾浜沪语,有不少还是从《红茶坊》、《老娘舅》那里学来的,等我有意识地跟她讲上海话,为时已晚。
生存竞争使得年轻人必须精神百倍地跟外地人讲普通话、跟外国人说英语。升学竞争更逼得我们的孩子成天埋在题目堆里,他们哪里还有闲暇讲上海话?语言是需要语境的,一旦失去生存的环境,这种语言的前景就不大美妙了,尤其是方言这种口头语言。我不敢想象,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代将会说出什么样的“上海普通话”和“普通上海话”?
套一个最俗最滥的形容词,对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而言,上海话就是她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道令上海人自豪过骄傲过的风景线,正在离我们渐渐远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也许,和她当初的兴盛一样,上海话今天的嬗变,只是这个国际大都会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程中的一颗流星、一片浪花?
尘缘
晨起扫地,看似光可鉴人的地板上又扫出不少灰尘,不禁有点佩服终年整洁的邻家。除了夏天,他家很少开窗。其实紧闭的门窗对室内的卫生毫无好处,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螨虫之类的寄生虫最容易繁殖。
细细想来,生命发端于海洋、根植于泥土,号称万物之灵的人,同样来自尘土。如果说水是生命的源泉,土就是生命的依托。“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自从这首偈诗流传开来之后,尘,就成了一个贬义词——比如堕入红尘、风尘女子、比如甚嚣尘上。形容某人贪生或恋栈,也总说他尘缘未了。尘,毋庸置疑地成了俗世生活的代名词、精神生活的对立面,给人一种不洁净不高尚的感觉。然而,又有谁能逃开尘世的羁绊俗世的喧嚣呢?在滚滚红尘之中,我们谋生养家、奉老哺幼,为琐碎的小事忙碌、为众多的纷扰担忧。那些出将入相做皇帝的,也天天耍阴谋弄诡计,甚至炼丹佞佛、妄想长生不老,恋恋不舍这个“堕落的尘世”。
但是,倘若人们永远沉湎于热闹繁华的物质生活,人类的精神就会日益猥琐,世界也将变成以武力和金钱取代公理的丛林——充满衣冠禽兽的丛林。于是,在人世的兴衰荣枯迭替更换之间,在人间的斗转星移悲欢离合之后,恢弘的思想、高深的哲学产生了,博大的宗教和高雅的艺术形成了。她们担当起了提升人类精神生活的重任,使我们能够欣赏和思考物质生活以外的东西。虽然她们有时会被铜臭所雇佣、被权杖所裹挟……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同是讲禅的偈,我以为,这一首更实在。尘,是人生的沧桑、是俗世的舞台、是真实生活的写照。再抽象再空灵的精神世界,也必须附丽于俗世的物质生活。所谓尘缘未了,正是对现实世界还有所留恋、有所牵挂,有所期待、有所希冀……在茫茫人世间,面对五彩缤纷纷至沓来的诱惑,怎样既不隔断尘缘,又保有一点真诚和善良、保持一份淡泊和超脱、不让自己变得急功近利老奸巨猾,变得利欲熏心寡廉鲜耻,远比四大皆空心如缟素地活着艰难。
不知不觉之间,一套小小的居室已经清扫完毕。阳光从敞开的窗口照进来,在温暖而透明的光束里,无数细小的灰尘快乐地上下翻飞。望着它们,我不禁想起多年前听过的一首歌,最后一句歌词的旋律我一直记得清清楚楚:“一切都归于尘土,究竟是谁赢谁输,我已不在乎。”在无垠又无限的宇宙里,一个一个具体的人,多么像一粒一粒短暂渺小飘忽不定的尘埃。倘若每个人都能跳出一时一地的得失,站在宇宙和历史的高度俯瞰一下审视一下在红尘中寻寻觅觅磕磕绊绊悲悲喜喜的自己,也许,人类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愚昧和贪婪、专制与凶残……
在变为尘土之前,让我们继续爱、继续恨,继续迎接并享受生活中的一切。尘缘,实在是很难了的啊!
放一放我们的疲惫
难得休息在家,整理整理房间,打扫打扫卫生。忽然发现,酒柜上又堆满了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有女儿的头箍、她弃用的笔袋,我的咳嗽药水、丈夫的通讯录、启封的牛肉干,还有一张铜版的彩色广告纸……
我家原来的凌乱之处是女儿的小书桌,这张小书桌实在太小,女儿便常常在餐桌上做功课。小书桌放在客厅门口,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全家人放包、搁杂物的好所在。直到有一天,我对那上面的凌乱状况忍无可忍,便下了死命令:除了各自的皮包拎包和书包,小书桌上一样杂物也不许放。
我的“命令”倒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杂物们却并未销声匿迹,而是转移到了床上、酒柜上、梳妆台上。跟以前相比,家里更乱了。我一边整理,一边叹着气。
反过来想想,倘若样样东西都井然有序,家与兵营与宾馆还有什么区别?或许,我们该容忍家中的杂物,尽管它们有悖于窗明几净一尘不染的好传统。正是它们的零星与琐碎,给我们带来了家的感觉。这些杂物沾染着家庭成员的气味,记录着主人的近况、透露出他们的消息。比如眼前的头箍、笔袋、咳嗽药水、通讯录、牛肉干和广告纸。它们并没有生命,却是鲜活生活的佐证,是家居生活中最具温馨意义的东西。或早或晚,总有一天,它们会被抛弃,被熟悉或陌生的手扔掉。但在跟随主人的那段日子里,对于主人而言,它们曾是那样的亲切和熟悉。
今天,在愈来愈紧迫的谋生的日子里,我们的家,太需要一块随意和轻松的地方,放一放我们的疲惫,搁一搁我们的委曲和压力。让我们屡受伤害的心灵在家的温馨里浸润一下,让我们绷得太紧的神经在家的柔软上小憩一回。也许,家最引人的地方,就在这些凌乱和琐碎之中。我们可以一边收拾这些乱哄哄的杂物,一边回味有它们伴随的日子和时刻。在这样的家里,我们能够卸下面具,说说真话、吵吵小架。在这样的家里,我们可以披头散发,不修边幅,不必在意仪容是否端正、风度是否翩翩。更无须注意睡姿是否优雅,大可以放心地磨牙、打呼、说梦话。说到底,再优雅再风度翩翩的人,也离不开柴米油盐。说到底,那些翩翩的举止与风度,也是根植于无数的琐碎和凌乱之上的。
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之类的故事,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之类的传统,最好还是留在成语中吧。倘若真的搬进现在的家庭生活,是不是有点儿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