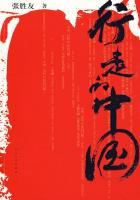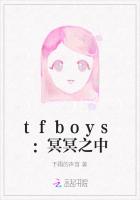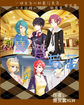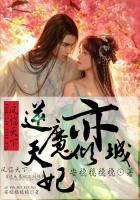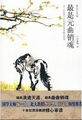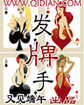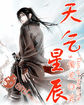(二) 唐沈亚之《冯燕传》和明陆人龙《型世言》中的《****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冯燕传》叙冯燕趁张婴外出,与其妻奸宿,适值酒醉的张婴归来,于是慌忙起身,躲在床后,头巾却落在床中。张婴因醉酒在椅子上睡去。冯燕指着头巾暗示妇人收取。妇人会错了意,却将配刀递给冯燕。冯燕认为妇人要杀亲夫,太无情义,反将妇人杀死。张婴因醉不知,第二天发现,到街坊上叫喊,被拘刑讯,屈打成招。冯燕主动向官府投案。节度使赞道:“好一个汉子,这等直气!”因上表皇上,请求赦免他的罪过。皇上也因他“奋义杀人,除无情之淫蠹;挺身认死,救不白之张婴”赦免了他。沈亚之是把冯燕作为一个讲义气的奇侠而不是罪犯来写的。后来陆人龙的《型世言》用这个故事作“头回”写了一篇《****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叙永乐间宛平人耿埴与董文妻邓氏通奸。邓氏不仅常常凌辱其夫,且与耿埴商量要将丈夫害死。耿埴觉得这妇人是个“不义的****”,一怒之下将她杀死。挑水的白大被诬认作凶手。正待处决,耿埴在法场上为白大喊冤并自首。永乐皇帝说他“杀一不义,生一不辜”(上几处引文均出《型世言》该回),赦免了他。后来他出家当了和尚,且还修成了正果。
像这样因为维护儒家伦理的需要,杀人者而得宽宥,或者说是为了宣扬儒家的某些伦理道德,有意让罪犯脱离法网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在古代小说中找出很多很多。限于篇幅,不能,实也不需再一一列举。
为什么执行法制与维护伦理构成矛盾冲突之时,小说家构筑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情感的天平往往向伦理一方倾斜呢?这与中国人的文化信仰、民俗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关联。
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百家之中,从思想影响而言,主要是儒、墨、道、法四家。后来又传入了佛教。尽管在中国,多元文化一直并存,但从孔夫子以来,影响最大的无疑还是儒家,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更一直是官方的统治思想。各学派之间固然有联系融合,更有分歧、矛盾和斗争。单从“争鸣”一词,我们不必细细证明就知道,春秋战国乃至秦代,这种分歧、矛盾,甚至你死我活的斗争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
儒墨道法等学派(包括后来的佛教)
学理上的歧见、儒家思想的成为统治思想;在强梁遍地的社会中,无奈的小民、弱者为抗衡强梁统治对墨家侠义思想的崇奉等,就是造成上述现象的深层文化因素。如果不带偏见,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儒家思想的成为统治思想,由于无奈的小民、弱者为抗衡强梁统治对墨家侠义思想的崇奉,至少从汉代开始,中国就成了一个轻法度而重礼教的国度,而中国人也多是重伦理而轻法制的人民。不仅在小说里,即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可以举很多因为某人遵从儒家的伦理道德或因所行包含侠义的因素,而得以使自己或他人减刑的案例。汉朝有个孝女缇萦救父的故事,说的便是汉孝文帝十三年时现实生活中的一件事情:缇萦的父亲有罪,被捕至长安。她也跟着来到长安,给皇帝上了一封书,说是愿意“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怜悲其意(《汉书·刑法志》),不仅赦免了淳于公的刑罪,律令也因之作了修改。这开了执行律令服从提倡儒家伦理——孝的先河。
到了唐朝,法律几经修改,已经相当完备。但太和六年,也出现了一件因孝义虽杀人而得免死的事情:上官兴因喝醉酒杀了人,逃亡在外,他的父亲被官府抓了起来。上官兴到官府自首,兴平县民上官兴以醉杀人而逃,闻械其父乃自归。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请减死。诏两省议。以为:杀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许以生,是诱之杀人也。谏官亦以为言。文宗以兴免父囚,近于义,杖流灵州。(《唐书·刑法志》)虽《新唐书·刑法志》的编撰者说:“君子以为失刑。”但这件事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皇帝因为上官兴“免父囚近于义”而赦免了他的死罪,底下的官员效法皇上岂不是理由充足?“近于义”杀人能够免死,真正的行侠仗义者犯死罪而免死,就更是应该的事了。前面论及的唐沈亚之《冯燕传》中所写的冯燕和明陆人龙《型世言》中《****背夫遭诛侠士蒙恩得宥》所写的董文,与上官兴的故事就十分相似。他们的被免死竟可说是有例可援了。
对于侠,太史公有精到的概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史记·游侠传》)
也就是说,侠的特点主要是讲究信义,舍生忘死,扶助弱小,而不图报。在古代中国,律令对于小民来说,有时固然是自己安定生活的一种保障,但有时却是维护道义的一种禁锢,因为在那个****时代,法主要为维护统治者权利而制订,此其一;吏治腐败,当小民需要法律保护时,执行者还往往不行法而使小民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甚至被诬害。“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执法者有时就是如此不公;“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也是民间对执法不公状况一个侧面的形象概括,此其二。因此,小民、弱者需要侠客为其出气,为其打抱不平,为其平反冤案……这形成了一种崇奉侠行的文化现象,以至司马迁说,“闾巷之侠”“声施于天下”,“而学士多称于世”。他自己也满怀情感的呼唤:“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者!”(《史记·游侠传》)
《江淮异人录》中的《洪州书生》叙述一个小孩靠卖鞋维持生计,一个恶人将他的鞋子弄脏而不肯赔偿。一个书生代恶人赔了,反遭恶人辱骂。于是书生在夜间杀了恶人。《绿牡丹》写任正千的妻子贺氏与权奸之子王伦通奸,并设计诬任正千为盗,将其下于牢狱。花子方将任救出、鲍自安杀奸夫****等报仇。故事反映的正是侠客的锄强扶弱,打抱不平。目的在借助一种超人的力量维护正义。这种崇奉和需要,乃是导致中国人轻法制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现实有时逼得人们运用儒家的伦理作武器来维护道义,因为儒家伦理是历朝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这样做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现实逼迫人们欢呼侠客锄强扶弱,因为法对他们不公或执法者不为他们做主。站在小民立场上的作家,情感上希望执法者服从公道,或者说宁愿他们枉法而服从公道,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这“公道”的标准是什么?自然而然地便是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和能为小民弱者出气的墨家侠义思想。《聊斋志异》里有一篇小说《田七郎》,写猎人田七郎受武承休周济救护之恩,武承休恶仆林儿欲奸污其媳不遂,逃入御史府中。武久索而御史弟不与;获之送官,又为县宰释付御史之弟。武承休反遭县宰杖责。为报恩,也为打抱不平,田七郎脔割了林儿,又杀死了御史弟和县宰。这是执法者枉法,小民无奈,于是作者借侠客替社会锄恶,为弱者出气的典型。更为典型的是《聊斋志异·红玉》。小说写退居林下的宋御史强抢书生冯相如的妻子,以至冯生老父呕血而死,妻子不屈而亡。冯生奔走于衙门之中,却因宋氏父子上下行贿而状告无门。一个与冯生素昧平生的“虬髯丈夫”手刃了宋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冯被当作杀人犯投进监狱,两岁的儿子被吏役弃于路旁。“虬髯丈夫”复夜入衙府,投刀示警,使官府放了冯生。而小儿则为一狐红玉所救。冯生出狱,红玉携儿来归,并与冯生结为夫妻,“抚慰着冯生这颗破碎了的心,也借以抚慰在那个社会中受尽欺凌而无处告诉的小民”(拙著《〈聊斋志异〉评介》,见张伯伟主编《文苑明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小说不仅写了人侠,还写了狐侠,深刻地反映了小民对那个社会的失望和无奈——人侠还不能解除人们的苦难,消除这人间的不平,这才又幻想狐侠出现。观世音菩萨的成为救苦救难化身,实际也是基于这一原因。小民对于这类小说的欣赏,乃是他们轻法制的证明——自然也更是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的反映。
(四)仁恕对义侠的屈从
——《水浒传》文化侧面的理性反思之四
在执法与护理发生矛盾之时,《水浒传》的作者的情感天平常是向伦理一方倾斜,这已在上面谈过。对伦理内部各构件,作者的价值取向也有轻重之分。为了阐说的方便,也选两个故事及其相关的人物作为个案来进行分析。这两个故事一是江州劫法场;一是攻打大名府。相关的人物则是宋江、黄文炳以及卢俊义与李固、贾氏。
江州劫法场故事梗概:宋江因在浔阳楼醉题反诗,被欲夤缘蔡知府的无为军赋闲通判黄文炳告发,戴宗让宋江装疯,又被黄识破,关在江州牢中。戴宗奉命往京师送信,暗中与梁山泊通气,仿蔡京手迹、印信,复书蔡知府,要将宋江押往京师处置,好于中途劫持,复为黄文炳识破,戴宗也被下在牢中。于是梁山好汉劫了法场,救出宋江,又去无为军里杀了黄文炳一家四、五十口,活割了黄文炳。
吴用智取大名府
攻打大名府故事梗概:吴用设计,赚卢俊义入伙。卢俊义不从。管家李固,与卢俊义妻子久有奸情,趁机去官府首告。卢回到家中,被擒拿下狱。李固又一而再地设计陷害,卢俊义被判处斩。正要行刑,石秀舍生忘死相救,也被陷在狱中。梁山发大军前来攻打北京,引出了一系列的战斗。最后破了北京城,救出卢俊义,拿了李固和贾氏,回到梁山,“将二人割腹剜心,凌迟处死,抛弃尸首”,报了冤仇。
这是两个救人兼报仇故事的范型。两次救人报仇,救一人而无辜死者皆数以百计。拿梁山江洲劫法场救宋江说,那李逵,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颠翻的,不计其数。……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里去。晁盖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伤人!”那汉那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第四十回)所以鲁迅说,李逵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所砍多是平民。那石秀大名府劫法场,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第六十二回)宋江攻大名府时,比及柴进寻着吴用,急传号令去,休教杀害良民时,城中将及伤一半。但见:
烟迷城市,火燎楼台。千门万户受灾害,三市六街遭患难。鳌山倒塌,红光影里碎琉璃;屋宇崩摧,烈烟火中烧翡翠。……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战争场。(第六十六回)也应了鲁迅的那句话。战争中两军对垒厮杀时,兵将的死伤尚不在其中。从当今的价值观而言,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这两场战争都不值得大肆赞扬。
题反诗在宋江的生命中乃是件偶然的事情。虽然他通风报信放了晁盖等劫生辰纲的罪犯,那不过是因了他们所劫乃贪官的不义之财,且出于一种兄弟之义,宋江本人其实从未打算背叛朝廷。杀了阎婆惜,东躲西藏,就是不上梁山是一证;刺配江洲,须经梁山(书上是这样写的),怕被梁山的好汉邀上山去,特意叮嘱解差走小路是一证;上了山,花荣要给他开了枷锁,他说:“贤弟,是什么话!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是一证;上了梁山,坚不落草,说:“……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第三十六回)又是一证。若真要造反,哪还会被刺配江洲?反诗不过“醉题”而已。从宋江的角度说,黄文炳、蔡知府要将他下狱并处斩,在某种程度上是冤屈了一个忠孝义俱全的人,确实是执法过酷。但若从朝廷的角度说,作为赋闲官员的黄文炳举报宋江题反诗,则也是本分之内的事情;识破宋江装疯、看出太师书信系梁山伪造,坐实了宋江反叛朝廷的罪证,建议知府拿下宋江,禁于死牢,乃是在替朝廷执法,对朝廷,黄文炳也可算是忠。但作者却将宋江扬上了九天,将黄文炳贬下了十八层地狱,这里,他遵循的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伦理标准?
首先这里有个真忠假忠的问题,当然还有个大情节发展需要的问题。